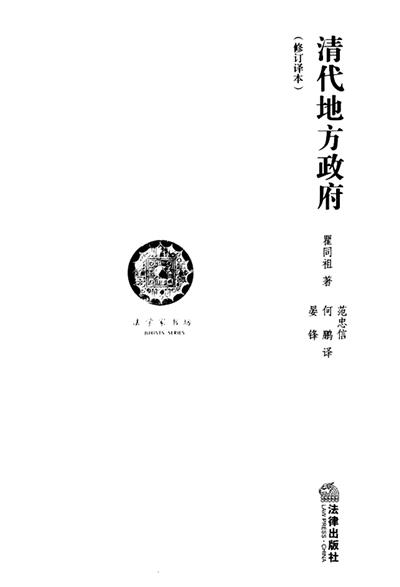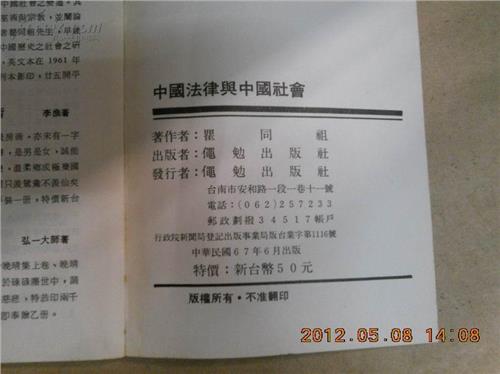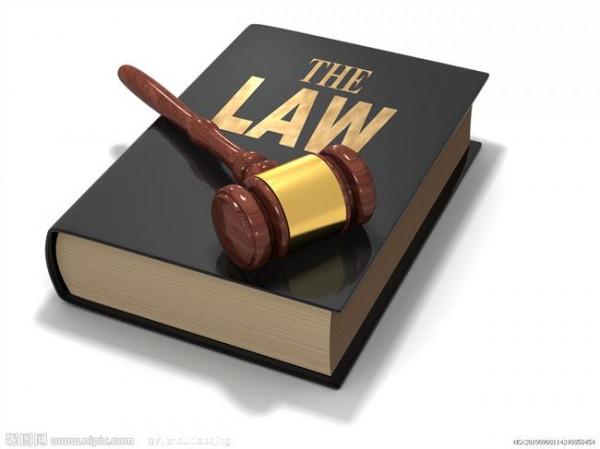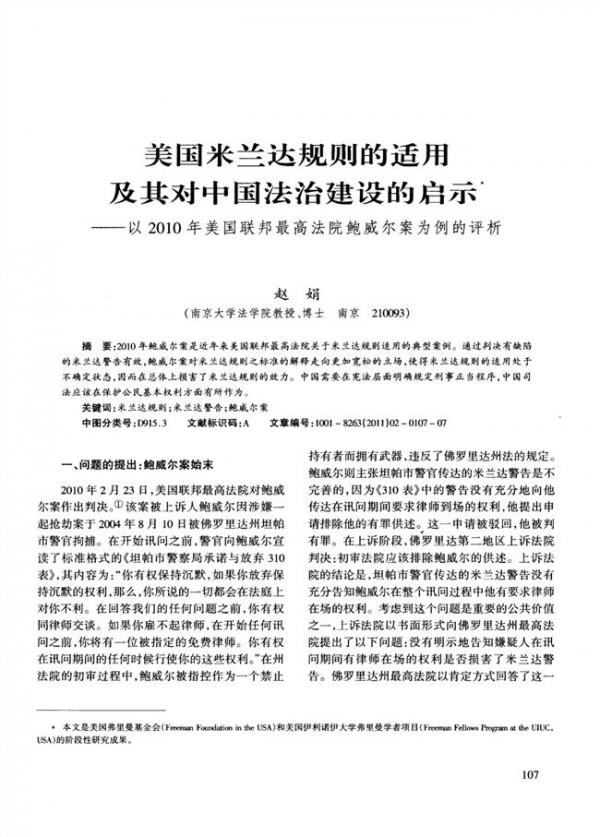瞿同祖中国法律社会史 瞿同祖和他的法律社会史 投稿:陆滈滉
1996年秋季,我们几个读法制史专业的博士生(胡旭晟、范忠信和我)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的丁小宣在一同开始筹划"20世纪中华法学文丛"的时候,就决意聘请法律史学界的老前辈—瞿同祖先生来担任这套文丛的学术顾问。
瞿先生有关法学方面的全部作品也在首批整理出版的选题之列。不过,虽然闻知瞿老在法史学界的大名已久,但对于瞿老其人及其治学的详细背景所知甚少,社会科学家辞典或者名人录一类的介绍显然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于是,利用这个机缘,我们有幸理由十足地访问了心中景仰已久的这位法史学老人。
是年初冬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按照预先的电话联系,在崇文门中国社会科学院宿舍大楼的十层,我们叩开了瞿老的家门。
以前,我们大多是从照片上认识瞿老的,而眼下,面对着这位已有86岁高龄的老学者,作为晚辈后学,我们的心中不觉微微地有些颤抖。
瞿老身材不高,看上去精神很好。略微泛着红润的面庞上隐约现出几处老年斑,在他善和慈祥的目光背后,不时闪现着智慧的神韵。他的言谈话语舒缓而平和,给人的印象是极其地安然闲适。
瞿老亲自开门,把我们带进他的书房。这书房非常地整洁,也很简朴。书架上的书并不是象我们原来想像的那样巨多。书桌上面,一小盆文竹沐浴着融融的阳光,给整个书房增添了几分雅致……
从这以后,我们便常常带着各种各样的好奇和疑问,开始了寻找法学家往昔足迹的漫长之路。通过与瞿老的多次访谈,渐渐地获得了对这位法史
学老人大部分治学经历的大致印象。
瞿同祖先生1910年7月12日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世宦之家。祖父瞿鸿
,号文慎,是
清光绪时的军机大臣。父亲瞿宣治,号希马,在驻瑞士和荷兰的公使馆里任职。瞿先生因与他祖父的生年同为庚戍,故取名同祖。又因生于阴历6月初6日,为天贶节,故字天贶,后改为天况。瞿先生在家里是独子,没有兄弟姐妹。1岁的时候,瞿先生就随祖父母和全家迁居到了上海,并在那里念完了小学。
1923年,瞿先生年仅13岁时,父亲就于回国途中去世了。不久,即由他的叔父接到了北京,先后进入有名的育英中学和汇文中学读书。瞿先生的叔父瞿宣颖,号兑之,时在北洋政府任职,是深具国学功底的文学家和史学家,曾在南
开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任教,有《汉魏六朝赋选》、《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等丰富著述。这使得瞿先生有条件从小就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史知识的训练和熏陶。
“我记得他在家里给我讲汉赋,他指点我古文,还教我历史,我对历史的兴趣就是受他影响的。
“上中学时,我叔叔请人给我和我的堂兄弟一起教中文,觉得中文学校不够用……有一件事印象很深,我在汇文中学时,自修古文,怎么办呢?自己拿了一本线装的《书经》,不带标点。《书经》是最难懂的一本书。我每天晚上自学,自己标点,不懂就看注疏,帮助理解。那时,《四书》、《左传》一类的书都已经看过了。”
1930年瞿先生在汇文中学毕业后,因为成绩优异而被保送到由美国在华的基督教会创办的燕京大学。当时的燕京大学经过司徒雷登多年的“苦心”经营,已发展成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大学。而且自1928年以后,燕大课程设置的重心就转向了文科。
除了声名显赫的新闻系外,社会学系也是燕大法学院的一个重点,以其雄厚的师资力量闻名遐迩。司徒雷登曾经在他的回忆录中讲道:燕京大学的“法学院包括政治系、经济系和社会学系,所有这些系科对中国的现代化都
是极其有用的。也许私人和政府机构最需要的就是那些主修社会学课程的毕业生。”瞿先生在燕京大学主修的正是社会学,他选读的一系列课程有林东海的“社会学概论”,雷洁琼的“社会学原理”,许士廉的“人口学”,杨开道的“农村社会学”和“统计学”,吴文藻的“人类学”、“家族社会学”、“西洋社会思想史”,张鸿钧的“社会工作”,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史”,并听完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派克(Robert E.
Park)教授来燕大所作的一学期的“社会学”讲座。
除此之外,他还选修了钱穆的“国学概论”,肖公权的“西洋政治思想史”,吕复的“比较宪法”,张东荪的“西洋哲学”,陆志伟的“心理学”,郭云观的“法学通论”等等。正是在这样一个有利的环境下,瞿先生在燕园度过了四年大学本科生活。
“在燕京大学,我主要上社会学系和历史方面的课。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吴文藻和杨开道老师。历史系的老师影响较多的是邓之诚,他教中国历史。还有洪业老师,他教历史方法……作为一所教会大学,与其它的学校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燕京的许多课几乎都是用英文讲的,除了中国历史和国文课以外。”
1934年,燕京大学依照教
育部新颁布的《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正式设立了研究院。瞿先生适逢当年毕业,接着便转入研究院,在吴文藻教授和杨开道教授的指导下,攻读社会史研究生,二年后毕业,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学位论文就是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封建社会》,它是在充实大学毕业论文《周代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写成的,而后者于1934年发表在燕京大学社会系出版的《社会学界》第8卷上。
《中国封建社会》是瞿先生研究社会史的第一部著作。据他的导师杨开道先生的评价,瞿同祖对于美国现在社会研究已具根基,对于欧洲
家纵横
中古社会情形亦极娴熟,然后以之研究中国过去封建社会,显已立于不败之地。“本书为瞿君对于中国过去社会第一次的分析,费时虽仅二载,然其了解,其组织,已有若干独到之处。比一班专讲空洞理论,或一班专收零星材料的朋友,自然又高出一筹。
瞿君誓以十年二十年之精力,从事于中国过去社会之研究,从此异军突起。”“当时国内一些大学曾把它作为一部重要的教学参考书。后来,该书又被译成日文出版。不过,后来瞿先生对此书并不满意,认为它是他的著作中最不成熟的一本”。美国华盛顿大学曾经有人翻译此书,虽已译出一章,最终还是被瞿先生婉言谢绝了。瞿先生对个人治学要求之严谨由此可见一斑。
1938年,瞿先生转往内地重庆。第二年又来到昆明,开始在云南大学执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在那里,他开设了“中国社会史”、“中国经济史”和“中国法制史”三门课程,另外又在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讲授“中国社会史”课。
在中国法制史课的准备和讲授过程中,瞿先生倾注了大量心血,精心钻研,利用授课之余,“伏案写读,敌机不时来袭,有警辄匆匆挟稿而走,时作时辍,倍平日之力,始得竟其功。”其结果就产生了他的那部名著—《中
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该书被作为吴文藻主编的《社会学丛刊》甲集第五种,于194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这部书中,瞿先生首次表达了他关于中国古代法律研究的一些基本观点,指出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是我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它们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中国社会的基础,而且是古代法律所着重维护
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在法律上占有极为突出的地位。后来,瞿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用业余时间将此书译成英文,并利用哥大图书馆丰富的馆藏,弥补了最初在昆明写作此书时由于缺少《宋刑统》这份材料而造成的遗憾,写成了英文版的《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Law and Society in Traditional China),该书收入法国巴黎大学高等研究实用学院经济与社会科学部《海外世界:过去和现在》丛书,由巴黎和海牙穆东书店1961年出版。
英文《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的问世,显然受到了国际汉学界和史学界的广泛关注:
“中文原作是中国法制史研究发展中最重要的一个里程
碑……向中国读者提出了创新的观点,……将法律看成是整个社会制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此书无疑是西文中关于中国法律最好的一本书。”
“此书原著是一部标准的中文参考书,它对一切研究中国法律的学者都有影响,并将继续影响他们……此书有丰富的重要资料,组织完善,论证精辟,研究传统中国的学者都深受其益。”
“作者不仅阐明了法律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的作用,并且对社会结构性质的理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此书是一本研究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其主要特征的专著。它结合中国历史发展的社会背景以及儒家思想和
法家思想对我国古代法律的影响等来进行论述,论史结合,寓论于史,对研究中国法律史和了解中国古代社会是一本有益的参考书。”
这部作品的问世,为确立瞿先生在古代法律史研究领域里的国际地位奠定了重要而坚实的基础。
瞿老早年本专攻社会学,然而为何又转向对中国古代法律的研究?是什么原因促使他把古代社会史与法制史结合起来,写出了广为学界称道且独树一帜的那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选取这种独特的观察视角,是出于怎样一种考虑?它的学术意义与成就又是什么?作为一位有着深厚学术底蕴的老学者,他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值得珍视的治学经验?等等,这些问题,令人颇感兴趣。
下面关于这些问题的访谈记录,或许会对我们有所启发。
——从社会学转向法律社会史
我当时在燕京大学上的是社会学系,想用社会学的方法和观点去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我的导师吴文藻和杨开道也鼓励我作这方面的研究。他们认为有价值,而且我这方面也有基础。于是我决心以社会史为专业,试图用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
中国社会史,希望能作出一点成绩来。当时,我读了享利·梅因(Henry Maine)的《古代法》(Ancient Law),还有他的《早期法律与习俗》(Early Law and Custom)。又读了维诺格拉多夫(Paul Vinogradoff)的《历史法学大纲》(Outlines of Historical Jurisprudence)。
读了这些书之后,又对法律产生了浓厚兴趣,也想写出像梅因那样能成一家之言的书。
后来去了云南大学,开了一门课讲中国法制史。这样就收集研究了中国古代的法律材料,又读了人类学家写的书,有马凌诺斯基(B.Malinowski)的《蛮族社会之犯罪与风俗》(Crime and Custom in Savage Society),罗布林(W.
A.Robson)的《文化及法律之成长》(Civiliziation and the Growth of Law),还有哈特兰(E.
S.Hartland)的《原始法律》(Primitive Law)。读了这些书后,深为叹服,受到了很多的启发。这样,既有法学家的影响,又有人类学家的影响,又因为要备课,研究中国古代法,就利用写讲稿和研究的心得,以及对中国古代法律特征的理解,写出了《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这本书是在云南写成的。
我个人认为,法律与社会现象是不可分割的;法律是社会中的一种制度,不能离开社会;研究法律必须放到社会中去。把法律史与社会史结合起
来的研究,是我个人创新的尝试,以前没有人这么作过,所以,它既是一部法制史,也是一部社会史的书。
——法律研究的经历燕京大学的法律系比较薄弱,课程不多。当时的法学院跟现在的概念不一样,我在的社会学系就属于法学院,还有政治系、经济系。我听过政治系吕复教授讲授的“比较宪法” ,另外,我还听了郭云观的“法学通论”,没有中国法制史一课,缺乏这方面的训练。
所以我说在法律方面,我“上乏师承”。法律都是自学的,也没有指导。从享利·梅因的书读起。(问:你自学法律是否感到有什么困难?)没感到困难,完全是自学的。梅因的书记得是由杨开道导师推荐的……
我读的主要是人类学者和其它的外国法律书。先读梅因、维诺格拉多夫,去云南大学后,为了备课,又阅读现存的古代法典,像唐律、明、清律、历代刑法志、“十通”、各种“会要”等有关古代的法律著述,完全是靠自己独立的摸索。研究了这些法典之后,有了一些心得,就想把这些心得写出来。如果没有心得,我也就无意写这部法制史了。你看,《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的体系与当时的中国法制史书完全不同。
家纵横
科的知识是不够用的,要不断
——法律社会史研究之特点
我的研究是要找出中国古代法律的特征和精神来,它们主要表现在“家族”和“阶级”的概念上,我感觉到,研究中国古代法律要总结出中国古代法律的精神与特征,要讲出个道理来,提出我个人的观点,供读者参考。事实上,对中国古代法律的观点也完全可以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提出来。
举个例子,一般人们都强调中国古代刑法,民法很少,特别是外国人都有这种认识,中国古代民法不发达,这是很多人的共识,我的研究也超不出这个范围,因为是共识,我就没有进一步去研究它。
——学术评价与治学经验 关于这部书的评价,国外已经有很多了。
《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和《清代地方政府》这两部英文版的书,至今仍是美国各大学亚洲系的指定参考书,在美国的汉学界有一定影响。
我治学的最大感受,就是用社会学观点来研究中国历史,对历史学和社会学都是一个出路,是一条途径。这也是我一生治学的方向。
作学问总要有勤奋和一丝不苟的精神。作研究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我感到现在大学学科分得太细,单靠一个学
这里我们不准备对瞿老的研究作更多的学术评论,因为扩充自己的知识面。我写《法律与社会》的时候,就不断阅读法律名著和人类学家关于原始社会法律的著作;研究清代地方政府时,就多读政治学、行政学、特别是欧美各国政府的专著,对各国地方政府进行比较。总之,要累积跨学科的知识,不断学习,才能有所成就,这就要靠勤奋和认真了。
我在写《法律与社会》那本书的时候,条件极为艰苦,要不是勤奋,是写不出来的。我记得有一年在农村乡下,晚上点菜油灯照明,光线昏暗,不能看书写作。我就想了个办法,躲在床上反复思考写作中所遇到的问题,有了腹稿,次日写稿就比较顺利了,这样就不致浪费时间。
有一年为了躲避空袭,住在昆明附近的呈贡县乡间,我们社会学系的几个人住在农民家里。我和费孝通教授住在一起。吴文藻教授一家在去重庆以前也住在呈贡。每个礼拜我们都骑马到火车站,然后坐火车进城去上课。我在城里有时住在西南联大的宿舍,有时到朋友家里去住。上完课又坐火车,再骑马回来……和现在大不一样,现在太舒服了。当时条件很艰苦,全靠毅力,作学问要有毅力。
那需要专门具体地分析和展开。不过,从以上他的学术自述当中,我们不难看出瞿老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与风格特色。大体来讲,首先是出于对历史和社会学的兴趣,瞿老把社会学的研究推进到了社会史领域,继而又在梅因等历史法学和人类学法学作者精湛研究的影响和感染下,把对象确定在了古代社会中的法律,并力图对中国历史上的法律提供一种社会学的解释。
这种社会学解释在方法论上表现为“功能主义”观点,即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风俗、制度或信仰等视为一个相互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的统一体,通过考察各个部分在社区整体中所占的地位,来探求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和理解。通过研究,在瞿老的心目中,法律被界定在这样的概念前提之下:
(1)法律与社会之间有密切的关系。瞿老认为,不能像分析学派那样把法律视为一种孤立的存在;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制度之一,是社会规范之一;法律与风俗、习惯、制度、伦理道德和意识形态等的关系极为密切;任何社会的法律都是为了维护并巩固其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而制定的;只有充分了解产生某一种法律的社会背景,才能了解这些法律的意义和作用。
(2)法律分为“书本上的法律”(law in book)和"行动中的法
律"(law in action)。瞿老指出,由于社会现实与法律条文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要知道法律在社会上的实施情况是否有效,推行程度如何,对人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等问题,就必须采取功能的研究,即不仅要分析法律条文,还应注意法律的实效问题。
据此,瞿老提出了自己研究的目标:一是研究并分析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主要特征;二是以前者为基础,进一步探究中国古代法律自汉至清有无重大变化。多年间的法律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分析,广泛利用正史、野史、笔记、小说中的法律史料和法典、个案和判例等法律文献材料(就只研究书面的历史记载这一点而言,瞿老的研究与梅因相似),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其主要特征,以及这种精神和特征的变化轨迹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
在兼跨社会学、历史、法律这三个学科领域之间,开创了把法律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的研究,由此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学术研究体系,它可以被称为“法律社会史”。
这正是他对中国法制史这门学科发展作出的一个独特贡献,它不仅仅是从未有过的一种尝试,而且直到今天,仍难有人超越他所取得的成就。
应当指出的是,法律社会史研究的出现,与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以来的影响,社会
史专题研究的拓展和深入都有着内在的思想逻辑关系。而就一般法学而言,这种研究正代表了当时世界法学发展的一个趋势。正如美国法学家庞德在评价19世纪后期以来欧洲社会学法学的发展时所指出的:“本世纪初,出现了各种社会学方法的综合,出现了各门社会科学的综合,出现了以考虑法律的作用为主,而不是以法律的抽象内容为主的功能观,这种功能观将法律视为可凭人类智慧的努力加以改进的一种社会制度……以上出现的情况,逐渐成了社会学法学家公认的信条,并日益成了所有法学家的公认的信条。
”
当然,瞿老所以能取得如此之高的学术成就,是与多种因素
有关的。例如,可以说自幼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开启了他的心智,哺育了他的人文情怀;连续的教会式教育,至少为他的英文功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名师指点下的系统严格的学术训练与伟大学者们精辟论著的感染,一方面使他具有了跨学科研究的基本素质,另外又开阔了他的视野,可以从中汲取他所需要的一切有益的养分;而凭着“勤奋”和“毅力”——这是瞿老以亲身体验而得到的两个极普通的词,最终使他成为一位渊博精深的学者。
说到这里,我们感到,一流的学术成就来自具有一流素质学者的创造,而一流学者的造就要有一流的教育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