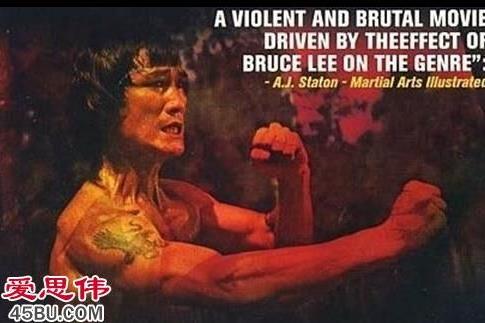成奎安说:“我自己就是黑社会 当然演得像啊!”(ZT)
Julio自传:Still alive in GuangZhou尽管还会偶尔买木薯面做家乡菜,但刚果人julio和他的哥哥Mathew携妻带子已在广州生活了多年,中文也说得相当流利,除了肤色,他们与中国人没有多大不同。
不过,很多人还是仍然只指认他们是“来自非洲的黑人”。julio说他在中国的20多年来,跟太多的中国人打过交道,而他在广州的故事,也可以说上几天几夜。记者·炫风 实习生 罗婷婷 杨禹章 广州报道 摄影·孙炯眼睛圆大,生活在广州的刚果人Julio最近有点烦:一是金融风暴让他的生意陷入了低谷,二是近来警察频频到他家查护照、签证,三是哥哥Mathew一家的照片出现在一份本地报纸上,成为了尼日利亚人在广州聚集事件报道的配图,尽管他们与此毫无关联。
我是Julio,来自刚果,42岁。小时候住在首都金沙萨,除了读书,我会跟伙伴们拿两条木棍做球门,光着脚踢足球。我也叫朱力,现在生活在广州。我有一个中国老婆,还有两个女儿。
我去过中国很多地方,最后留在了广州。1990年代中期,广州还没有多少黑人,我已经在沙河顶(注:广州的老服装批发集散地)做生意。我爱广州,熟悉这里的酒吧,老婆也是在这里认识的;我也曾在城中村被偷过裤子,在小北路(注:目前广州非洲人最密集的地区)开过公司,不过最近却被警察频繁地查护照。世界在变。小时候我是天主教徒,现在我信基督。小时候我不想来中国,但爸爸跟我说“中国至少可以发射卫星”,所以我来了。
小时候我和哥哥在教堂弹吉他,10年前我在东莞夜总会卖唱,现在我要为两个女儿还有车子与房子,在广州奋斗。我曾经差点崩溃——从香港到上海都找不到工作,我打国际长途向爸爸诉苦,但爸爸却说 “你是个男人,你回到刚果照样也没有工作,你必须留在中国”。
我在中国的20多年跟太多中国人打过交道,而我在广州的故事,也可以说上几天几夜。哥哥说,我们的孩子就是Afircan Chinese,他们的中文都会说得很好,在中国的前路将会更顺利。
未来他们的中国故事,大概也不会像我这样离奇。中国印象如今我在广州租房居住,一个月2500元。这是个炎热的城市,有时我会带着孩子们去游泳。我的故乡很少高楼,四野开阔,广州曾经也这样,很适合我,可惜现在广州的高楼也多了。李小龙和《丁丁历险记·蓝莲花》是我最初的中国印象。动画片里那些带着飞檐的建筑,还有象形文字都是我感兴趣的。想不到,这些在几十年后成了我生活的大部分。
刚果也有中国这样的官僚系统。我爸爸是公务员,他在首都国土局工作的时候,生活得很滋润,给我们几个兄弟每人都准备了一块几十平方米的土地(将来盖房子),可惜后来一个一个地都卖掉了。老实说,我在刚果时只对上海有好印象,因为留学归来的同胞说上海人思想很开放。后来我也到过上海找工作,当时上海人确实不排斥外国人,他们“排外”排的只是外地人,不过听说现在已经好多了。我刚来中国的几年,是在北京的大学里度过的。
那是1980年代,街上基本上看不到黑人,很多人见到我都会“哇!看看看!”这样叫,让我有点不舒服。在学校,有的老师会告诉学生尤其是女生不要接近我们,说我们会传染疾病,所以如果我坐在某个位置,旁边是绝对不会有女生的。
即使是现在的广州,仍会有类似的情形。我哥哥说广州有两种中国人:一种就是主宰广州的人,他们觉得外国人没有什么不同;另一些就会很在意你的肤色,如果你走近他们,他们会走得远远的。我现在还记得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在北京快毕业的时候,我曾经在一个饭馆里被几个中国人围攻,额头都被打破了。
当时我和一个中国朋友在饭馆里坐下来,就听有人喊我“滚”,接着先是有一个人拿扁担来袭击我,后来又来了三个人用凳子砸我。我没有反抗,拼命用手护着头,直到血流出来,他们才停手。后来警察对我解释说,这是因为那些人早前被一些换外币的黑人欺骗了,希望我不要把这个事情闹大。我觉得很委屈,为什么其他非洲人的犯罪,要让我来承受痛苦?1990年前后,我在中国的生活并不顺利。
我毕业后去过上海和香港,但找不到工作。香港对外籍人打工监管很严,上海企业则对我说他们只招本地人。那时我最大的乐趣是在酒吧里弹唱赚钱,酒吧里外国人多,在音乐中喝酒的气氛也很适合我,那些时刻,我就像回到了金沙萨。
夜场江湖我住过广州的各种楼房。1996年我住在天河的城中村,有一天我的裤子被偷了,后来发现是窗外的小偷,用长长的棍子伸到屋子里挑走的。我在城中村住得并不久,因为警察很快就跟我说,我(非洲人)不能在这里住,因为不安全。
于是我只得搬到更贵的地方。活在广州,不免要跟派出所打交道。我当时住的一个小区,就只有我一家黑人,我入住时还主动去派出所登记。我就算接待故乡的朋友,也会主动带他们去派出所登记,但警察还要到你家里查,我就想,为什么要这样?是的,他们对我不信任,他们太紧张了。在中国最艰苦的一年,是1990年,当时刚毕业的我在顺德打工。公司安排我住农民房,整个冬天都没热水。
我跟上司经理出去谈业务时,必须说英语,不准说中文,还要自称美国人。这个经理不喜欢我跟其他人接触,甚至不让我跟董事长接近,但我开始交朋友了,学会吃狗肉、吃海鲜,董事长秘书还开车带我去兜风。1990年代下半期到2000年年初,我是个到处跑场的非洲歌手。
我到过很多省份唱歌,有小城市的小剧院,也有大都市的酒吧。在有些地方,人们来看演出只是为了围观我,广州曾经很旺的“非洲吧”,也是我1995年驻场唱歌时带红的。
东奔西跑地,很多人请我喝酒、洗脚,我还曾经很纳闷,中国人为什么要专门去洗脚呢?在夜场唱歌,基本上没遇到过警察来盘查的情况,反倒是在一些小城市里,文化部门会来演出现场找碴,然后说我是外国人,又没有演出证那样的要罚款,有一次还把我的护照给没收了。不过,经纪人还是能通过关系或花钱把我的护照给弄回来。弹琴唱歌的那些年,我才二十多岁,月收入上万,花钱很随意,每个月交给广州移动的话费都有两千多。
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去东莞的夜总会演出的情形:很多漂亮的女孩子列在大门口,好架势,我从来没有见过。在一些大的夜场,我还跟一些明星同台过,譬如香港艺人“大傻”,成奎安。我当时好奇地问他,你能演这么多黑社会角色,而且演得这么像,他回答说:“我自己就是黑社会,当然演得像啊!”在夜场的台上,我要唱歌,要搞笑,有时客人还要你陪喝酒,有的客人喝疯了,把一叠叠港币、澳(门)币、人民币拿出来甩,成千地给我小费。
有的客人喝多了也会乱说话,有一次,我穿了八路军的演出服唱歌,一个观众就走上台来,抢了话筒,说你们外国人敢侮辱中国的解放军!还有些客人,会用很难听的话来挑衅我,但慢慢地,我也就习惯了。放浪的生活始终不是长远之计。
我经常两三点才能睡觉,偶尔被迫喝醉,而且我遇到的人都是素质比较低的,站在台上还得不到尊敬。在2001年的时候,我已经32岁了,我真的想放弃那种生活了。风月过后我是有梦想的。刚果有很多河,很多水资源,却没有人知道利用,刚果人不会用机器,只会用手去劳作。
我和哥哥最大的梦想,就是在中国买一些养殖设备,将来运到刚果去发展农业。但是,在中国的头十几年,我几乎把自己的信仰都抛却了。在我想离开夜场,离开唱歌岁月的时候,我又重新接近了上帝。是的,我感觉到孤独,我想跟上帝说说话,得到他的指引,而且我很想安定下来。
这时候我想结婚了,但在中国找老婆并不容易。第一个跟我玩得好的女生,是在北京读书时的大学同学,班上同学都对她说外国人很会骗中国女孩子感情,但她觉得我人很好,而且她找我也是为了练习英文。
在夜场唱歌的时候,我也交过一些女朋友,但我知道那些都是短暂的——很多只是想我给她买东西,或者懒得干活,住在我家而已。我曾经对一个中国女孩动过结婚念头,她叫阿兰,我在1996年开始跟她谈恋爱。她是一个开美容店的广州人,从来不要求我买什么、做什么,一切都是顺其自然,不像其他女孩子那样懒惰或者随意。
我们断断续续地在一起,直到2001年的某一天,她跟我说,她交了个可能要结婚的男朋友??结果我参加了她的婚礼,当然,新郎不是我。
2002年认识我太太时,我也没想到会与她结婚。她是在小北路做服装生意的北方人,粤语说得很好。除了阿兰,她是第二个会帮我洗衣服、做饭的女孩子,也不喜欢看我在夜场的那些演出。我一直跟她说,我很想安定下来,好好地在这里生活下去,但如果你的父母不同意找一个黑人做女婿,我不会勉强与你在一起——很幸运,这次跟过去的女朋友不一样,她父母并不反对接纳一个非洲的女婿。
2005年,在拍拖3年后,我们结婚了。我到太太的老家去时,她家里来了好多亲戚,四乡的人都来了,每天都有很多人来看我。那真是很奇妙的事情,那种感觉,跟过去在北京,或者现在在广东的农村被围观的感觉不一样。我爸爸妈妈也过来了,他们不懂中国话,但两个不同种族的长辈能坐在一起,真是一件太奇妙的事情。我现在有两个女儿,长得既像她们的爸爸,也像她们的妈妈。
我每天给他们看英文儿童碟片,逗她们玩,教她们说中文、英文和刚果话。我会带女儿参加基督教小组的活动。我的大女儿说她将来要做个医生,每天都要给我打针,我则学会了用打针来吓唬其他小朋友,无论他的皮肤是黑的,还是黄的。
在我的故乡,家庭的关系就是像弹簧一样,可以无限地拉长,却不会断裂;亲人间会有不同的意见,会有一些矛盾,但是决不会断绝关系。但我觉得很奇怪的是,现在很多中国人都把自己的孩子丢在故乡让老人家抚养,我们刚果人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
生意难做我做的第一笔贸易生意,是在2002年。那次我为一个刚果商人采购了一万多人民币的货物,她给了我100美元的酬劳。哈,当然,她不知道我在采购时,其实也像其他中国人一样吃了回扣。当时,广州向非洲的出口正在起步加速,小北路开始有非洲商人聚集,我已经能带着同胞在沙河顶一带采购货品、运回刚果了。
广州周边的轻工业、电子工业发达,又有很多批发市场,加上离香港很近,很多非洲人都来做生意——有的是穆斯林国家的商人带过来,有的是香港的非洲商人转移过来。
广州不像香港那样空间密集,生活成本也低一点,买货、发运都很方便,而且,广州的警察长期以来对我们也算友好。2005年,我的公司也开到了小北路附近。那时候生意真是好啊,很多非洲下家的采购者一来,就有很多人——无论是非洲人或者中国人拥过来抢生意。我很聪明,把公司稍微开在附近非洲人没那么密集的地方,这样我就可以避免客人被撬走。
我觉得很多事情,是从去年奥运会之后开始变得糟糕的。之前很多事情都很好,生意很顺利,非洲商人来来往往,但奥运之后,很多人从非洲的中国大使馆那边拿不到签证了。既然没有签证,非洲客户也来不了,加上金融海啸,所以对于我来说,2008年真是很坏很坏的一年。
金融海啸加剧了一些贸易纠纷,收了钱没出货,给了定金不付款等事情经常发生。其实,中国商人提供的货物的质量未必过关,非洲经济也不稳定,非洲客户签了合同也会有付不起的时候??唉,很倒霉,我的公司现在也有个生意官司缠身,已经花了十几万(打官司及赔偿),还有几万(花销)在后头呢。
我是个良民,每年都会去工商部门办执照年审,不过也有小部分商人不办手续,一般是那些没有固定办公室的皮包客。你想想看,不办执照,在天秀大厦里每个月租金就要3000多,被查封的话损失该有多大呀!而且有了营业执照,你就可以办就业证,这样你的签证就可以有效了。
今年六月和七月,人们不知道的是,警察查非洲人护照的次数突然增加了很多,这让我很不习惯,我经常跟那个早就认识我但又三番四次到我家查证的警察说:“你明知道我不会跑路,为什么还这样不信任我呢?”中国是一个正在发展的国家,是非洲国家的榜样。
中国30年之前和现在的非洲国家一样,我们到这里,是想知道中国是怎样做到(目前的样子)的。连你们记者都不懂,这里面有复杂的东西,但很多非洲人却以中国为豪。在尼日利亚人聚集的事件发生以后,中国的媒体一下子都来关心黑人问题了。
其实对于黑人,记者是应该多报道的,这么多非洲人在中国,又有哪个中国人肯坐下来好好跟他们谈谈,看看他们在想什么呢?人们总是懒得去寻根问底。我猜测,尼日利亚人并不是针对中国人在游行,而是针对公安部门的执法,为什么你们(记者)只去写非洲人的不好呢?去年金融海啸到现在,我公司的生意很淡很淡,我曾经请过三个中国雇员,现在为了节约成本,只留下了一个。
生活还是得继续,我还得养大我的孩子。我还得寻找安哥拉的大客户,他们有石油、有购买力,我想继续把医疗设备和电器交易卖到非洲去。希望倒霉的日子尽快过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