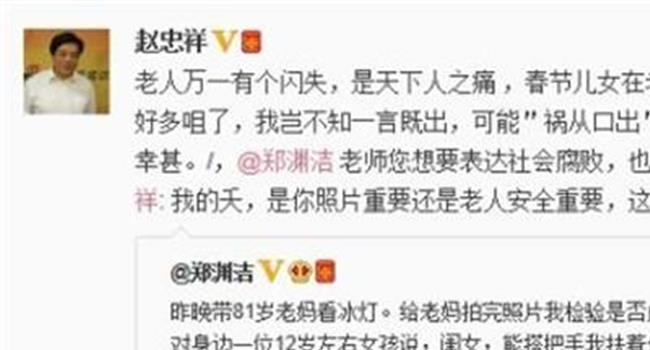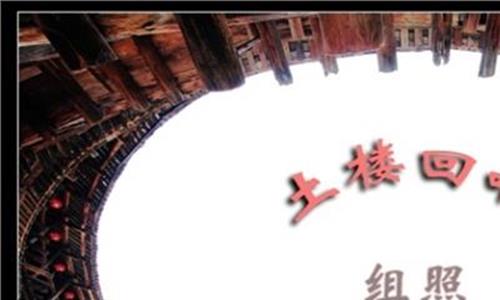打工诗人郑小琼现状 郑小琼:东莞的打工女诗人
她成了中国打工者的坚强代表,“她总在诗里面写这个群体的痛苦,像前两年查暂住证,像现在很多厂里工人的工伤完全得不到补偿”。她觉得这些感受不是她个人的,更是这个群体的。
2000年,20岁的郑小琼从四川南充的卫校毕业后,在当地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只能去一些黑诊所当护士。她非常抵触,可是家里为她上学欠了一大笔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她南下东莞打工。“那是我特别不愿意想的日子。”习惯微笑的郑小琼在提及为什么离开家乡的时候,陷入了痛楚。
本来怕见生人,话就很少,声音突然低沉下去,更沉寂,她习惯把一切放进文字中。郑小琼最初写的诗全是怀念家乡的,是简单清浅的乡愁,可是流水线上只有编号和工伤的日子,很快让她的写作风格有了巨大的变化。她开始投稿,并且和一些散落在珠三角工厂里的诗人们有了联系,人们把她定位于珠三角为数不少的“打工诗人”中的一个。
7年多过去了,她获得了许多来自文学界的奖项,可丝毫没改变她的处境。她还是在一家小五金厂打工,每天发送传真,或者在东莞的乡镇间奔波,为自己厂的产品做售后服务,随身携带的粉色廉价小布包里全是产品销售单据。
最近她又要到北京领奖,这让她不安而又期待:不安是害怕请假时间过多失去工作,去年得奖后就是这样的结果;而期待的不仅是荣誉,更是那不算高的万元奖金,“可以顶我一年的收入了”。
某个机台上打磨生活
东莞的城市化程度非常高,被铁门封锁的灰色工厂连绵不断。这并不是想象中齐整的厂房,一幢当地农民盖的简陋楼房,就可租给若干家开设工厂。处处机器轰鸣,几乎看不见乡野该有的绿色。
许多家工厂门口都悬挂着招工条幅,经济发展使打工者的选择越来越多,呈现所谓“民工荒”。“比我8年前来这里时好多了。”郑小琼小声说。8年前刚来东莞时,她好久找不到工作,有时连着几天靠各个老乡的帮助度日,某天在地上捡了5块钱,“赶紧捡起来,好感谢掉了这钱的人,让我能吃上一顿饱饭”。
离开的时候很难受,那是她到东莞好不容易找的一份比较安稳的工作。之前她做过流水线上的工人,那里只叫编号,“我刚被叫245号的时候很不习惯,后来明白那是管理的最好办法,因为工人三天两头离开,流水线前后协作的人还记不住名字的时候,这人也许就走了”。
在那种环境里,她学会了忍受各种打工者必须忍受的生活:夏天睡在地面上,因为没有电扇;和坐了一个半小时车来看她的朋友隔着铁门说话,因为一个月3次会见朋友的时间已经被用掉了。
也有她完全不能忍受的生活。有次她的指甲被流水线削掉了半个,送进医院时,发现别的床上的病人伤势都比她严重很多,每到夜晚,那些床上的哀鸣使她无法入睡。她还记得自己的工友断指时,老板怕弄脏自己的新车,坚决让工友等采购车回来,“一等就是半小时”。
而那工友也并不急忙去医院,因为治不好,可能获得更多的几千元赔偿。多年后讲起这些,她还是很激动:“那些机器,能把人的手压成蒜泥的样子。说起来也并不全是某个人的责任,那些落后的机器,很多时候逼迫你必须要把手放得深一点。”
这种愤怒难忘,使她在《人民文学》颁奖典礼上的讲话成了某种意义的经典文本:“在珠三角每年有超过4万根的断指之痛时,我一直在计算着,这些断指如果摆成一条直线,它们将会有多长,而这条线还在不断地、快速地加长着。此刻,我想得更多的是这些瘦弱的文字有什么用?它们不能接起任何一根断指。”可是,“讲这段话的时候,我还是结结巴巴的,可能是为了掩饰我的自卑”。
生活也没有改变,甚至还增加了她的支出。东莞很多工厂因为偏远而不在邮局送信范围内,邮局送信上门后要收取费用,工厂则把这些费用转加到收信人手上,“我的信最多,每次去取信都要付十几块钱,好心疼”。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最低的时候只有几百元。
现在她把自己的收信地址转到一个也是写诗的朋友那里,朋友在一家公司做中层,代她收信很方便,可是所在镇距离她的工厂有两小时的路程。她晕车,所以上车就开始强迫自己昏睡,东莞的马路上交通拥挤,所有司机都在尖锐地按着喇叭,可是她还是趴在窗口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