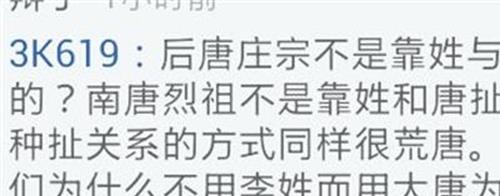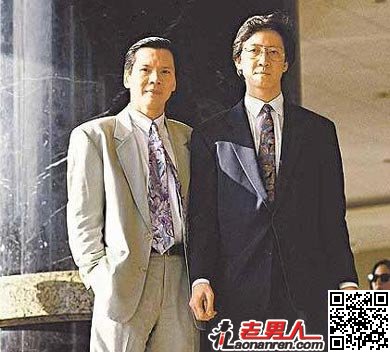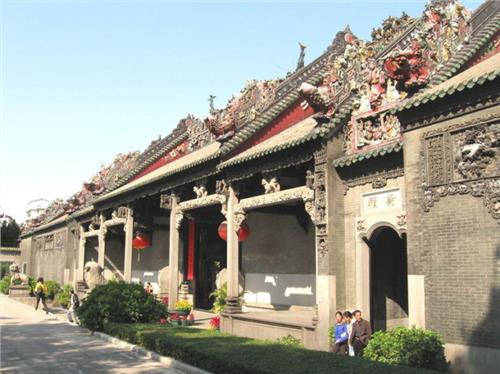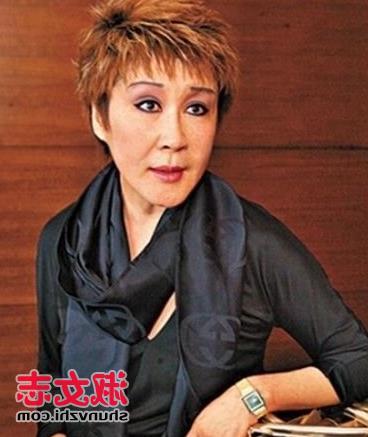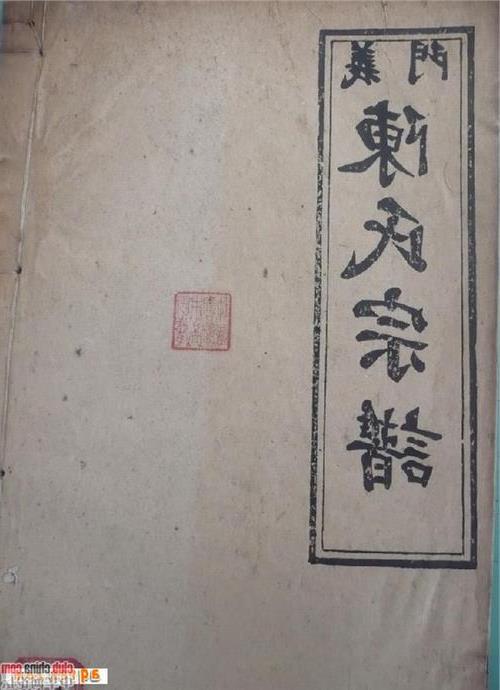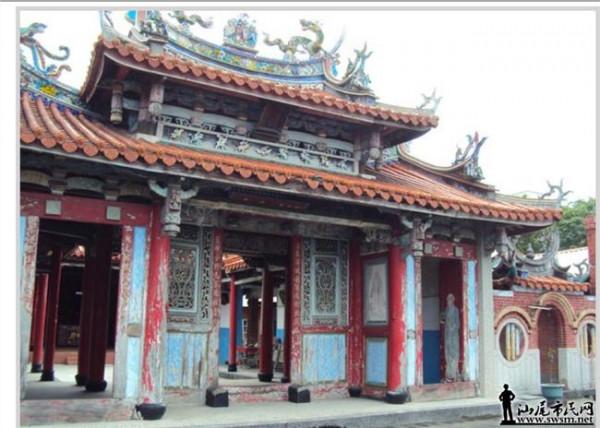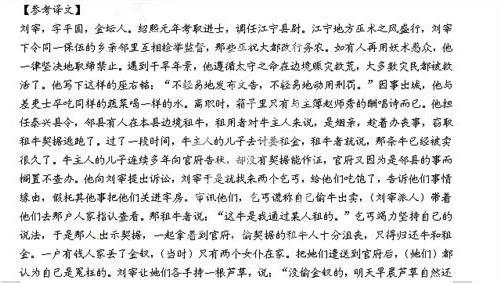陈实字仲弓 颍川陈氏始相——汉太邱长陈实公
陈实字仲弓,是颍川郡许县人(今河南登封县),生于东汉和帝永元十五年(公元一〇三年)。实幼年的时候因家境清贫,所受教育无多;但他的天资非常聪颖,自从做儿童的时候起,就在游戏中也已为一般小儿们诚心悦服而归向他。
稍为长大后,在县吏处找差事做,后来擢升做都亭刺史的助手,却很有志好学,平时除办公之外,其余的时间,都是手不离卷,当时县令邓邵见到这情形很诧异,常常面试他的学识;更为惊奇,而大加赞赏,从此邓邵甚为器重,而想提拔他,设法培植他成大才,于是保荐他进入太学(官办的学府)里头读书。
嗣后实的学问更加进步。他在太学里学业完成后,县令复召他回去做官,可是他竟以才学不够,而婉言谢绝,就隐居于阳城山(在登封东北),闭门读书,不愿出来。
恰在那个时候,阳城地方有一个杀人犯在逃亡,同县人杨吏则疑心是陈实所为,便逮捕了他归案,经过拷打审判后,没有实在凭据,方才释放出来。第二年实公做了督邮职(为太守的佐吏,负责督察属下各县吏的得失),便密托许县令,用礼召那位杨吏到郡府款待他,远近听得这事的,都为钦服。
他因为家贫,便再出来做郡西门的亭长,后来转做功曹的职位。当时中常侍(内宫大臣)侯览,托太守高伦任用一吏,高伦便吩咐署他做文书椽(文书署理职),实公知道那人是干不来事情的;于是他就怀藏了檄书请见,对高伦说:“这个人不宜任用他,但是侯常侍,却又不可违负他的,实请从外面署他,庶几不累着你的盛德。
”高伦接受了实公的意见;但是乡里中的人们议论纷纷,都怪实公荐举人不当,可是实公却始终保持沉默。
后来高伦被召做尚书,郡中士大夫,送行到轮氏县傅舍,那时高伦对众人说:“我从前替侯常侍用一个吏,陈君暗地拿了教令还来,另在外边置他的名字,后闻议论者都以此事件来厌恶他。这罪过实因故人,怕着强御而做的,陈君真可称为善事归君,过失归已的了。”此事实公却仍然自己认错,当时每人听到此事叹息不已。从此全国的人民都很佩服他的德行了。
司空黄琼选他去治理繁剧地方的政事,又补任他为闻喜县长职。旬月以后,因丧事不仕。后来再迁官职,转受为太邱县长。在任期间,因他修德行,很清廉,百姓都能安居乐业,地方治安良好,邻县的人民多来归附他,实公常常教诲劝导,以各种譬喻和解说给他们听;发落他们各归本部主官,胥吏恐有争讼的事发生,告诉实君,要想禁止他。
实公说:“争讼不过要想求其曲直,如果禁止了,理由怎的明白呢?不宜拘执呀!”司官听到这句话,叹息地说:“陈君所说如此,难道还会有怨恨他的人么?”也就究竟没有什么争讼的事。后来因相赋敛违法,他便解除了印绶去官,一时吏人们多追念着他。
桓帝时(公元一五零年),宦官专权,密告李膺、陈实、范滂、杜密等人为朋党,那个时候,很多士大夫被捕入狱,禁锢或被杀死者达二百余人。或者有逃遁不获者,皆悬金购缉,因此,余下的人多都逃避;求免其祸,实公却然依旧在家,无意逃避;且对众犬说:“我不入狱,众无所持”,就请官府拘囚了他。
次年,尚书霍谞,校尉窦武等呈表请于桓帝,始准赦归田,惟禁锢终身,永不许出来做官,而诸党人的名字尤刻书于王府。到了灵帝初年(公元一七二年)大将军窦武想请实公出来做属吏。
是时窦将军属下中常侍张让权势强大,当让的父亲逝世时,归葬到颍川郡地方,那个时候,大至一郡之长,都来吊丧;可是在颍川的一般名士,除了实公一人赴致祭外,却没有一个赴吊,此事给张让感觉很以为羞耻的事。
后一班宦官,如曹植等人,又纵使灵帝,复下令大捕党人,连大将军窦武,大臣陈蕃、李膺等百余人都被陷害了;然实公幸得全赦。此事一般人说诛党人时,实公能得宽宥,实得张让感念他为让父吊丧事。不久黄巾贼起,京都震动,灵帝马上召群臣集议,幸帝听从皇甫蒿,吕强二臣之谏,便敕令解消党禁,大赦天下党人。
实公获赦之后,隐居乡间,平心处事,静默潜修,郡中有争讼的事件,往往来求他判辨是非,公总是替其排解,辨别曲直,退去的人,没有一个怨言者;甚且叹息的说:“宁为刑罚加着,不可给陈君说句不是的。”当那个时期,农收荒歉,人民很是俭啬,某夜有一贼进他家里去,躲在屋梁上,实公私下见了,他则起来亲自拂拭,召唤了家里孙子们齐集堂上,于是实公正色地训诫他们说:“做人不可不自己勉励,不善的人,未必生成就是恶的,习惯了,就好像天性一样,所以变成这般下流,像梁上君子,就是这样哩!
”那贼听到这些话,大吃一惊,急自跳下地来,低头认罪,实公慢慢地譬喻给他说:“看你的状貌,并不像恶人,应该有深刻判定自己,回到那善的道路上去;或者许是贫困而造成的吧!”于是命了孙子把两匹绢布送给他去。嗣后,在一县里,再没有盗贼之徒。
太尉杨赐,司徒陈耽等,每拜公卿,群僚们都来道贺,赐等常对众人叹说:“陈实还没有登这大位,而我们实惭愧在他之先。”自党锢解禁后,大将军何进,司徒袁隗等,要想特别推荐他,常遣派使者敦请实公出来担任要职,拟不照常规序次的位置给他,可是他推辞谢来使说:“实久绝人事,饰巾侍终而已!”
当时三公每次集议,有所补缺,多提荐于实;但他始终不愿再登仕途,只是闭着门搁起了车子,隐居游息家园,不管闲事,以终晚年。时孙子们常常争论其父之优劣,咨之祖父,实对众孙说:“元方难兄,季方难弟。”实君尝携子孙聚会,训勉孝和,朝廷史宫屡仰天象,见德星奎聚,因公家积德应天,后来“德星堂”成为陈族宗表。
中平四年(公元一八七年),时实公年届八十有四,是年秋间遭疾而卒于家。临终时且嘱子孙说:留葬死时衣服,薄棺槨,俭丧事,时群僚百官,闻者莫不嗟叹。知名之士,赴吊者,多失声挥泪,大将军何进差使赴祭,赐词以嘉谥曰:“徵士陈君,禀岳渎之精,苞灵之纯,天不慤遗一老,俾屏我王梁,山崩哲萎,于时靡宪,缙绅儒林,论德孝行”。
谥曰:“文范先生”,传曰:“郁郁手文哉!!书曰:“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文为德表,范为士则,存诲没号,不亦宜乎?
出殡之时,各地赴执绋者,有万余人,著哀麻衣者,竟有百多人,皆刻名立碑,以留追念。
公配梁张二氏夫人(有云夫人旬氏),共生男六位。纪、洽、休、光、夔、谌。(有载:长纪,次忧,三洽,四谌,五信,六光)长子纪,字元方,六子谌,字季方,与父兄同德,时人称他三人为“三君”,稍后,在陈文帝天嘉年间。(公元五六零年)追封为“康乐侯”。
至陈宣帝太建年间(公元五六九年)再追封为“颍川侯”。(取材后汉书陈实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