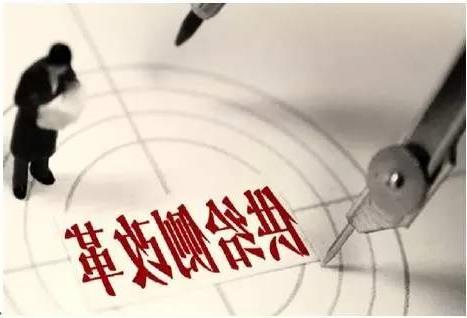李近维的弟弟 东莞30年巨变:前市长李近维郑锦滔的城市史
在李近维主持全县工作期间,他洞悉了这一切,“当时我们实力很弱很小啊,我心里害怕,却不敢告诉别人,不敢生事”。拯救之道,当然在于把东莞经济的总量搞大,使东莞能够升级。东莞升级了,从行政角度看,“纵向可以减少层次,而横向就可以扩大分工,做大自己。别人来吃我们,就不容易了”。
不过,一切仍需用实力来说话。10年后,198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来东莞调研,描述截止于前一年的东莞数据:“1987年与1978年相比:社会总产值增长了5.4倍,达65.8亿元;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5.1倍,达51.
5亿元;国民收入增长了4.3倍,达29.3亿元;出口创汇增长了5.8倍,达2.67亿美元;财政收入增长了2.1倍,达2.02亿元。”更关键的数据在于,“9年中,全市工农业总产值以平均每年22.
3%的速度发展,高于广东省13.5%的速度。特别是1985年以来,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净增7亿元,平均年增长速度37%。”细读这份报告,调查者的明白远远超过后来人的想象,报告论及,“1978年与1987年比较,农村人均收入从193元提高到1039元,大大高于广东省全省的人均645元的水平……据我们了解,东莞市的人均收入,特别是农民的收入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如茶山镇对塘村1987年统计人均分配为1372元,而仅水果一项人均收入就达1185元,其他各业的收入肯定不止187元。其他地方大体上也是这个情况”。
如此实力,1987年东莞再次申请升级为地级市,很快,次年1月国务院即予批复同意。
如果对比1985年东莞撤县设市,这次升格为地级市的东莞,仍是原来东莞的面积范围,也没有设县,只是由原来县管镇变为市管镇。这是李近维梦寐以求并努力争取的格局。
对于东莞市管镇的格局,有着缜密而战略性思考的李近维,当然不会不考虑真正升级后的东莞市构造一个什么样的组织结构。“我们总是说精兵简政,减机构减人数,为什么越减越多呢?”这是李近维的思考的起点,“其实做减法,远不如先做加法稳妥。
加法是,干部人数不变,把产值与规模做上去,按产值与人头来比较,机关人员也算是精简了。”这是做足增量的思路,东莞10年已经实施李的这一增量思路,问题是他如何说服上面,不设县而而改为市管镇的建制呢。
1987年9月,李近维在中央党校干部进修班学习,这是一个时间机会。李近维形象的故事讲述的是邻县惠阳县,“以前东莞和惠阳差不多,但后来,惠阳先是分出一个惠东县,又分出一个县级的惠州市,最后还分出一个大亚湾开发区。
结果在同一块土地上,4个县级的4套班子,而这又是个指挥层,并不是直接生产财富。这好比同一块草地,草再肥,也经不起4群牛来吃啊。我们东莞如果在市与镇之间设几个县或县级区,地还是这块地,按当时的财力就难以经得起那么多‘牛’吃了”。
原东莞市政协主席袁李松后来讲述一份数据,或许是更能阐述李近维的思路:全国由财政供给的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平均28人供养一个,广东省为26人,而东莞如果保持格局不变,则为68人供养一个。这尚未计算庞大的外来人口。最终东莞没有设县,市管镇保留至今。
这一组织框架背后的政治理性,当然比“精兵简政”的说辞要复杂。一般而言,升格为地级市之后,相应的各种权力当会扩大,比如投资审批额度,批地额度等等,这些当然是东莞快速发展的必须条件。但核心的问题非此,而是市镇组织框架之下的权力安排。
研究这一框架,我们又必须回到东莞起步时期的路径选择:“三来一补”与人盯人的资源争夺的制度安排。“所谓权力,核心是可支配的财力。”李近维当然对此深思熟虑,“治国本于理财。总理理一国之财,省长理一省之财……问题是,镇长是否也应理一镇之财,村主任是否也要理一村之财呢?三来一补把各镇各村甚至农民个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但如果你不给他财权,这种积极性能否维持呢?财富的生产与分配,其间的权力安排才是关键。
1984年,在我提出向农村工业化进军之时,就相应提出建立‘五级财政’,县、镇、村、生产队以及个人。这一体系的建立,我的原则是:统一开源、分级截流、以丰补歉、减少劫富济贫。谁赚钱谁花钱。
相反高度集中权力,就可能高度集中矛盾;高度集中财力,就会高度集中困难。”如此理念,显然李近维的权力制度安排是分权制的——它带来的东莞高速发展,结果已经彰显。升级后的东莞获得的权力与权力再分配,只是技术性问题。但这一财富的生产与分配制度仍没有解释市镇结构,为什么中间不设县治。
或者政治的本质在此方得显现,当各级财政相应建立之后,上下控制如何产生?站在地级市市委书记的位置,这是关键之处,“在现有人事制度结构里,如果设县治这一层级,那么县级领导的人事任免,权力在省里;而镇级干部的任免权却又在县里,市里两不靠。市镇结构,镇级人事安排全在市里。市里既已让渡财权,如果没有人事上的控制,岂不容易失控?”市镇结构安排的政治智慧在此。不过,这种的制度安排,李近维强调,“市委书记必须公道正派人,权力实在够大了”。
很幸运的是,东莞完成由县升地级市后,李近维由东莞市委书记的位置调任惠州市市长之位,先前东莞县委书记欧阳德回来任市委书记,欧阳德对东莞的情况非常熟悉,而且他又是李近维的老领导、老师傅,思路基本一致。李近维给后任留下了一个可以保持财富快速生产的制度安排,未来的东莞已有根基。
城市化
江西吉安女孩汪雪英1987年来东莞时,还不知道广东在哪里。她是被广东正式组织招工来到东莞的。对于农村孩子,广东招工差不多算得上“特大喜讯”,一时间报名者甚多,结果吉安县不得不限制名额,有高中文凭的可以免试录取,初中的要参加笔试。
参加笔试也有名额控制,汪雪英的村子因为比较大,所以有两个名额,“可是村里报名的有6男6女,最后只能通过抓阄选择一男一女参加考试”,结果汪雪英抓到了。现在坐在我对面,汪雪英跟一般城市白领区别不大。
很难想象当时广东对他们的强烈吸引力,反复限制报名资格后,参加考试的还有6000人,最后仅录取了2000人。汪雪英被录取了,终于她爸爸觉得她将会成为一个城市人。到了东莞,汪雪英发现,这里到处都在招工,第三天她就和几个女孩“跳槽”到常平镇的一家玩具厂。
第一个月挣了83块,第二个月就有158块,到第三个月涨到180块了。电视剧《外来妹》的编剧谢丽虹向我回忆1989年在东莞体验生活的意外,“采访打工妹时,她们一定要请我吃饭,那时我一个月工资120块,人家已经达到200多块了”。汪雪英再回家,她村子里的那些同伴们一个个跟着她到了东莞。
中共中央办公厅那份调研报告描述那年的东莞,“吸收了全市劳动力15万人,外地劳动力17万多人”——在吉安汪雪英来到东莞这年,东莞的外来劳动力由本省其他地方开始扩大到外省;而同时,也在这一年,外地劳动力开始超过本地劳动力。
这是一个重要时刻,当东莞真正像自己所希望那样成为一座城市之际,解决本地劳动力过剩的任务开始转折,进入到为全国其他省市提供就业岗位。认真研究东莞市统计局所发表的历年来人口统计数据,1987年也确实是一个转折点,当外地劳动力首次超过本地之后,每年以超过10万人的数量新增外来劳动力;10年后的1998年,东莞外来劳动力达到199.1万人,首次超过本地户籍人口数量(148.8万人),之后,以每年新增50万人的速度增加。东莞接纳外来劳动力的能力似乎没有尽头。
土地与劳动力,在由多种种植转向工业制造业之后,两者的函数关系不再简单。刚刚成为真正意义上城市的东莞,马上面临城市化的全方位压力。
与外来打工者急速提升对应,1989年,台湾IT业投资者叶宏灯选址石碣,开办他的东聚电业公司,从25人开始起步,13年后发展到拥有10家工厂、1.2万名员工,并将自己生产的鼠标产量排进世界第二,电源保护器与扫描仪的产量占据世界第一。叶的高速发展当然可以对应东莞对劳动力的广泛而大量吸纳,但数量上的跃进,带来的是结构上的根本性变化。
1994年,李近维从惠州市市长之位又回到东莞,出任市委书记兼市长。东莞的社会总产值已由1988年他离开时的96.68亿元,跃升至1993年的288.17亿元。随后,李近维发布他的发展纲领,“第二次工业革命”——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科技社会。这一口号当然响亮,但是李近维过去的同事有些疑惑,“李书记怎么从惠州回来后有点保守了?”李近维最初的举措不是“发展”而是整肃,每个村每个镇开始清产核资。5年后,在东莞市第十次党代会的报告里,李近维描述说,“过去,我们基本是靠举债建设,自有资金甚少,每增加100万元的资产,就得增加70万~80万元债务”。这其间的关键是,东莞不是发展慢了,而是快了,太快了。一旦如此快速起来,负债自然陡升。“这不仅是东莞的现象,全国都这样,我在惠州时就考虑好了要压一压,但调回了东莞,在这里先来压实基础。”李近维解释说。
在那些打工者、投资者云集东莞的背后,当时东莞各级政府为了应对快速发展,借贷之外,还向老百姓大量集资,年息到18%甚至更高。“当时香港商人很精明啊,他们知道我们这里是年息18%,就商量愿意一次性把修公路的钱给我们,同时反包给我们,要求我们按年息17%给予他们20年回报。
大家来找我,问我干不干,毕竟可以一次性拿到钱,而且还低一个百分点的利息。我告诉他们,坚决不干。而且还要赶紧把那18%年息的集资还回去。
”李近维向记者解释当年为什么跟壳牌谈判谈了那么久,很简单,其中有一点对方要求每年12%的回报,希望在政策上给予优惠,但我们要求他必须从技术上解决,谈了又谈。结果回来发现,我们自己给别人的集资款利息有这么高。
“我的秘书问我,为什么不要港商的钱呢?在那个年代,其实大家当时都是头脑发热的。我问秘书:你想不想当个百万富翁啊?他很奇怪我为什么会这样问他。我说,如果你想,那么你找5万块钱来,去参股买公路,每年的利息再投进去,如果这样利滚利20年,你最后的收益是本钱的22倍。
你再算一下,你是不是百万富翁了?”李近维早已算清楚了这笔账,他当然坚决拒绝。城市发展的陷阱,远比想象得多,一不小心,便会一脚踏空。“对于东莞发展而言,我们有的核心资源就是土地,如果别人的钱还不上,自然就会把土地拿出来抵给人家,未来哪里还有空间。”土地与劳动力两个变量,在这个时刻已经被李近维意识到其间所蕴含的风险。
说到这里,李近维脱下鞋,蹲上了他所坐的沙发边缘。“我当时就这样告诉我的干部们,这样蹲着,蹲到边边也不害怕,为什么?因为离地近,即使跌倒也不会有大问题,但如果蹲到十几层楼那么高,又没有墙壁和栏杆挡着,你敢蹲到那么边吗?我们必须注意负债量和负债率的关系,经济起步时,我们资金短缺,负债量也少,借点钱启动经济是非常必要的。
现在我们已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又用了那么多土地,应该更多的通过增加积累进行建设。负债量那么大,但有些地方还盲目举债,高利息集资,管理也不到位,这就像蹲到十几层楼那么高的边边,又没有栏杆挡着一样了,我们能不担心吗?”债务的背后关系到土地的消耗,要控制土地消耗,必须防止乱举债。
乱举债的人盯着的就是农民的土地,用农民的土地换取他一时的所谓政绩,必须从防止乱举债做起,才能防止到偿还时带来乱卖地。
在李近维“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报告里,更为重要的内容是,“以1980年为基数,改变耕地用途已超过一半的、或人均已达到150平方米的,除国家建设需要外,原则上不能再占耕地,促使其向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同时,严格执行用地审批程序,对未经批准随意改变耕地用途或买卖土地的,坚决依法严肃处理”。
当年发现种植经济作物即可使土地升值的李近维,现在“保守”了,决定坚决控制土地数量。这是1995年的决定,如果按此时间推导,对土地价值的洞见及其警惕,李近维当然超前同辈。李近维所意识到的问题,后来亦有数据给予印证。由陈桂明2005年编辑出版的《持续发展的动力——东莞工业产业升级之路》里描述:“东莞生产总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要消耗1200亩左右的土地……全市可利用的土地资源已十分有限,实际可利用的土地只有40万亩左右,如果继续按照现在的土地消耗速度,10年时间全市的土地资源将消耗殆尽。”转变增长方式,势在必然。
解决债务的招法也很有趣。李近维先摸底找出两个高负债的典型,万江街办与市二轻局,让市里各级干部、各部门负责人还有镇委书记与镇长用一个月时间去调查本来很富裕的万江街办为什么负债率会高达146%,大家一起会诊,分别写出报告;会诊后,各镇各单位对照万江回去自查,然后再写出分析自己情况的报告交市委。之后,就是由东莞市统计局进行全面的统计调查工作,各项数据分门别类列陈。现在东莞市统计局局长吕崎元是当年调查统计的负责人,他告诉我,当年的主要任务就是调查资产负债率,土地存量也是调查里的一部分。后来我们去李近维过去的办公室,李近维很迅速找出了当年清产核资的调查数据,12大册统计表,细致到每个村庄,这一统计项目自此保留下来,延续至今。李近维现在仍很得意当年的统计调查,“我摸清了东莞的家底”。吕崎元对李的这项举措的理解是:在分权结构之下,摸清家底才是实施有效监管的关键所在。这其间自然包含着治理的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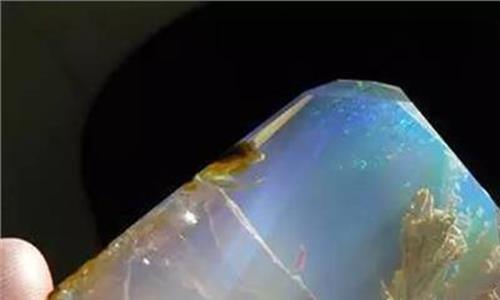







![>汉中市李九红 汉中市常务副市长李九红带队检查消防安全[图]](https://pic.bilezu.com/upload/3/16/31677c7f68dc4b1108c50dc712619901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