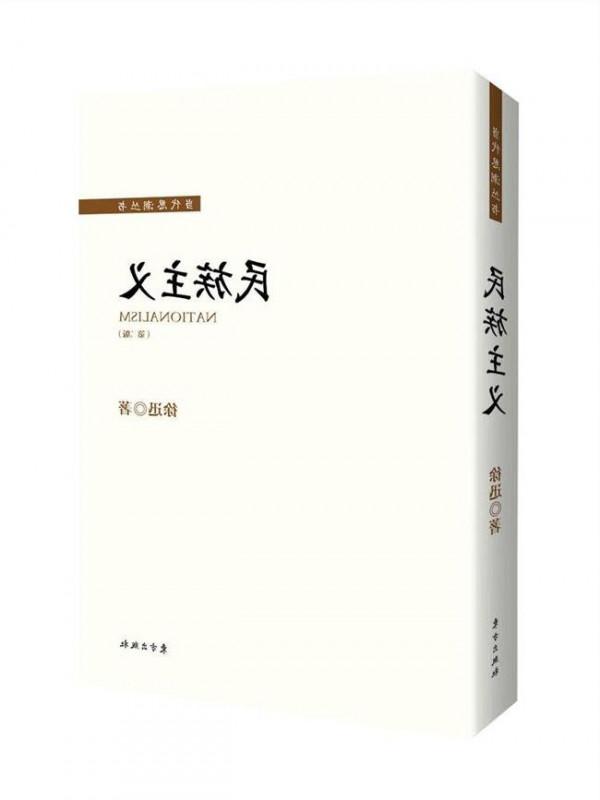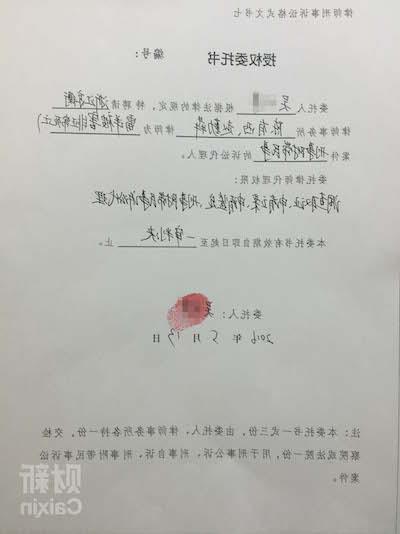雷颐警惕法西斯 雷颐:法西斯主义的形成与终结
“二二六事件”虽被镇压,但加强了军部在政府中发言的力量,而且舆论一边倒地支持这些法西斯青年军官。参加政变的士兵在重返原来部队时,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
当然,除了这些较为直接的社会现实原因以外,法西斯之所以能如此长时间且如此强烈地吸引如此多的人,还在于它精心构造了一个颇为完备的关于民族特性、民族文化优越最终导致种族优越论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
这种理论制造了有关历史、民族和国家的种种神话。德国法西斯主义声称世界历史中只有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是高贵的(在纳粹语言中雅利安人有时指非犹太血统的白种人,更多是单指日耳曼人),其中日耳曼人又最高贵,世界历史是由雅利安人创造的,人类的科学文化都是由日耳曼人创造的。
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优劣种族间血统对血统、种族对种族的斗争史,当代日耳曼人是最优秀的人种,是被上苍赋予“主宰权力”的高等民族,理所当然地“应该主宰世界”。
这种种族主义成为纳粹民族主义的核心和基础,但反过来又可说,民族主义又是种族主义的温床和基础,极易导致种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这种民族/种族主义具有强大的煽动性,激发起一种热血沸腾的英雄主义浪漫情怀。
但是,在这种“英雄浪漫”之下,可能“还有一种更深、更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这种动物身上暗藏的无意识的原始欲望和本能翻腾到表面上,那就是弗洛伊德深刻看到的、被他称为‘对文化的厌恶’,即要求冲破这个有法律、有条文的正常世界,要求放纵最古老的嗜血本能。
也许这种暗中的力量也参与到飘飘然的感觉之中。热烈的陶醉混杂着各种东西:牺牲精神和酒精;冒险的乐趣和纯粹的信仰;投笔从戎和爱国主义言辞的古老魅力。那种可怕的、几乎难以用言辞形容的、使千百万人忘乎所以的情绪,霎时间为我们那个时代的最大犯罪行为起了推波助澜、如虎添翼的作用”。
要反对这种燃烧的激情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谁表示怀疑,谁就妨碍了他们的爱国主义事业,谁提出警告,他们就嘲笑他是悲观主义者,谁反对战争——反正他们自己在战争中不会受苦——谁就会被打成叛徒。
时代几经变迁,但总是这一帮子人,他们把谨慎的人称为胆小鬼,把有人性的人称为软弱的人”。(《昨日的世界》,第 252、281页)
为了对外扩张,他们还制造出了与种族理论紧密相关的“生存空间”理论。这种理论竭力论证弱小种族没有独立生存的权力,因而空间多余,其领土可由强者任意宰割。相反,一个强大、“优秀”的民族必须拥有足够的空间才能生存下去,所以强者拥有剥夺弱者空间的自然权利。
一本名为《德意志民族及其生存空间》的读物成为纳粹思想入门的基本教材,“为德意志夺取生存空间”成为最富煽动性的口号之一。“夺取生存空间”这一非常抽象、“中立”的概念,的确很容易掩盖血淋淋的侵略实质。
“这一事例清楚说明:一种简洁而又内容丰富的表述由于言辞的内在力量可以转化为行动和灾难,就像先前的百科全书派关于‘理性’统治的表述一样,最终却走向自己的反面,蜕变为恐怖和群众的感情冲动。”(同上书,第211页)
“以施本格勒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思潮是纳粹主义兴起的直接背景之一,被认为是法西斯的直接先驱和同路人。”(《法西斯新论》,第249页)“一战”后欧洲兴起的这种“新保守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反对自由主义、法国大革命及民主制度,主张以强权、扩张、民族(国家)社会主义等方式来解决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施本格勒的成名作《西方的没落》影响巨大,其基本理论是把“文化的生命周期”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将一切都归结为直觉和体验,并上承尼采的“超人”哲学,认定历史由“超人”创造,所以可以主宰一切。
由这种“超人”哲学出发,纳粹意识形态对自由精神和民主政治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认为民主制是一种照顾迁就庸众的软弱的制度,只有领袖独裁才是真正强者的制度。
因此早在还未掌权时,纳粹就公开声明要破坏民主制度。希特勒毫无顾忌地说:“我是民主的死敌”,“共和制度和历届政府毁灭了德国的一切,这种制度最终被消灭的时刻到了。”戈培尔凶狠地咆哮:“我们进入国会,是为了在民主武器库中用它所具有的武装为我们自己服务。
我们将要成为国会议员,以便用魏玛民主的支柱去瓦解魏玛民主。如果民主那么愚蠢,竟为了这种给人帮倒忙的差使给我们发免费车票和津贴,那是它自己的事,……我们是作为敌人而来的!
如狼冲入了羊群,我们就是这样来到了。”(同上书,第211、275页)这段话倒是说中了民主政治的困境和软弱的根源:作为民主制度,独裁者也享有民主的权利;倘不给独裁者以民主,那就违背了民主原则。因此,在民主政治中,每个人都应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
对自由、民主的批判必然导致个人独裁,“领袖原则”是纳粹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的极权主义便是以领袖或“领袖原则”为指导的。这种领袖是绝对正确的神和圣人,不仅是政治的、行政的领导,而且是信仰、道德精神世界和世俗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导师,不仅是国家、民族的唯一代表和化身,而且高于国家和民族,领袖意志便是最高法律,所以领袖的各种权力是无限的,有权干预、监管任何组织和个人的任何事情,而绝不允许对领袖有任何反对、批评、不满甚或怀疑。
“谁要是在德国参加过有希特勒在场的集会,都不会忘记他所能唤起的那种感情,那种宗教狂热与虔诚的气氛。他的那种吸引力后来竟使得久经沙场的将军在他面前发抖。”(《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第254页)
由于与中国关系密切,日本的法西斯理论更值得仔细分析。日本从明治维新起逐渐走上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从侵占朝鲜、中国台湾和东北,最终发展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与此相应,在这大半个世纪里,日本也发展出了一套相当“深厚”的侵略理论。的确,如果没有这样一套理论做基础,它的侵略扩张不可能得到几乎是举国一致的长期支持,因而也难以持久,更难不断扩大。
明治维新以后,随着对外侵略的野心不断膨胀,走上对外侵略、对内专制的军国主义道路,与之相应的是出现了种种支持侵略和专制的理论。首先出现的是“脱亚论”。这种理论认为日本只有学习西方脱离亚洲才能强盛,就国内改革而言,“脱亚论”有进步意义。
但“脱亚论”立即成为支持对外侵略的种族主义理论。有人提出:“现在随着我大日本帝国之开化进步,已经超过了顽愚的支那,凌驾于固陋的朝鲜,不仅如此,这也是我国藐视支鲜两国,自诩为东洋霸主的资本。
”连日本进步思想家福泽谕吉也认为“朝鲜、中国还未‘开化’,即将为欧美所亡,所以日本不可再犹豫踌躇、坐等邻国之文明开化而与之共同振兴亚洲,毋宁应脱离其行列,去与西方文明诸国共进退。我国对待支那、朝鲜之法,无须因其为邻国而有所顾忌,只有按照西方人对待彼等之方式方法加以处理”。这种理论成为明治政府制定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理论依据。
但是,随着日本的逐渐强大,特别是日俄战争后,日本战胜了欧洲国家俄国,民族自信空前高涨,“归亚论”渐有市场。从20世纪20年代起,“归亚”成为主流。所谓“归亚”,即是说日本与亚洲尤其是东亚诸国“同文同种”,要实行“亚洲的门罗主义”,由日本充当亚洲各国的领导者和保护人。
早在1888年,《日本人》杂志发表一篇名为《保存国粹要旨》的文章,提出日本历史、文化等都有自己的特殊性,要发扬日本国民优良的素质。国粹论,提出日本民族中心论,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和排外性,成为日本早期的右翼团体最重要的思想基础。进一步说,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最早的思想资源之一是“国粹主义”。
概括地说,所谓“归亚”理论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诉求,它把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说成是促进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提出发动这次战争是为了使有色人种从白种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不仅是求日本的发展,而且要救济和解放东亚被压迫民族,为了誓死抵抗西欧帝国主义的压迫,不得不进入大陆,中国人应理解这些事情。
提出亚洲其他国家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已无力保护自己,所以要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防卫体制,宣传是日本长期以来以自己独自的力量,反抗着欧美帝国主义对东亚的压迫,正因为有了日本,才避免东亚完全成为欧美的殖民地。
这样,亚洲各国的抗日运动其实都是被白人误导,反成了欧美和苏联白人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则分别是英美和苏联的代理人。
这种理论认为,中国民族运动基于凡尔赛和莫斯科制的民族理论,企图获得民族独立和自由,是非常危险的,反给白人以可乘之机。因此,亚洲诸民族应追随日本反对欧美帝国主义的各种势力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
在经济方面,这种理论十分狡猾地批判西方对东亚的经济剥削、谴责西方列强对东方实行殖民经济,用数据说明欧美帝国主义一方面破坏东方固有的经济,将近代企业置于它们的统治之下,同时又维持有利于自己的封建经济,榨取东亚的勤劳大众。
东方诸国的经济除日“满”两国外,都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经济,其经济命脉完全被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帝国主义操纵,欧美帝国主义全面支配着东方经济。所以日本的经济政策是要引导中国经济从次殖民地状况下解放出来;亚洲各国只有与日本经济一体,才能摆脱欧美的经济殖民。
在文化方面,日本法西斯理论除了强调日本本土文化,还十分强调东亚的儒家文化,认为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来自欧美的“文化殖民”,破坏了东方固有文化。它尤其强调东西方文化有本质差异,反复论证西方文化是儒家所批判的霸道文化,东方文化是儒家理想的王道文化。
在不远的将来,东西方文化将发生最后冲突,决定是霸道还是王道统治世界。现在,只有日本是东方文化的代表,是王道的化身,而王道不仅事关日本的繁荣,而且事关世界的发展,实现王道是日本民族的光荣使命,所以以日本为代表的东方王道文明应主宰世界、拯救全人类,在日本的领导下为万世开太平。总之,这是日本为建立“王道乐土”而进行的“大东亚圣战”。
在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现代世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无疑具有极强的煽动性,因此这套话语系统无疑具有异乎寻常的“魅力”,使当时日本大多数国民都如饮狂泉,认为自己国家进行的是场正义的“圣战”,愿意为之奉献、牺牲自己的一切,心甘情愿地充当侵略者的炮灰。
确实,抽象地提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经济文化殖民,强调东方文化有自己的特点,东方文化复兴论等,很难说不对。但唯其如此,日本的法西斯理论就具有更强的迷惑性,使人更难认清这种理论制造者背后的真实面目。而这些冠冕堂皇的“反殖”“反帝”理论就这样为另一种更野蛮、更凶残的殖民主义所利用。
理论与现实的关系之复杂,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事实说明,如果抽掉或无视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历史内容和时代背景,如果抹去日本侵略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造成的巨大灾难,而仅仅做一种“纯文本”阐释,即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以“后理论”证“前理论”,以“新概念”证“旧概念”,以“今文本”证“昔文本”,找出二者的某些类似,那么,我们今日很可以拿时下颇为流行的“反对跨国资本”“反全球化”、东方文化可“为万世开太平”等各种理论来论证、诠释当年日本进行“大东亚圣战”的合理性和正义性。
同时,很可以得出当年亚洲各国人民对日浴血抗战竟是“维护白种强势文明对黄种弱势文明殖民统治”、是“依存英美之错觉抗日排日之谬误”的结论!
因此,对各种话语,万勿仅据其自我表白便轻做判断,它的言辞其实并不重要,关键在于要洞察它是由谁掌握、针对什么、又是如何被运用的。
公平、公正、社会正义,无疑应该是社会追求的基本目标,也是人性的基本要求。法西斯主义深谙此点,因此如前所述,德国、日本的法西斯理论十分注重以“社会主义的工人语言”、以反对“国际资本”、以为平民大众争“平等”……种种宏伟言辞来吸引大众。
事实证明,这种宏伟言辞很容易成为野心家的工具,他们往往凭此被当成人民的化身,当成“平等”的分配和保障者,而实际上成为至高无上、权力不受任何监督制约、为所欲为的独裁者。当社会动荡不定、政治严重腐败、权势者不择手段化公为私、社会分配极度不公时,法西斯主义的这种宣传、理论对大众确实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对政治腐败、社会不公的痛恨,确实使人一时难看清法西斯思潮的真面目,难以认识到它将造成更大的灾难。
因此,对这种无比完美崇高,却能深深打动人心的宏伟理论一定要高度警惕。
当然,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会有形形色色极端思潮的产生与存在。在承平时期,在健康的社会中,种种极端思想只能蛰居一隅,始终是无足轻重的配角。而在社会利益进行调整的转型期或社会危机严重时,这类思想却使人如饮狂泉,往往能突然掀起最终毁灭一切的狂风巨浪。进一步说,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对权力进行制衡的政治制度,任权势者无止无尽地化公为私,分配不公急遽加大,公民权利不获保障,恰为种种极端思想提供现实的社会基础。
概言之,强烈的民族主义、狂热的国家社会主义、对强权政治的鼓吹、对个人的彻底否定、对暴力的热烈颂扬、对伟人/强人的崇拜迷恋,是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特点。只要一有条件,它将一跃成为令人望而生畏的力量。
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使经济刚刚开始好转的德国再次堕入深渊,为法西斯最后夺取政权提供了现实条件。1933年1月30日晚上,希特勒通过合法程序组成纳粹政府的消息传出,举国若狂,全德大小城镇都举行了规模盛大、通宵达旦的火炬游行,人们向希特勒热烈欢呼,以为找到了德意志的拯救者,找到了反抗以英美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压迫的英雄,找到了“公正”的庇护神。
直到十几年后,德国人民才意识到自己当时犯下了灾难性的错误,但为此已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当日本民众支持诸如“血盟团”、青年法西斯军官以血腥、恐怖的手段来切除腐败的社会毒瘤时,确实难以意识到,他们正在把日本推向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