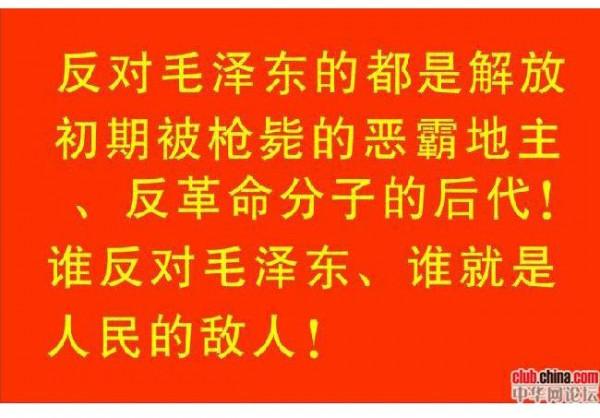杨奎松毛泽东 党史学者杨奎松:毛泽东是如何发现大饥荒的 ?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毛泽东又打算如何去改变粮食紧张的现状呢?以往的党史、国史著述,大都很重视庐山会议的转向问题。即认为会议原本是要反左的,彭德怀7月14日一封上书,批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惹恼了毛泽东,会议于是从反左一下子转到反右去了。而这个说法,也是毛泽东事后自己多次讲过的。
然而,如果我们注意到庐山会议上从始至终毛泽东都没弄清发生问题的根子在哪,那么,说彭德怀不上书,会议就能形成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就会一直坚持反左,也不那么可信。事实上,研究一下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前段提出的解决粮食问题的意见,就可以印证这一判断。
7月5日,毛泽东结合粮食部部长陈国栋的报告,就粮食问题专门提出了他的建议,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假定今年年成确实比去年好的情况之下,还要多征购一点粮食,以备危急时国家手里有粮。二、下年度销售计划应该大力压缩,向1957年看齐。1957年大家不是过得挺好吗?“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可多收,可以多吃”。四、“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
从上述三、四两点可知,毛泽东是注意到了公社化导致农民日常生活受困的一些问题的,也提出了一些有助于解决农民饥荒问题的办法。但是,他的前提却还是“食堂吃饭”。“食堂吃饭”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农民还是不能自己开伙,意味着毛泽东还是希望坚持对农民实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意味着农民还必须要过集体生活,自家的东西不能归自己所有,自家的房子多半也不能自己住。农民在连基本的家庭生活都不易维持的情况下,又如何去经营自留地、私人菜园、田头地角?如何能节约归己、自种自吃呢?
至于一、二两点,就是要求“多购少销”。“多购少销”是中共中央自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以来的一贯方针,但是,在粮食供应已经开始与民众生活需要严重脱节,许多地方已经出现严重断粮并开始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明确提出这一要求,一旦确定下来,岂不会带来更严重的灾难性的后果吗?毛泽东所以看不到这一点,显然是因为他并不清楚粮食问题的危险程度。他的信心和数据依旧是从主管经济和粮食工作的负责人那里来的。他所以要在全会上专门就粮食问题发表这几点意见,原因也就在于多数省份的领导人都在喊粮食困难,要求中央减少1959年度的粮食征购数量,放宽1959年度的粮食销售额度。而中共中央主管经济、财政、粮食工作的负责人和地方领导人之间已经出现顶牛现象,他出面要求其实是帮中央做说服各地领导人思想工作的。
毛泽东的依据是:一、1958年就算粮食总产量只有5000亿斤,也还是比1957年增产了35%,实现了“大跃进”。如果照谭震林等人报告的情况,1959年虽然播种面积有减少,但年成肯定比1958年还好,亩产还要高,产粮总数不会低于1958年,那么,为什么不可以仍旧比照1958年,征购到1100亿斤呢?二、1957年全国只销了839亿斤,没有出任何问题,1959年为什么不可以向1957年839亿斤的销售量看齐,甚至再低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800亿斤,或者810、820亿(斤)呢?”扣除军粮、出口和养猪饲料120亿斤,这一进一出之间,中央和各地不就可以净储备160亿斤,以弥补现有300多亿斤库存的不足了吗?
显而易见的是,靠听汇报了解全局的毛泽东这时不仅不了解全国粮食问题的实际状况,而且不了解1958年工业、水利“大跃进”所造成的城乡人口结构的改变,带来粮食供需关系极大改变的情况。他只注意到1958年度粮食销售了1018亿斤,超出1957年度839亿斤太多,却没有想到城乡工业“大跃进”和大搞水利建设后,城市人口一下子增加了2000万,农村企业和兴修水利也使相当一部分农民转去吃商品粮了。
光新增2000万城市人口,就需要差不多100亿斤以米、面为主,不含地瓜干的粮食。
再加上全国上亿农民被投入到大型水利建设工程中去,所需商品粮数量十分巨大。只要保持现有人口结构不变,继续各项“跃进”政策,1959年度的粮食销售量根本就不可能低于1958年度的水平。
粮食部最初也是按此水平计划的,原定1959年度的销售额为1020亿斤。但是毛泽东会上一提出质疑,粮食部马上就动摇了,改调到855亿斤。对这个数字,毛泽东却还是觉得多,总觉得应该可以“和1957年看齐”,即所谓1957年大家不是过得挺好吗?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不是很了解城乡人口结构的这一变化情况,至少对这方面问题不敏感。中共中央负责经济、农村和粮食工作的领导人则不然,他们早就谈到过这方面的情况。可是,他们这个时候也没有意识到需要从这个方面着手来解决问题。相反,他们从缓解自身主管的国家粮食储备紧张的角度,马上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不仅如此,对毛泽东所提恢复社员自留地,自种自吃、免征公粮的意见,他们还表示不同意,认为对国家粮食利益影响太大。李先念就特别提醒毛说:“按照自留地占耕地面积5%计算,全国约减征23亿斤细粮,折人民币2亿元左右。我建议,免征的这部分公粮,可以暂时转由公社或者基本核算单位交纳,执行一年再看。”
上述这一切讨论和决策,都发生在庐山会议初期,即彭德怀上书的7月14日之前。事实上,彭德怀也一样不清楚1958年度粮食的实际产量,更不了解当时粮食问题的严重程度,他同样认为“粮棉增产30%是肯定的”。换言之,7月14日之后,毛泽东虽然因彭信转而发动批右,会议对粮食问题的看法以及毛泽东在会议前期所拟解决问题的方案,其实并未改变。
7月31日,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制定了下一年度粮食征购和销售的指标,计划总产量5000亿斤,购1100亿斤,在征购量与上年度基本持平的情况下,却较上年度减少了近1/4的销售额,确定为820亿斤。加上增拨国家生猪生产基地饲料20亿斤,即840亿斤。这一数字基本与1957年839亿斤持平。而且,计划中粮食出口还有所增加,即由1958年的82亿斤,变成了100亿斤。
粮食部部长陈国栋在解释这一方案的报告中称:按照这一购销计划,并不会减少农民的口粮,相反,较1955年所定的417斤的标准还有增加,全国农民年平均每人留有口粮可到440斤,约相当于330斤成品粮,平均到每天每人可以有9两粮食吃。“如果在有瓜菜的季节里,掺食一些瓜菜,并有计划地加工一些干菜,储备起来,和粮混着吃,不但可以吃得饱,而且可以吃得好。”
从陈国栋的上述算法和介绍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即使是粮食部部长本人也不了解,农民实际到手的口粮数是不能这样在纸面上平均推算出来的。除了种子粮、饲料粮未算外,光是一个公社化带来的县社提留的所谓公积金、公益金及各种机动粮,就从中截去了农民大量的口粮数。
毛泽东年初在郑州会议上就尖锐批评过公社一级“积累太多”,什么都“共产”,“实际是抢产”。他举的例子是河南,说河南除国家征税7%以外,县社一级从生产队的总收入中抽去的“积累”就占26%,生产消耗至少20%,还要收百分之几的公益金、管理费,如果再算上20%以上的统购数……农民年平均口粮数最多也只有两三百斤原粮,根本不可能达到440斤原粮的水平。
如果我们注意到柯庆施介绍的情况,就更能了解纸面上的计算有多不靠谱了。他讲,华东各省社队两级干部为工作便利,甚至为自身谋利,存在大量提留机动粮的情况。据江苏镇江9个公社15个大队调查,社员每人每年负担机动粮达31斤。有的大队为此不惜克扣社员口粮,本来每人年应得基本口粮只有226斤,竟被克扣去80斤,致社员实际到手只有146斤。
随后的情况也很快证明了粮食部的算法完全脱离实际。由于各地粮食已经非常紧张,根本不可能照人均440斤原粮水平给农民留口粮。在无法抗拒中央征购任务的情况下,各地不久即纷纷要求压缩农民口粮以满足征购所需,中央对此也只能迁就同意。一个多月后,即9月17日,中央正式批转甘肃省委关于粮食工作的报告给各地,同意“农村一般每人全年平均留原粮400斤上下,最低不少于365斤”。这意味着,农民即使能够按照官定的标准拿到全部口粮,每人每天也只能吃到七八两粮食(此处指成品粮,原粮转化为成品粮的比率一般为70%~80%)。不要说农民每天所得的这七八两粮食相当部分是杂粮,不仅包括豆子在内,还有不少地瓜干。就是这些并不完全顶数的粮食,多半也还会因为各种中间过程的损耗和上述各种克扣、贪污而大打折扣。许多地方农民一天只能吃到四五两粮食,甚至更少,严重断粮乃至广泛饥荒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可
知,在1959年粮食问题已经相当严峻的情况下,无论庐山会议批左还是批右,只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及其症结所在,继续坚持制定并实行“多征少销”的方针,就必然会加剧饥荒大面积的扩散与发展。
反右倾创造出的虚假成绩
庐山会议转而批右,使得从中央到地方,大批试图向中央反映基层严重问题的干部成批成批地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严厉处罚。湖南80多个县,有30多个县委第一书记挨整。河南信阳地区16个县的县委第一书记被撤职。山东聊城一个地区,2万多干部被批判或定性右倾,并且批斗了数万名群众。由此带来了两个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是各级干部吓破了胆,只能更加不顾一切地采用各种强力措施向农民催逼征粮;二是虚假信息更加盛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看到的情况与实际愈加脱节和扭曲了。
因为各地干部尽心竭力地为完成中央交付的“多征少销”指标而努力,1959年秋冬到1960年年初,国家购销指标完成得异乎寻常的好。粮食部为此极为兴奋,在1960年1月26日粮食部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中,上来第一句话就是:“当前粮食局势好得很。”
据粮食部报告称,按照1959年度(即从1959年7月到1960年6月)的征购计划,不过半年时间,即到1959年12月25日,就已经完成了94%。加上1960年5至6月份将征购到的新夏粮,肯定会超额完成计划。粮食销售计划的执行也十分稳定,1959年7月至12月仅销售了401亿斤,比1958年同期减少了42亿斤。同样,粮食出口供应计划也顺利完成,而且超额。报告说:“从以上情况来看,多购少销,争取粮食工业变被动为主动……已经做到了。”受此鼓舞,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更明确提出,要争取国家粮食库存(包括周转粮在内)到1962年时,能够达到1000亿斤。李先念也提出,有必要争取使粮食总产量到1962年达到7500至8000亿斤。
据此,中共中央于1月30日正式批准了国家计委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其中粮食一项的目标被规定为6000亿斤,比1959年要增长11%。中共中央相信,1959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了5400亿斤,比1958年增长了8%,因此1960年粮食产量理应争取更进一步的增长。
这个时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不是完全没有渠道发现问题。像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就还在零星地反映报道一些比较真实的基层情况。比如它在年初一段时间里就接连反映了江苏、甘肃、湖北、宁夏、贵州等地出现农民断粮逃荒、浮肿干瘦、非正常死亡、弃婴死婴、妇女子宫脱落,乃至于人吃人等情况。但是,和1959年上半年毛泽东高度评价《内部参考》刊登农村实情的消息,并几度批示的情况不同,1960年上半年毛泽东对《内部参考》这种零星的报道明显不重视。他主观上显然更乐于相信来自中共中央和各地党政领导人的形势判断,更愿意听到他们讲,“目前形势很好,去年春夏都没现在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是从1958年开始,1959年巩固,从1960年看,是更前进了一大步”。
受此心态影响,这一年3月,中央发现山东再度出现春荒,农民外流10余万人,肿病9万多人,死亡1000多人,也只是认为,问题出在省里各级干部没有安排好农民的生活。只要重视起来,做好工作,粮食不是问题。
几乎同时,周恩来读到反映安徽省和县、无为县大批饿死人的群众来信,也只是批转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称:“转上一信,请阅后派人前往两县一查,也许确有此事,也许夸大其词,但这类个别现象各省都有,尤其去年遭灾省份,更值得注意。主席在批转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文件上,也曾着重指出这一点”。
如此政策下粮食问题的大爆发是迟早的事。进入三四月份以后,各地粮食紧张即导致粮食销量无法抑制地猛增,原定1959年度销售计划被大大突破了。还在2月底,中共中央就已经不得不同意各省关于增加粮食销售数额的要求,把原定销售820亿斤的计划修改为917亿斤。到4月中旬,中央吃惊地发现,各地粮食销售的数量还在增加,年度销售指标很可能会超过1050亿斤。
与此同时,还是有大批农民得不到粮食,因而越来越多的地方发生严重的饿死人事件。鉴于无数群众来信雪片般地飞往北京,许多中央高级干部也通过亲友了解到农民饿毙的惨况,许多地方难以隐瞒,不得不把一些情况上报到省委和中央来了。
3月中旬,江苏省委上报了所属“高淳县在1958年冬和1959年春,发生了浮肿病、消瘦病、妇女子宫下垂患者1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6000多人和外流人口10000多人的严重事件”。
4月初,河南信阳地委上报,“从去年十一月份以来……全区发生浮肿病、紫疳病和其他疫病累计596176人次,死亡71658人(包括正常死亡在内),占总人口的0.85%”。
事实上,凡是这时地方自报的死人情况都有隐瞒。如中央赴信阳工作组6月调查即发现,信阳地委上报的死亡数字被人为地大大缩小了。实际死亡人数超过43万,其中非正常死亡人数竟然达到28万之多。
毛泽东就推动“共产风”做自我批评
从1960年5月开始,全国性粮食紧张的情况已经是再明显不过了,大量发放粮食救急,国家各地粮库也日渐露底了。国务院财贸办并粮食部从5月下旬开始,接连4次向各地发出“紧急指示”,并以中央名义几度召开各省、区农业负责人电话会议,要求全力完成中央计划和部署的调运粮食任务,但各地自顾不暇,纷纷向中央告急,始终不能照中央要求行事,以至于由中央负责供应的北京、天津、上海、辽宁三市一省也面临断粮之危了。
7月12日,国务院财贸办和粮食部负责人不得不联名求助于李先念,要求救急。李先念随即先后向周恩来和邓小平,乃至毛泽东告急,说明:“现在粮食库存,北京、天津只够销4天,上海只够销2天,辽宁只够销6天,如果不加速调运补充库存,照当前这个样子下去,是会出乱子的。”
到8月初,中共中央已经发现此前的乐观估计又错了。1960年的粮食产量不仅无法达到计划中的6000亿斤,很可能只能收获4500亿斤。粮食产量一下子缩水1/4,无论是购还是销,原来的计划全都无法实现了。这一情况让中共中央十分紧张,开始提出,全国下一年度的粮食安排必须马上“按需要从低的原则”妥善部署计划。按照这一思路制定的1960年度粮食收支调拨计划,仍旧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坚持要大大增加国家征购粮的数量。1960年度的征购数字被进一步增加到了1325亿斤,虽然销售粮数也相应提升到1108亿斤,出口粮数降低到48亿斤,但在粮食总产量已经低于1957年水平的情况下,即使纸面上全国农民每人全年口粮也只能安排到360斤原粮。不要说留给农民的这部分“粮食”不少是靠白薯、大豆之类充数,即使农民真的能够拿到这个数字的粮食,每人每天平均也只有7两的东西可吃。
眼看粮食真的出了问题,毛泽东第一个反应是,必须坚决压缩水利等农村基本建设工程,“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加强田间生产的力量”。他显然很着急,但并没有想到解决眼下问题的办法,而是指望来年下大力生产粮食。他提出:“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必须全党动手,全民动手,大办粮食。”
9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的指示更是不切实际。它要求进一步压缩城乡口粮标准,并且提出,农民口粮按淮河南北划线,一般应维持平均每人全年360斤原粮,一些地方应压到平均每人300斤以下。指示介绍称:“据河北省委调查,平均每人每天有0.8市斤原粮,加上2斤到2.5斤菜,大小人口调剂着吃,劳动力可以维持通常的劳动。”
可想而知,正是在此前后,因实在无粮以救饥馑,大家纷纷异想天开地构想种种含有这样或那样蛋白质及碳水化合物的“代食品”来充数。从毛泽东一直到地方,各级党政主管部门也都信以为真,想方设法地进行鼓吹,并且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组织生产。
连续两年“大丰收”,为什么还会发生如此严重的缺粮现象,并且会出现粮食产量大幅下滑的情况呢?毛泽东这时无论如何不能不去寻找答案了。而他这个时候也终于考虑出了一个模糊的答案。
1960年10月到12月,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共中央接连撤换了饿死农民人数太多的山东、甘肃、河南3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与此同时,毛泽东把造成农村问题的症结归纳成“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并据此要求各地整风整社,“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11月27日,毛泽东在各中央局汇报时再提粮食增产、丰收,“为什么还会出现饿死(人)的现象”这一问题。他自然不承认“大跃进”或人民公社的基本方针政策有什么问题,而是强调这根本上是“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化”闹的。至于为什么会刮起“共产风”呢?毛泽东带头承认自己“有缺点、有错误”,说“第一个要负责任的是我,北戴河会议决议,有些内容写过了头”。
第二天,毛泽东借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的机会,用“中央”之口再度就他在推动“共产风”问题上的责任做了更具体的检讨。他写道:毛泽东“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而且,当时没有注意到不能由公社来“共”生产队的产,不能搞“一平二调”,不能多搞公共积累,不能过多地搞公共工程,等等。
毛泽东主动检讨后,中共诸多领导人也纷纷在各种场合进行了自我批评。至此,建立在“大跃进”思想基础上的粮食计划指标也迅速降下来了。
1961年1月中共中央还估计1961年度的粮食产量可以达到4100亿斤,但春夏粮食全面紧张,全国十几万个粮站存粮降到160多亿斤,京、津、沪粮食供应全面告急;夏收时更发现全国粮食产量最多可能只有2800亿斤,甚至2650亿斤左右。鉴于此,中共中央不得不大幅调低1961年度的粮食征购数。因粮食严重减产而造成粮食供应缺口,中共中央除下决心将城镇人口压缩2000万以外,还被迫决定动用国家黄金储备41万两、白银储备1.4亿两,以每吨70美元的价格进口上百亿斤粮食来填补。但即使这样,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计算来计算去,还是认定必须要征购780亿斤粮食,并要把农村粮食销量从418亿斤压缩到空前低的300亿斤。
按照毛泽东1959年2月的说法,粮食征购不超过总产量的1/3,农民就不会造反。但周恩来在1960年8月24日中央工作会议上承认,1957年以前征购比例一般在1/3以下,即27%至28%左右,最高也只有29%。但1958年因估产过高,征购比例实际上已经超过35%。1961年如果征780亿斤,合原粮900多亿斤,恐怕也要占到总产量的33%了。考虑到这一比例可能带来的危险,最终这一征购数字不得不下调到717亿斤。当然,这已经无法阻止1961年更加严重的饥荒全面发生了。
1961年1月上旬,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3位被处分的省委第一书记也都正式做了检讨。
甘肃省委原第一书记张仲良承认:甘肃工作中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1958年粮食产量公布220亿斤,最后落到110亿斤;1959年粮食数字开始提400亿斤,公布370亿斤,以后定为270亿斤,实际产量仅仅85亿斤。”“从1958年春季,几个县就发生外流、浮肿、死人。1959、1960年发生问题的面积愈来愈大,时间愈来愈提前,情况愈来愈严重。死人数字是骇人听闻的。现在知道,总数85万人(包括非正常死亡),耕畜死亡70多万头”。
河南省委原第一书记吴芝圃也痛切表示:“估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200万左右……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人民被摧残得家破人亡,几乎人人戴孝,户户哭声,有的整个村庄变为废墟,令人目击泪下。”
山东省发生严重饿死人的情况1958年底就开始了,持续时间更长,故山东省委原第一书记舒同也不能不受到更多的批评。
实际上,除此三省外,其他许多省的死人情况也非常严重,只是多数地方盖子还没有揭开。即使是那些开始揭盖子的地方,由于粮食紧张的局面一时无法改变,因此饥荒死人的现象难以很快得到遏止。好在,毛泽东终于不再坚持办公社食堂了。1961年2月,他第一次在食堂问题上松了口,表态说:“办食堂或搞别的事,不要千篇一律,一定要适合情况,一定要根据各地的特点。如果不适合情况,比方办食堂,势必要垮台,也应该垮台”。
据此,谭震林于3月初在中央会议上提出,办不办食堂的问题和要不要继续实行供给制的问题,农民很关心,但又不敢公开提出来,是否可以讨论一下。
4月15日,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在毛泽东家乡韶山公社调查报告中提出:“从群众反映看来,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愈早解决愈好。”报告并列举了食堂破坏性作用的种种例证。
4月下旬,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均表示,在食堂问题上受了骗。大家一致同意胡乔木的报告,主张“当机立断”。周恩来说得好:“食堂不解决,什么也不能解决。因为自留地要人来种”。
这一年夏天,对农村生产及农民生活破坏性最为直接的公共食堂终于停办了。食堂散伙后,供给制亦废止了,社队从农民手中“抢”去的各种私人财物等部分退赔给农民,农民重新回到家庭生活当中来了。这样,农民又可以养猪、养鸡、积肥,自主经营自留地了,也因此再度有了一些自我应对粮食困难的调节能力。
除此之外,中共中央这时也意识到了解决粮食紧张问题的另一个关键点,即工业、基建、水利“大跃进”的严重副作用,特别是1958年大办钢铁、大办工业、大办水利等猛增出来的吃商品粮的2000多万人。他不得不痛下决心将这些增长出来的人口强行“精简”到农村去,并且对工业、基建、水利等诸多大中型项目建设实行“关、停、并、转”,全面缩短工业、水利战线。如此,持续三年多的严重饥荒,又经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才逐渐得以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