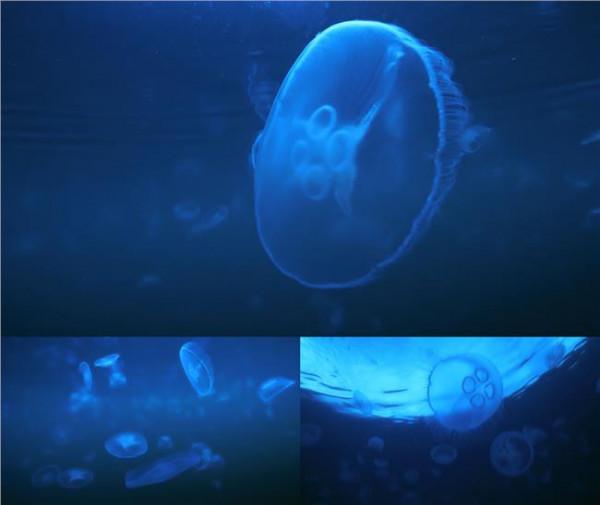上海知青金训华 金训华(上海籍知青烈士)
金训华邮票金训华上海市吴淞第二中学1968届高中毕业生,上海市中学红代会常委。1969年3月,金训华参加上海市革委会上山下乡办公室组织的知识青年学习访问队赴黑龙江,返回上海后发起成立了“知识青年赴黑龙江插队落户联络站”,通过报告会、批判会、座谈会、家庭访问,广泛进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员。
5月25日,金训华和一大批上海知识青年前往黑龙江省农村插队落户,被分配到逊克县逊河公社双河大队。8月15日下午,暴发特大山洪,金训华为抢救国家财产(两根电线杆)牺牲于激流中,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金训华的死,给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注入了悲壮的色彩。在他死后的3个月后,六九届毕业生下乡了,他们纷纷要求去逊克县插队。
金训华人物事迹编辑
如果不是陈健的出现,一段历史就不会激活,一位历史人物也将默默地在黑土地沉沉睡去。
陈健是黑龙江北大荒的上海老知青,名列2005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2006年2月10日公布)之
一。他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行为,只是在36年里静静地信守一个诺言:我要永远留在北大荒,为金训华守一辈子墓。
叙事长诗《金训华之歌》,这是1970年8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至今已经历了35年的沧桑岁月。
金训华,上世纪60年代的“知青英雄”,他的生命在第19个年轮定格。1969年8月15日,山洪突发,150根待安装的电线杆面临危险……有两根被卷走了,金训华跳入滚滚洪流《金训华之歌》抢救,陈健等三位知青、民兵也紧随下水……
陈健被救上了船,现在是黑龙江林区“最后一个知青”,他把信义的坚守,在茫茫雪原上写了13000多个日子。信义,在当今被一些人随意扔进泥淖之时,哪怕小小的坚守,都会像小兴安岭的冰花一样,显得那样晶莹。
《金训华之歌》是在“学英雄”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红色细条纹组成的封面,装饰着青松和火炬,扉页上的“内容提要”说:“这是一部叙事长诗。作品以饱满的革命激情,歌颂了革命青年的榜样——金训华的壮丽青春及其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创作方法上,作者也作了一些新的尝试。”
《金训华之歌》迅速在当时的年轻人中间广泛流传。
“文革”十年的出版物中,诗作者以工人诗人和农民诗人为主。《金训华之歌》的作者仇学宝,就是上海的一位工人诗人。此后较早出版的有李学鳌的《长城放歌》,好像他是北京印刷厂的工人。在武汉地区,长航工人诗人黄声笑也名气颇大,到处请他作报告,我们中学也请他登上大操场的主席台抒发豪情,可见当年诗歌之少。所以,毛泽东不久提出“文艺政策要调整”,批评“没有小说,没有散文,没有诗歌……”
金训华价值评论编辑
上海知青金训华乃1700万中国知青“悲壮青春”的一个符号,38年前死在黑龙江边陲,随即被树为那个年代的“雷锋式标兵”。
38年后,别说年轻一代,就是50岁以上的中国人,还有几人记得住金训华。可是金训华墓,因为冒出个他当年的“插友”陈健(也是上海知青)以及众媒体对陈健的热炒,金训华本以安宁的灵魂再次被亵渎。他家人本已平静的心绪也再次受到搅扰和伤害。
最先“挖掘”出陈健为金训华守墓37年“大新闻”的记者也是个上海知青,此人叫费凡平,供职于上海劳动报社。随后众媒体“闻风起舞”,直至央视“共同关注”栏目一锤定音,最终把陈健先生抬上了“2005感动中国人物”领奖台。
感动中国颁奖词
颁奖词这样描述陈健:一个生者对死者的承诺,只是良心的自我约束,但是他却为此坚守37年,放弃了梦想、幸福和骨肉亲情,淡去火红的时代背景,他身上有古典意识的风范,无论在哪个年代,坚守承诺始终是支撑人性的基石,对人如此,对一个民族更是如此。
也许这个民族太需要重新拾回对诚信的坚守,陈健的“事迹”经众媒体添油加醋加味精后迅速感动了国人。然而,麻烦随之而来,只缘当年与金训华和陈健一起插队的上海知青大部分都健在……
质疑迅即聚焦于陈健,陈在含糊其词时“供”出了费记者,还责怪许多媒体的报道曲解了他的表述。费记者系始作俑者,他承认“守墓”一说是他采访过程中的“提炼”。徐纯中绘《向金训华同志学习》好了,不可责怪费记者,也无须嘲讽其它“闻风起舞”的媒体(包括央视的品牌栏目)。
为某种需要或者达到某种目的,拔高受访对象很多时候已成“习惯性动作”。只要是“正面报道”之需,追求报道对象的“完美”几乎是一种“条件反射”的冲动。要怪就怪多年不改的新闻报道的体制弊端吧。
为了特定年代的特定政治,金训华被树为“知青标兵”;为了感动中国,为了召唤人们重新拾回诚信,陈健再被刻意包装。陈健今日的尴尬,与他自个说话“不留余地”有关;与刻意拔高他的众媒体有关;但说到最痛处,亦与这个时代尚存着的,且仍然大有市场的“劣文化”有关。
在那个荒诞年代,因为各种原因死在异乡的知青成千上万。在回顾和抚摸那段不堪回首的血泪历史的悲壮时,各种版本的纪实文学可谓“浓墨重彩”,可是很少有文字深刻反思,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期间,1700万城市知识青年(他们本该是产业工人队伍的新鲜血液)上山下乡,真如“最高指示”所声称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么?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革前就开始批量输送,那是被权力斗争和大跃进的疯狂折腾而濒临破产的国家的无奈之举;是对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另类转嫁;是让千百万知识青年代为支付“坚持阶级斗争为纲”导致内乱不断所支付的国家治理成本。
一代知青命运背后的社会成本,可能几代人都难以清偿。君不见,如今生活最窘困的45至55周岁的那批社会成员,当年的知青仍占据着大多数。作为上山下乡运动的亲历者,我深深地同情他们,还有他们因经济窘困而缺少良好教育的子女。
文革40年祭悄然来临,如果说深刻反思文革的条件尚不成熟,那么,我们最好不要去打搅已经安息的金训华和“金训华”们的灵魂——否则,这是非常不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