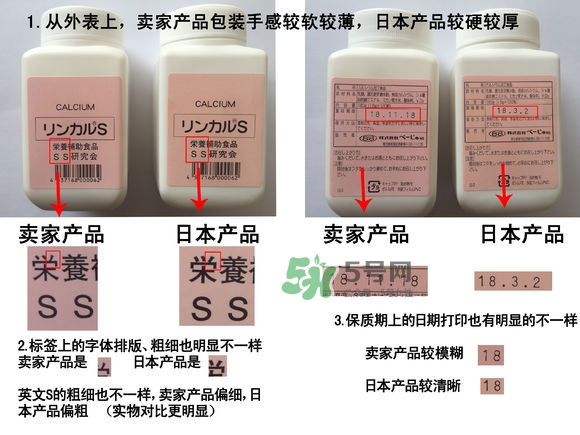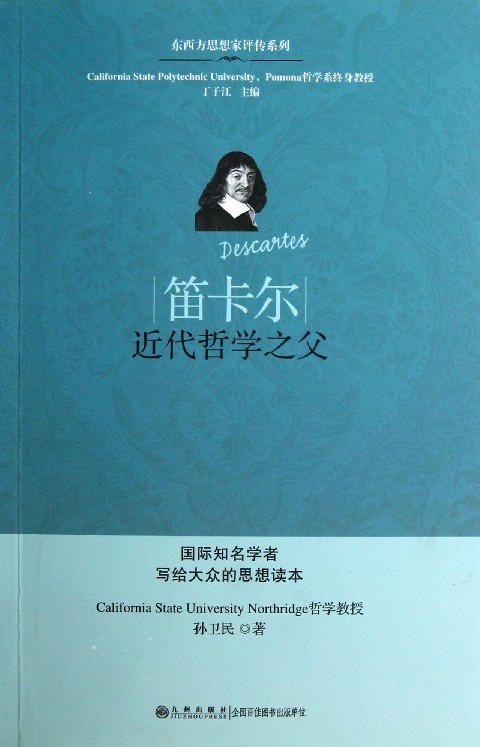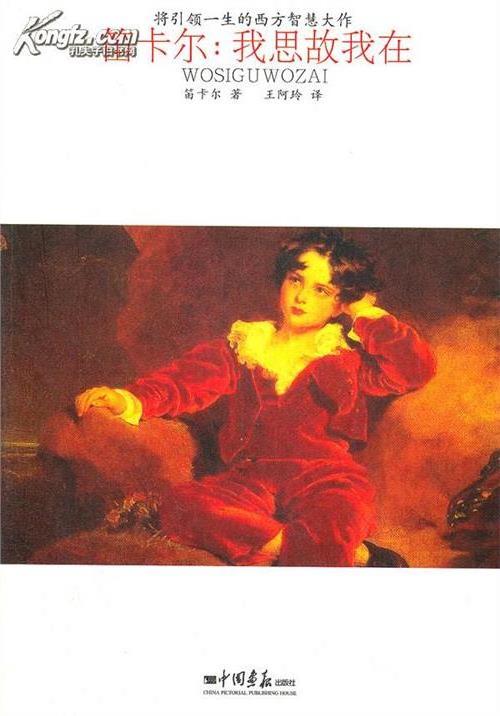笛卡尔方法论 直觉与演绎:笛卡尔的方法论选择及其困境
笛卡尔对西方哲学的贡献主要有两个:一是他主张将追求真理(知识)作为哲学的根本任务,肇启了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二是他系统提出了心身二元论的形而上学观点,成为近代以来西方关于心身问题的一切讨论的缘起。
笛卡尔的上述贡献是西方哲学中不争的事实。不过,当我们理解和阐明笛卡尔的有关观点时,却不应忽视他为提出这些观点所诉诸的直觉和演绎方法。在他那里,直觉和演绎是根本的方法论选择,是哲学研究的真正起点和进路。
根据这种方法,他为近代理性主义认识论奠定了方法和原则的基础,并为一切知识提供了一个形而上学的框架。可是,恰恰在这一方法的选择中,蕴涵着使笛卡尔哲学瓦解的因素。尤其当他试图进一步说明心身结合和相互作用的形而上学问题时,他陷入了与其方法论原则相背离的困境。
本文将从考察笛卡尔关于直觉和演绎方法的论述入手,阐明其在笛卡尔哲学体系中的地位、作用、演变和意义,并结合他关于心身结合问题的观点,指出其方法论的局限,探讨它对全面理解笛卡尔哲学所具有的意义。
一 直觉与演绎是获得真知识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笛卡尔是形而上学家,他曾说形而上学是哲学大树的“根”,包括物理学在内的一切科学知识都是从这个“根”上生长出来的。不过,他所说的形而上学不仅仅指关于“存在”或本体论的那些方面,它还包括知识论的基本原理,[1] 而知识原理的核心内容是关于认识方法的。
就哲学之为严密、精确的知识体系而言,确立正确的认识方法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方面。在他看来,正确方法的选择和运用是第一位的,“存在论”的说明是第二位的,后者只是运用正确的认识方法所必然得出的理智结果。
以上观点可以从笛卡尔的论述中得到说明。笛卡尔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是1628年写成的《指导心灵的规则》(Rules for the Direction of the Mind)。这部著作规定了笛卡尔哲学的发展方向,是他后来一切哲学奥秘的真正发源地。
在这部著作中,笛卡尔不但将追求全面系统的科学知识作为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从而将认识论置于哲学的中心地位,而且还确定了从方法入手解决一切哲学问题的途径。他认为,关于精神、物质的形而上学知识是必须弄清楚的,因为它们是其他一切科学知识的基础,但是要获得可靠的形而上学知识,必须首先确定获得这些知识的正确方法,这是一切哲学和科学研究的关键。
笛卡尔后来的主要著作《谈谈方法》、《第一哲学的沉思》等也遵循了同样的思路。
比如《谈谈方法》(全名《谈谈正确运用自己的理性在各门科学中寻求真理的方法》)的书名已经清楚表明了该书的主旨;[2]而《第一哲学的沉思》按笛卡尔所说,则是运用与《谈谈方法》同样的方法原则对上帝、灵魂等形而上学问题所作的更深入探讨。
[3]笛卡尔进而将直觉和演绎确定为获得一切真知识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将其看成是全部认识论原理的核心环节。他认为,哲学研究的目的是获得人类理智所适合的一切知识,这种研究不能以以往的各种学说为依据,也不能建立在猜测和或然推断的基础上,而必须诉诸于直觉和演绎,这是人类理性唯一合理的选择。
他说:“……在此,我们要注意那一切能使我们毫无错觉地获得关于事物知识的精神活动。这些活动我只承认两个,即直觉和演绎”;“除了借助精神的直觉和演绎之外,任何科学都是不能达到的”。[4]
何为直觉? 何为演绎? 在《指导心灵的规则》中笛卡尔作了明确的规定。他认为,直觉和演绎是人类理性的运用方式,是最基本的认识活动。直觉是指心灵对它所理解的事情形成直接、明确、没有任何疑问的概念;演绎是指心灵从确实无误的事实(概念)到另一个事实(概念)的必然推断。
直觉与演绎的主要区别在于:直觉的概念是心灵“直接”、“全部”把握的(其方式与眼睛的“看”相似,因此也常称为“精神的视觉”mental vision),它不涉及任何思考的过程,它是“非推理的”;而演绎则是“推理的”,它需要由此及彼的思考“过程”,根据推理的不同要求,这个“过程”可以是简单的或复杂的。
笛卡尔将是否包含“推理”当作区分直觉与演绎的根本标志。
“我们根据如下事实将这种精神的直觉与演绎区别开来,即在后者的概念中加入了某种思想活动或接续,而在前者的概念中则没有”。[5]在这里,他实际上继承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观点,只不过他强调的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直觉(nous)与三段论推理的区分,而是直觉与普遍意义上的形式推理方法的区分。
不论直觉还是演绎,它们都是获得必然确实知识所必需的。直觉的知识是“自明”的,它构成了人类知识的“第一原理”;演绎的本性在于其推理过程的无误,它通过将“第一原理”当作推理的前提而提供绝对必然的知识。
因此,由直觉和演绎得到的知识必定是清楚、明白、不容怀疑的。于是,“清楚”(clear)和“明白”(distinct)就成为直觉和演绎知识的标准和特征,也成为一切“真知识”(真理)的标准和特征。后来笛卡尔将“凡是能够清楚明白理解的东西都是真实的”作为认识论的基本准则。
显然,笛卡尔的直觉和演绎方法是从数学的“公理 演绎”方法概括出来的,也可以称作“直觉 演绎”方法。他选择和确定这一方法,既与当时数学取得的重大成就有关,也与他早年从事数学研究的科学实践有关。在他看来,数学的精确性是由数学公理的直觉确定性和数学推理的演绎必然性所保证的,他明确表示要用数学模式来改造哲学和各门科学。
[6]于是,数学公理和推理理所当然地成为直觉和演绎方法的样版。与此相应,笛卡尔反对将感觉、想象和或然推理当作有效的科学方法,他认为这些方法是不精确的,由它们得出的知识往往是错误的、可疑的、靠不住的,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它们至多只能起辅助作用。
笛卡尔关于直觉与演绎的论述有重要意义。首先,它是西方近代哲学关于直觉与演绎概念的经典表述,尤其它对直觉与演绎的区分,不但极大影响了斯宾诺莎、洛克、休谟等人关于知识的确实性和分类的观点,从而成为近代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共同财富,而且还为后来西方哲学中直觉主义和演绎主义的分野提供了依据;其次,虽然笛卡尔所用的“直觉”一词来自于经院哲学,但他赋予其以近代意义,他是第一个将“直觉”引入近代哲学的人,他试图以此为理性主义认识论确立一个可靠的起点,使绝对确实的知识体系成为可能。
他的这一做法不但对理性主义者有广泛的示范意义,对经验主义者也有同样的意义:洛克、巴克莱、休谟等经验主义者将“常识”当作认识论的出发点,在方法上完全可以看成是笛卡尔直觉主义的翻版,在他们那里,“常识”本来就是与“直觉”同义的。
也正因此,经验主义者不同意笛卡尔只将以数学和逻辑为代表的普遍概念看作直觉,即“理性直觉”,他们还将心灵面前直接呈现的感觉也看作直觉,即“感性直觉”,“感性直觉”是与经验直接相通的。
直觉概念上的这一分歧是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分歧,是两种不同认识论立场的分歧,它涉及到知识的起源和确定性等重要的认识论问题;最后,笛卡尔把数学的精确性作为知识的理想,要求将数学的演绎方法引入哲学,他的这个要求不但与经院哲学对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顶礼膜拜不同,也与F·培根对“新”归纳法的竭力推行不同,它实质上是对现代意义上的“形式科学”的追求。
这一追求不但将笛卡尔哲学与传统的经院哲学区分开来,也将它与以心理描述和情感取向为特征的经验哲学区分开来。而他所提倡的形式主义思维方式,深刻影响了后来西方理性思潮的发展,被后现代主义者当作“科学理性”和“逻格斯中心主义”的祸水源头加以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