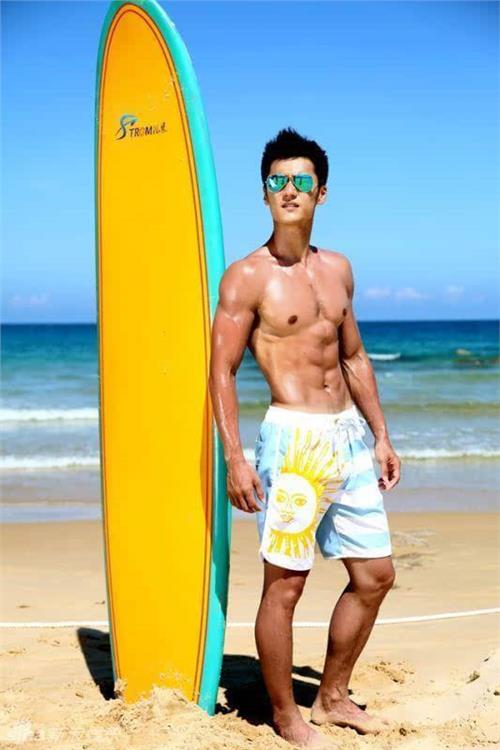纪小龙医生:俺不愿当“专家” 只想做“医生”
北京今年的夏天酷热难耐,难以集中心思干活,胡弄着做事还不如干脆不干活,休养一下又何妨?于是,有空整理一下脑子中的一个念头:我是“专家”吗?得出的结果如下:
1952年我出生在一个中国最普通的农民家庭。小时候在生产队里放过牛、喂过猪,种过田。命运的不可预测性的“阴差阳错”,曾经是“地道农民”的我,现在在医院里每天的一项主要活儿,就是满怀信心地坐在显微镜下对付着各地找上门来的疑难病理的会诊。
不时会有一些年轻医生,带着各种问题来请教,要求我给他们一些诊断病理的“窍门”和“捷径”,俨然成了一位大专家的派头啊。其实,这都是外表,我自己打心底里憎恨“专家”这个字眼,平时不容易对人们述说清楚其中的原委。在经过多次漫无边际的思考,渐渐有了一点条理后,现在整理一下,写下来当作大伙儿干活累了放松时的“笑谈”吧。
一“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美丽”---- 俺很敬仰、崇拜和迷信专家
苦不堪言
小时候,经历过三年饥荒岁月,在村里的小学一边干农活一边读点书。我的鼻子有毛病,小时候整天鼻涕不断地流,就没有干净利索的时候。当然了,农村娃,流鼻涕,那是自然的,没人关心这样的小事,不象现在会被带到医院去瞧瞧。
初中3年在县城中学念的书,还记得有一天上课时老师在上面讲课,我的鼻子不通气,就自己用纸卷成桶状硬塞到鼻孔里面去,想把鼻孔撑开,没想到越捅越不通。1966年夏天正在准备考高中时遇到文化革命,学校停课了,我也就回家继续种田挣工分。每天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里,能混口饭吃就不错了,鼻子通气不通气也就无所谓了,只是有时有些头痛而已,挺过去就算了。
“时来运转”有一
1969年,应征入伍,扔下锄头来到军营,当了5年卫生员。这时有了点医疗条件,懂了一点医学知识,当有一天鼻子不通气加上头痛发热,被师医院的军医知道后,让我拍了一张头部的X光照片,诊断为“上颌窦炎”,并进行了“上颌窦穿刺”治疗。
虽然几天后没有头痛发热了,但鼻子通气状况还是不理想,军医说,我的鼻窦毛病他解决不了,要到大医院里专家做“上颌窦根治术”的手术。而对于我这样的一个基层卫生员来说,这样的岁月从没与“专家”有过任何瓜葛,也就无从谈起“什么是专家”之类的高深话题了。
无独有偶,“时来运转”有二
1975年,我被推荐到军医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学习临床医学,准备当医生了。两年的听课,对我来说犹如海绵吸水,如饥似渴地获取基本理论知识,第三年实习更上如虎添翼,分秒必用。当年轻的实习医生满怀热情,走进一家县级医院实习的时候,对每一个病人的认真仔细,可谓是对每一个病,会对照书本仔仔细细翻查究竟,恨不得每个病人身上的病到这里都能手到病除。
对于一个刚放下书本来到临床的年轻人来说,对照书本弄明白什么病,然后治好,也可以值得洋洋得意了。
但是遇到疑难病症时,免不了会请学校交过我们的老师们来会诊。虽然当时还是文革时期,教授名医们还在政治的重压下沉默着,但是一到病人面前,在我们这些刚踏进医学大门的年轻医学生,对他们还是那样的形象:高大,神圣。
憧憬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佩服之情难以言表。暗暗想着哪一天我也如他们一样,会成为受人崇敬的专家。这期间,我的不争气的鼻子多次扰乱过我的求知生涯,不是轮到我学习外科手术时候发烧就是考试时头痛,当时唯一的念头就是赶快找个五官科的专家诊治诊治。
再一次幸运,“时来运转”有三
1978年我,考上了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来到中国最大的医院,这里名医云集,当时的一级教授就有10来个。自然,当我又一次鼻子不通气伴发热头痛时,马上就住进了医院的耳鼻喉科。这下多年的痼疾总算有个头了,曾经多次求医未能彻底治愈的鼻通气障碍,这一次住进了全国最大的医院的耳鼻喉科,这么多名医专家,治好我的毛病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果然,住院后第三天的早上,终于等到主任来查房了,我的病室门口一下子涌进来20多个医生,围绕簇拥着高大威武的老主任,队伍浩浩荡荡。
主任听完主管我的医生流利的报告着我的病历后,只发出了六个字:“上颌窦根治术”。这时,我顿然感到多年来的痛苦要被消除,心底的喜悦和期待可想而知。对专家的崇敬之情,又一次从心底油然而生。
第二天进了手术室后,刚开始还知道手术医生的一步步操作,不一会儿就被麻麻醉去了,醒来时在病房躺着,虽然刀切口疼,但想到痛苦了三十多年的鼻子的毛病能够解除,也就不在乎疼不疼了。
由于当时是夏天,那时候病房里没有空调,我住的病室在耳鼻喉科三层朝向东南的位置,上午的太阳就透过窗户照在我的床上,感觉到热得很又痛得难忍,不过窗外正好有一棵大槐树,那树枝树叶快接近我病床前的窗户,当时还觉得有一点幸运,因为我的病床刚好被大槐树挡住了炎热的太阳,就这样一个人满怀希望静静地在疼痛中坚持着。
二“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跻身专家而自得,心中疑问也愈多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患者尤其是重病和疑难症患者到大医院找名医、找专家看病的增多,中国医院的“专家门诊”应运而生。按规定,专家是指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临床医师。我是1987年被晋升的副教授、副主任医师,自然也就被列入专家名册了。
当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医院专家的名录中时,心跳不自然的加快了,身子不自然的轻飘了;当外出参加会议等公众场合自己被安排在主席台或前排就坐并面前还有一个“名牌”时,脸上觉得光彩了,心里觉得甜悦了。
可是,我自己鼻子不通气的痛苦依然如旧,尽管手术后管了一两年,可是,时间一长,又回到原来的鼻塞和脑袋闷闷的不爽中。于是,第一次在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专家的本领在哪里?
再看看现在的医院里,大批大批的硕士、博士充填着医院的各个角落,在每天实践着“治病救人”的活计。目前在医院的职称晋升中规定:硕士毕业后工作2年可晋升主治医师;博士毕业后工作2年可晋升副主任医师。而我们知道,近代医学几百年来所实行的是医学院校毕业后实习2年才能当住院医师,任住院医师5年才能晋升主治医师,再经若干年的经验积累才能晋升为高一级医师。
这种时间上的规定主要是基于医生要经历足够多的临床实践,亲自诊治一定数量的病例,处理各种不同的病情变化,才能具备不同级别医生的能力和资格。
因为人的生命只要一次,在疾病诊治中任何一点点失误,其后果都不堪设想,而且毫无返工重做的余地。因此,作为以人为对象的特殊职业的医生来说,其训练、考核和晋升必须严之又严、慎之又慎。而现行的硕士、博士晋升高级医生后,由于缺乏医生训练必备的临床实践,遇到病人便感到无从下手,这样的“专家”能看病吗?
在美国,博士分为医学博士(M.D)和哲学博士(Ph.D)只有医学博士才能当医生,哲学博士只能做研究。而我国目前实行的研究生培养制度下毕业的硕士、博士,是属于搞研究的,其过程是读书、学理论、考笔试、然后做动物实验,写论文,通过答辩便毕业。
这种模式培养的是Ph.D而不是M.D,即具备了做研究的能力,却不具备给病人看病的能力。因此,把培养做研究的博士(我国未区分医学博士和哲学博士)拿来做医生,做实验的“专家”来看病,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软指标能打硬仗吗?
更有甚者,看看医院里“专家”是怎么“炼”成的。目前,我国现行的医师晋升制度是大学本科毕业后一年定为住院医师,五年后有资格申报主治医师,主治医师工作五年后可以申报副主任医师,再过五年申报主任医师。
晋升的硬指标是要有发表的论文或著作。不同的医院对论文数目有所差别,一般的要求是要有三篇以上、而且是中华级或核心期刊上发表的。
至于其他晋升条件都是软指标,这样一来,医生要想晋升除了熬年头以外,唯一的就是发表论文。至于医疗水平、为伤病员服务就无关紧要了。所以,致使一些临床医生不能专心为病人看病、钻研临床业务、提高临床业务水平,而是每天钻到图书馆查资料、搞所谓的科研、写文章、找门路去发表。
而就目前医学期刊能发表的论文数目来说,则是十分有限的。就拿消化内科来说,够得上档次的专科杂志仅有四种,每年刊登的论著总计也不超过500篇,一人3篇计算,每年晋升的人数也不过170人。如此看来在诺大的一个中国,显然这是一个可笑的数字了。怎么办?唯一出路是造假!
目前医学期刊的论著追求的是所谓的高新技术,粗略浏览,有一半以上是研究生的论文材料所成。这些文稿的大多属于实验研究,而且是模仿或跟随国外已经做过的工作,并且可信性也不高,不仅学术价值不大,更缺乏临床指导意义。这样的论文让每天在临床第一线的医生去为了刊登文章而去花大力气、大量的时间去编造能够被编辑部录用的、具有“高新技术”含量的文稿,又能有多大意义,与当好一个合格的临床医生又有何益。
不论国内外,一般来说医学院读书的年限都是最长的。首先是预科四年,然后是医学的本科学习(解剖、组织、胚胎、生理、生化、病理、药理等十多门前期课程和临床二十多科目后期课程)。
毕业后还有二年的实习,再有五年的专科实践,这时才初步具备了意识的条件。由此可见,医学培养要求学生阅读大量阅读社会、心理、政治、经济、法律、伦理、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这是因为人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
因为医生面对的是病人。只精通医学,只能算是学者,即算不上一个好的临床医生,因为他往往不善于用最恰当、最巧妙的方法使病人得到医学所能给病人带来的最大获益。这里需要的是经验!而经验的获得是来自理论知识 临床实践 分析思考三者的结合。
旧事重提,专家能治我的鼻塞病吗?
再回到我的鼻子毛病上。在专家给我施行了“上颌窦根治术”出院后,开始几个月觉得通气了,有了挺大的变化,可是不久,鼻子又不通气了,症状和以前一样。再过了一两年,拍个X光片,说我那手术时打开的上颌窦开口已经又闭合了,也就是说上颌窦根治术白做了。
再到门诊让另外的医生检查,认为我鼻子的毛病主要是下鼻甲肥大,阻塞了鼻腔造成不通气,跟上颌窦关系不大,治疗应该做鼻甲切除。听起来说的有道理,为了鼻子能通气,只好又一次住院做“鼻甲切除术。”
这一次,仍然遇到大专家查房,每次也是几十个人来到了我的病床前,最后结论说是鼻甲肥大的手术不需要全麻,让我配合好手术医生。当时我想,专家们如此重视,那我就好好配合吧。没想到所谓鼻甲切除术,就是用个钢丝套着鼻甲,一块块的往下拽肉,第一第二第三下,我一直强忍着,再往下实在忍不住了,就吼叫起来,无奈,手术也就草草收场。
鼻腔手术后,为了止血,要往鼻腔内塞上一大卷纱布条,称之为压迫止血。
回到病房,巧得很,还是我两年前住的那张床,还是靠大槐树挡住阳光,可是鼻腔压迫的纱布只能坚持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实在忍受不了那种长时间压迫的难以忍受的坐卧不宁的苦痛,恨不得一把将那纱布全部拽出,唯一能做的就是看这窗外的槐树枝,一片一片的数这槐树叶的数目来熬时间,并且感慨:以后要想叫罪犯开口说话,只要请耳鼻喉医生往鼻腔里塞紧纱条就可以实现了。
这一次虽然很痛苦,倒也管事,手术后鼻子还真的是通气了,心里想:吃这点苦倒也值得。一年过去了,鼻子还是通气的,可是到第二年,鼻子又开始一点点堵起来了。我开始有些失望了、灰心了、无助了。
一年又一年,熬到了1992年,我自己也成了主任医师,教授,1993年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我的名字出现在名目繁多的杂志编委之中,我也被不同的场合请上台做一些“报告”,有一次在省级以下的城市,我坐的车也曾被警车开道了,呼啸着开到主席台,俨然过了一把“大专家”的瘾。
但是,我自己明白,再有名的专家不过如此!我的鼻子还是不能正常通气,毛病依旧!鼻塞的痛苦依然陪伴着我,每到寒冷季节,夜晚我只能靠嘴巴被呼吸,药物的“救济”不计其数啊!
各种治疗措施已经是“琳琅满目”了。我开始说出:“连耳鼻喉科主任,堂堂一个院士,都难以对付一个小小的鼻塞,那专家又有何价值所在呢?” 我对“专家”这一的冠名的怀疑产生了:我们那么多老一辈在“专家”的光环笼罩下,究竟解决了多少问题?我自己已经在“专家”的名下晃荡,又解决过多少难题呢?
如此这般,在中国的大大小小的医院里,每年产生着大大小小的数不清的医学“专家”,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分子!于是,我彷徨了,我动摇了,我自愧了,我退却了。我羞于别人把我列入“专家”的行列。我想大声喝道:“我不是专家!”
三“我们需要你,医生……”----我经历着从专家到医生的回归
从“上颌窦根治术”不成功打碎了“专家”在我心目中的神圣偶像,“鼻甲切除术”的短暂效果彻底动摇了我对“专家”的最后一丝敬意。
怎么办?再去切鼻甲?受不了那种痛苦。不开刀呢?终日不通气的鼻腔也痛苦。时间一长,当手术后难忍的疼痛淡化了一些,就又一次萌发出对于鼻塞的痛苦的求治之心。于是又去找耳鼻喉专家,看还有什么法子。这一次专家检查后,象有新的发现,说:你的鼻塞根子不是鼻甲肥大,而是鼻中隔弯曲,由于鼻中隔偏向一侧,所以鼻甲稍微大一点,鼻子就堵住了,因此要解决鼻子不通,应该做鼻中隔弯曲矫正术。
经不起专家的透测分析的理论的穿透力度的影响,于是,又一次住院接受鼻中隔弯曲矫正术。
没想到,此手术仍然不用全麻,只是鼻腔里喷一些麻药,不仅要把肉切开,把弯曲的鼻中隔小骨片凿出来,修正以后再放回去,手术后,又是塞的满满的纱布条。回到病房还是住的那张床,还是靠数着槐树叶子熬时光。出院后,每天我上下班,路过病房楼,看见楼前的这一棵大槐树,都会想起我躺在病床上数过了无数遍的它的树叶。
看来专家的结论这一次终于对路了,一年两年三年过去了,鼻子还是通气的。但是,没想到,第四年开始,一点一点地鼻子又开始堵起来了。怎么办?还有什么办法吗?我的鼻子已经塞了我快五十年了。
又一个夏天来临了,大槐树又枝繁叶茂,高高地耸立在楼前。我是否还要再次手术,再去数槐树叶?一天夜晚,突然的闪电雷鸣,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原来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不一会儿,雨停风歇,我又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雨过天晴,空气清新,我漫步着去上班,来到楼前,一下子惊呆了:大槐树倒下了!
怎么可能呢?这麽大的一棵槐树,突然就这样倒下了吗?晚上的暴风雨不是太大呀,怎么那么多树就这棵大槐树倒下了呢?当我再走近一看,难以相信,高大的槐树的树根却只有菜篮子那么大一块儿而已,与庞大的树身是如此的不相称!
如此微小的树根,那自然就经不起风雨了。真没想到,地面上那么高大的树枝树干和茂盛的树叶,而树根却这麽微弱!当天,就有工人来把树干锯成一节一节的,拉走了。我不知数了多少遍树叶的大槐树,从此就消失了。楼前只剩下草坪上的青草,大槐树也就无影无踪了。
四 “三个医生,赛过专家” ---- 俺不愿当“专家”,俺要做个医生
人类纪元进入到21世纪。这一个跨世纪的时刻,我在想:难道我一个小小的鼻塞都没法解决吗?一天,无意中我和一个每天都在第一线与大量病人打交道的年轻医生,苦诉起我的鼻塞毛病的整个诊治过程,引起了他的兴趣,于是,我俩就仔细分析着以往治疗失败的教训。首先,我从病理学的角度分析了我鼻粘膜的病变是一种“过敏性”病变,要想解决问题,就要采取“三管齐下”的具体方案:
1、从抑制过敏反应入手,用药控制鼻粘膜局部变态反应(滴鼻药)。
2、尽可能多地去处肿胀粘膜(电子鼻镜下),只有把鼻腔“气道大路”修通了,才能根本改变症状。
3、一旦获得效果就要坚持下去,不能中断,避免半途而废。
于是,我就又一次接受了电子鼻镜下的鼻腔鼻窦粘膜清除手术,请呼吸科医生帮忙选择了局部变态反应抑制剂并坚持滴鼻腔。几个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3年过去了,到现在8年过去了,我的鼻腔畅通无阻。
看,治病原来不是靠“专家”的,而是靠“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啊!这时,我开始认真思考起来:专家是什么?
亲身寻医路,
病体品真知。
何为大专家,
不舍昼夜乎?
文明的历史是一部自始至终贯穿着与疾病作斗争的由浅入深、由低到高的认识史。医学就在这漫长的认识和斗争过程中发展成现在的较完整体系。
稍微留心一下医学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远古人类的医学是大众的、平民的、简明的、普及的、实用的、容易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约BC 460—BC377)是古希腊最伟大的医生。医德高尚,医术高明。
曾用过没药、明矾、硝石一类的自然药品。能进行外科手术,用牵引法复位骨折和关节脱臼。这样的方法,因为正确,至今还在使用。中国民间至今仍然广泛采用的正骨、推拿等医术,说明古代医学是平民医学,农人也可以成为高手。
但是,在其后的医学发展过程中,所谓的“高深”、“复杂”、“尖端”笼罩了医学。现在的医科大学读的书要比其它文理科要多,学年要长,要学习的科目几十上百,硬着头皮读完书,出了校门到当医生又要“磨练”数个年头,这样的经历往往使人望而却步,使得医学离人们越来越远。至于普通人,更是被拒“医门”之外。
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活生生的身体,而且,从小到大再老,何时不在关注自己的身子?“久病成良医”已经是公认的事实,即使没有“久病”经历,小毛小病谁没有经历?谁都曾有过的亲身经历就是对身体、疾病、医学的最好解读及最宝贵知识。
医学知识并不深奥,它是人类长期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的总结,是逻辑性叙述的文字句段,是常人可以读懂的。古人那么多文人都同时兼职医生便好理解了(如苏东坡、曹雪芹的医学知识)。尤其是当今数字教学课件的大量普及,要自学医学知识是没有任何困难的了。
但是,为什么病人一到医院看病,就会产生“医学深奥”的错觉呢?原因是被现代“高深”医科大学训练出来的医生已经成为“牺牲品”了,只会用那些“专业术语”和“医学名词”了。这种故弄玄虚的教学体制造成了老百姓听不懂的“医话”了。再则,一个医生如果自己还在“云山雾罩”中,又怎么能说得让别人明白呢?实际工作中也可以看出,只有真正深入到疾病内核,自己吃透了疾病本质的医生,才能让病人听得明白。
可见,病人看病是不需要“高深理论的专家”的,只需要认认真真做事、仔仔细细观察、明明白白治疗的医生!从此,我再也不会崇拜什么专家了,我自己也就不愿意混在“专家”队伍中了,也就不愿意听别人叫我为“专家”了。从内心憎恨“专家”而只想做实事,我要回归到一名普普通通的医生行列中来,做我本该做的医生的事儿。
医生不是靠读书读出来的,也不是靠论文堆出来的,而是靠一例一例的病例诊治过程中“积攒”起来的。如果一个医生不偷懒,能把每一天得到的点点收获积累下来,那么十天、百天、一年、十年、三十年,不间断地坚持下去,那么,他比常人所积累的东西要多出几十、上百倍,而这些积累下来的知识经验在诊治疑难疾病中就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此后,我开始留心“积攒”着每一天的点滴收获,需要提醒的是,积累时要把自己的实践内容作为重心来关注。医生只有亲身体验的病例才会有最真切的感受,这个过程可以是成功,也可以是失败,我认为失败给人留下的教训是更为宝贵、更为刻骨铭心的。能够在经历失败时记录下失败的一步步过程,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计其数的“名医”已经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就仿佛它们从来没存在过。不计其数的“专家”也已经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许多曾有过的知识被淹灭在无穷无尽的时间的浩劫之中。“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任何“专家”何尝不是如此呢?我已经摆脱了“专家”的枷锁,站在了普通医生的地面上,消除了迷茫,透明了视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医)消得人憔悴”,在明确目标下的这样一例一例地诊治,一例一例地推敲,一例一例地积累,最终能多正确诊治一些例子,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