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怡微情书 张怡微:世情小说的“情”与“不情”
两年前,张怡微开始写作《细民盛宴》。最初是想写一部以次要人物为主的家族小说,即不以“祖父、父亲、我”为主干的故事,相反聚焦家族中一些“毛刺”人物,类似于继父、继母、继子、继女,那些家族墓碑上不会有的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这部作品关注重组家庭,更像是她过去十年写作“单亲”题材中短篇小说的总纲,可以说是张怡微前期“家族实验”小说的集大成。在《细民盛宴》中,张怡微写了单亲女孩袁佳乔参与的大大小小八次家族饭局,小说中的少女袁佳乔既有继父,也有继母,孩童无从选择的破碎再重组家庭,不得不去也永远无法自如应对的无数顿“细民盛宴”。
《细民盛宴》涉及的一个概念是“世情小说”,它的叙事模式是传统的,唯一增添的面向,是一个作为对象的“我”,投射于继母、继父眼中,内心所历经的千里江陵。作为中国古典白话文学的体裁,世情小说历来易遭逢“格调”的质疑。
哪怕是写爱情,理论家往往也一定要添上一笔“不只是爱情小说”,以示其为严肃小说,而非滥情之作。但在张怡微看来,其实大可不必。她说,如果看《金瓶梅》、《早春》只看到婚姻,那就是婚姻吧,如果能看到作者到底在做什么,那就看到了世情小说牺牲格调背后的那个意图,那便是有趣的。“情”与“不情”与“无情”,从来只有发生,而无所谓辩证。
访谈
南都:在《细民盛宴》之前,你已经出过不少围绕“家族”这个议题的作品,这部小说算是一个阶段性成果吗?
张怡微:应该是。《细民盛宴》是“家族试验”写作计划中的一个小长篇,“家族试验”今年还会出一个短篇叫《樱桃青衣》,至此我的这个计划暂时结案。
南都:你对家庭伦理问题非常关切,似乎是你的写作母题,为什么会如此关注?
张怡微:我写过离异、写过失独、写过过继,很多状况,比方我今年会出一个短篇关于老年人的婚姻家庭,重逢、相聚,和子女一起参与家庭成立的过程。我想写的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如何以家人的方式生存,基本上围绕这个核心。
《细民盛宴》就是一个重组家庭的故事,里面的人物在一起吃了几顿饭。对于中国人来说,吃饭是一件挺复杂的事情,随着家庭的不断重组,有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必须以家庭的形式生活在一起,你得跟他们过节、吃饭,我想写的是这些并不算团圆的“团圆饭”。
封建社会的很多礼在现代社会都不存在了,但是你会发现在继父、继母、继子这些关系中是存在礼的,比如说有些话是继父继母不能说的,有个分寸跟尺度,说了就会牵扯到“关你什么事啊”。
南都:小说肯定脱离不了时代处境和社会背景,袁佳乔在重组家庭中的处境,也牵扯到很多社会现象,比方说独生子女问题。
张怡微:是的,从现在来看,独生子女是一个很短暂的产物,生生地把伦理关系砍成一个非常简单的形式,开放二胎后你会发现伦理关系又产生了新的生态模式,独生子女变成一个历史。我们并没有很老,但我们的伦理已经成为历史了。很多人对独生子女的看法是觉得他们对亲戚叫不清楚,要用最近网上很红的“亲戚计算器”来叫,但是这个状况现在也在改变。
南都:从原生家庭到重组家庭,你认为家庭模式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
张怡微:我觉得这是很偶然的命运,没有人可以选择出生,只能接受。其实离婚并不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大概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现,随着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后才有财产划分,它产生的很多问题也是历史上新鲜的问题。一直到今天离婚现象的日常化,婚姻的变迁带来很多新的家庭模式,也产生很多故事。
我们的父母都是普通人,随着成长你会发现他们跟书上、电视上的好爸爸好妈妈不一样,时间久了你也会发现人都是很复杂的,不仅是父母,你自己也很复杂,于是慢慢就理解到当中为难的部分。尤其活到父母的离异的年纪时,会发现你也没办法处理这个复杂的感情问题,你做的不见得比他们好。
南都:当这些人物在你的笔下成型的时候,他们有多少你真实生活的痕迹?
张怡微:生活经验是真实的,但跟我本人的生活没什么联系。真实与虚构之间的距离很难把握,当我写到婚姻生活就很难,我没结过婚。之所以我从离婚开始写,因为我父母就离婚了。
南都:小说落笔于细微之处,人物之间细腻的关系连结,和幽微的情感变迁得益于小说家的观察,具体来说这是如何习得的?你在这个过程中经历过怎样的试炼?
张怡微:找一个既不是开心也不是不开心的瞬间,去展开其中复杂的一面。书里描写了一场事故,一个70岁左右的爷爷出车祸,副驾驶是他的女朋友,因故逝世了,人们去采访爷爷的儿子,他儿子流露出一个很复杂的表情,因为死的不是他母亲而是他年老父亲的女友,这个瞬间我印象非常深刻,就真的是不难过,只是很遗憾的表情。
这些瞬间是生活的横截面,发自内心的复杂感受,很难说它是好或坏的局面。
南都:一个年轻作家很容易受制于可用经验和回忆的缺乏,你会有类似的忧虑吗?
张怡微:忧虑倒是没有,比较担心这个故事到底有什么意义,这个忧虑比没东西写要大得多。
南都:这个意义怎么理解?你是希望它在世情小说的层面上有所超脱?
张怡微:所有市民故事都面对一个问题,这个故事它不让你沉沦,也不让你升华。你不断地描摹生活,它一定会存在一个意义的问题,通过讲这样一个复杂的、不怎么令人愉悦的故事,你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
南都:你写的是否算世情小说这种传统叙事在当代的延续?是否有相关古典文本的影响?
张怡微:算是吧,它肯定不是文人小说,我没有在讨论前人的社会问题或思潮,确实只是讨论生活本身,上海又是一个很特别的方言城市。它有古典文本的影响,特别是三言二拍。
冯梦龙所处的是明代商业文化环境,他一定有很仔细地考量,比如说这是一个三千块的人情,还是一个五千块的人情,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里,蒋兴哥休妻打包十六个箱笼,他会把数字写得很具体,这个数字肯定是有意义的,不是随便说的,这跟我们上海的文化非常接近,一个商业的人情世故状态。
南都:对一个既年轻又有作品的作家来说,会经历一个沉淀期,比如有的人会拓展一个新的书写题材或领域,有的人钻研怎样把一个故事讲得更好,结构上、形式上逻辑更完整,接下来你是否思考过,关于小说会往什么方向上做进一步的探索?
张怡微:像刚才提到的,希望去解决故事的意义。可能我也不是一个多好的写作者,我会尝试努力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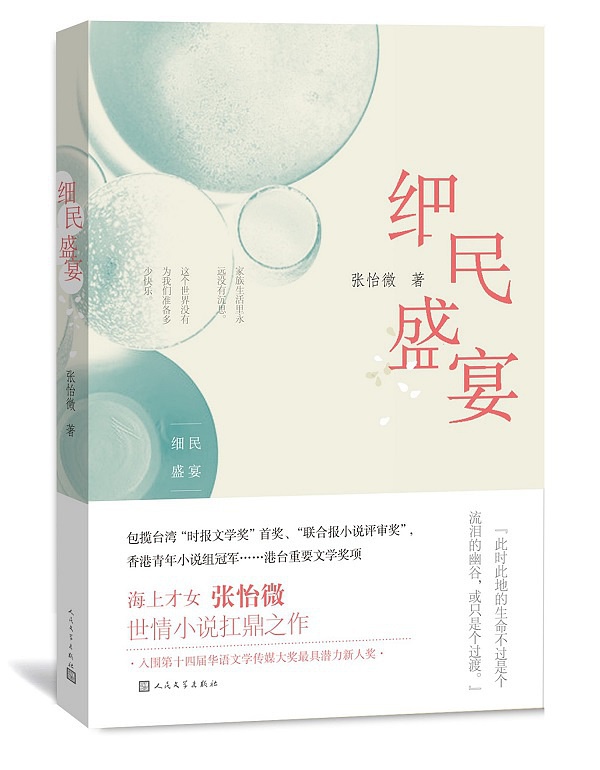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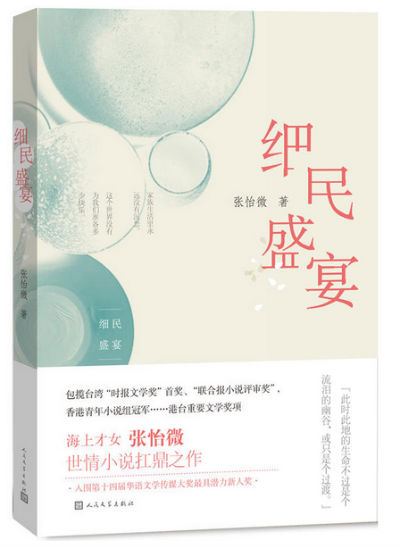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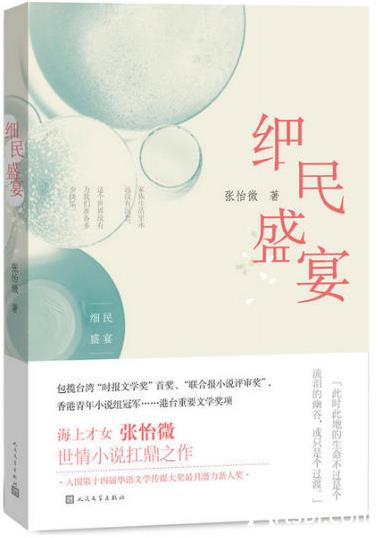



![张近东陈怡 张近东与陈怡离婚]张近东老婆陈怡近照](https://pic.bilezu.com/upload/4/dd/4dde7d596d4598d26fa390e363c141f3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