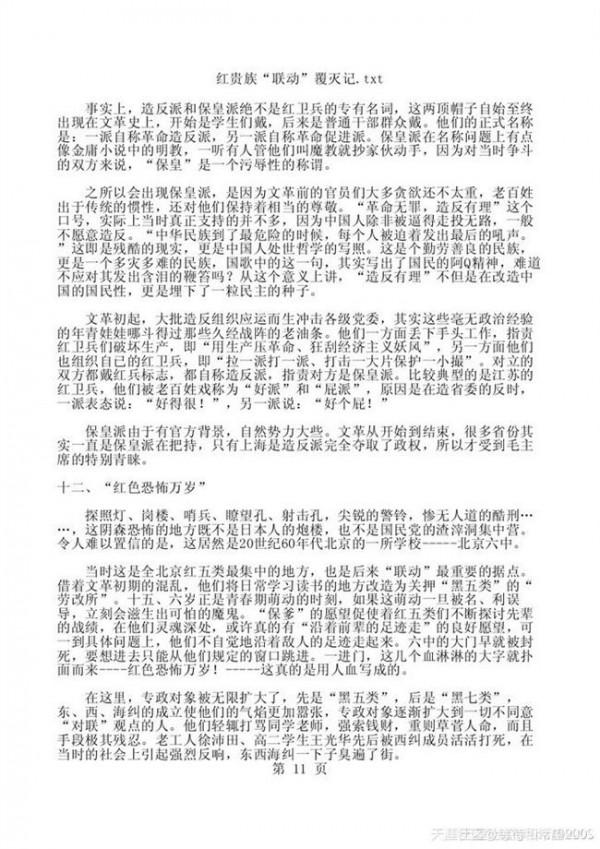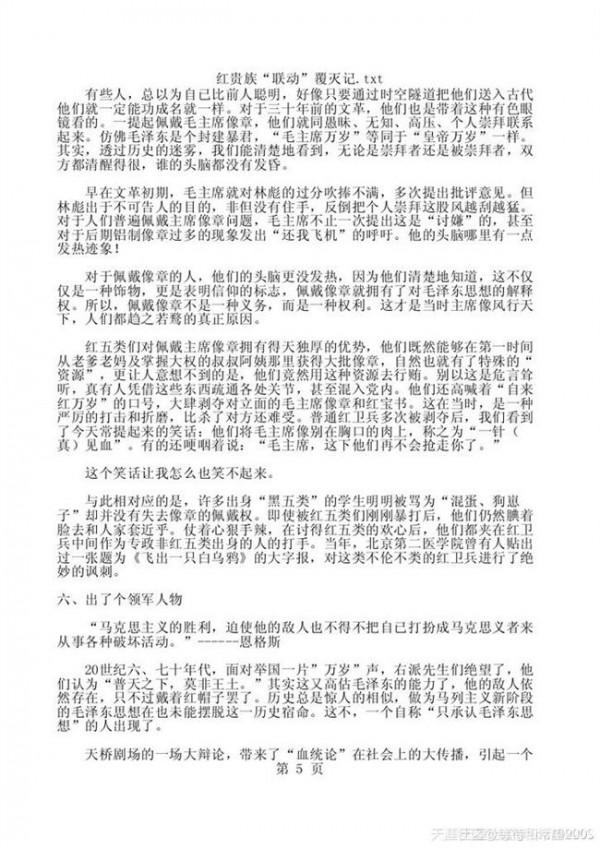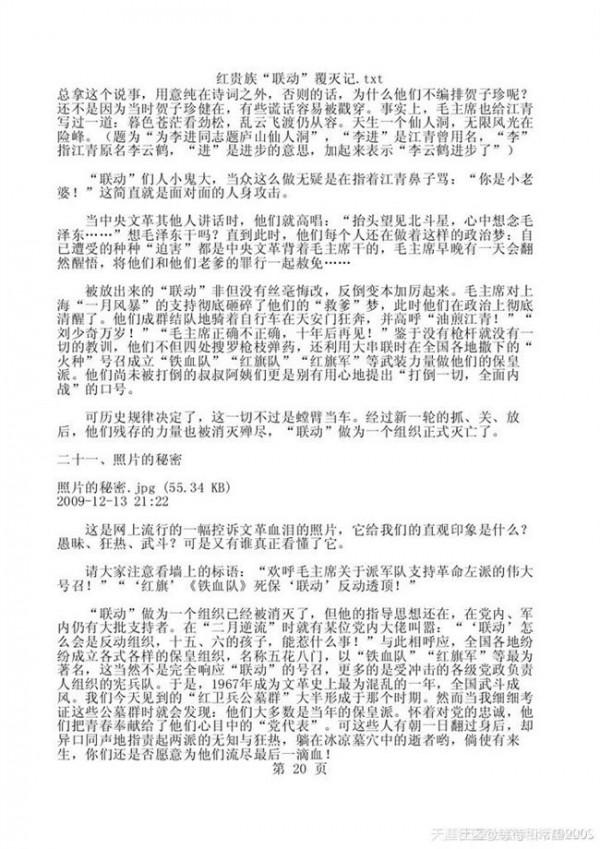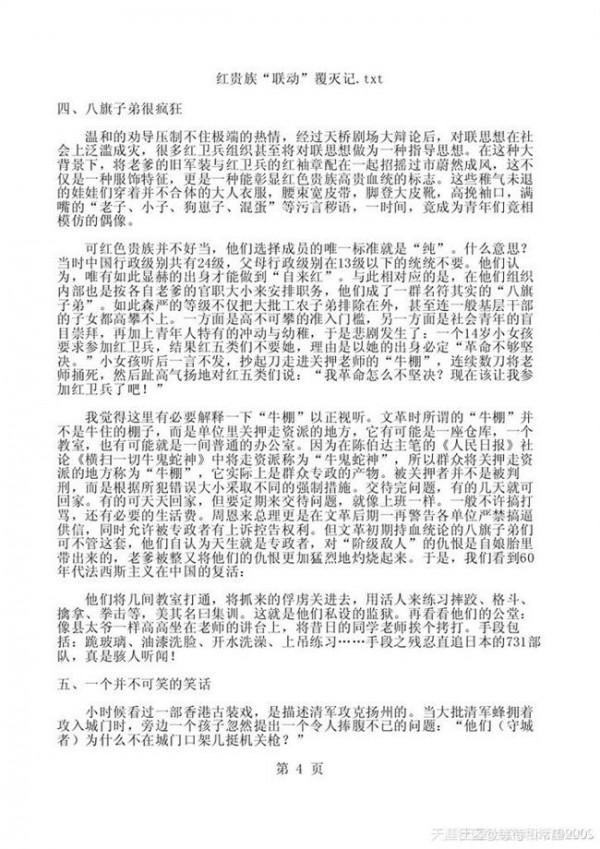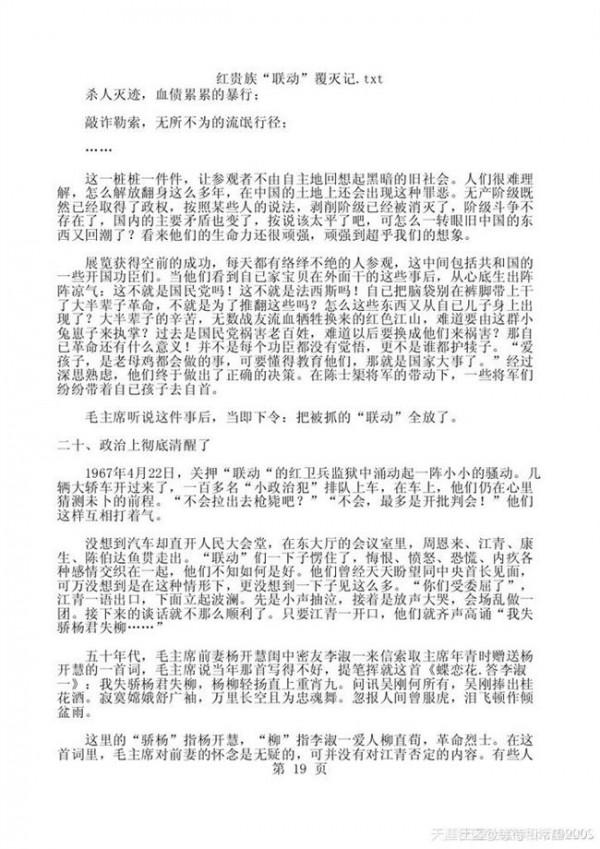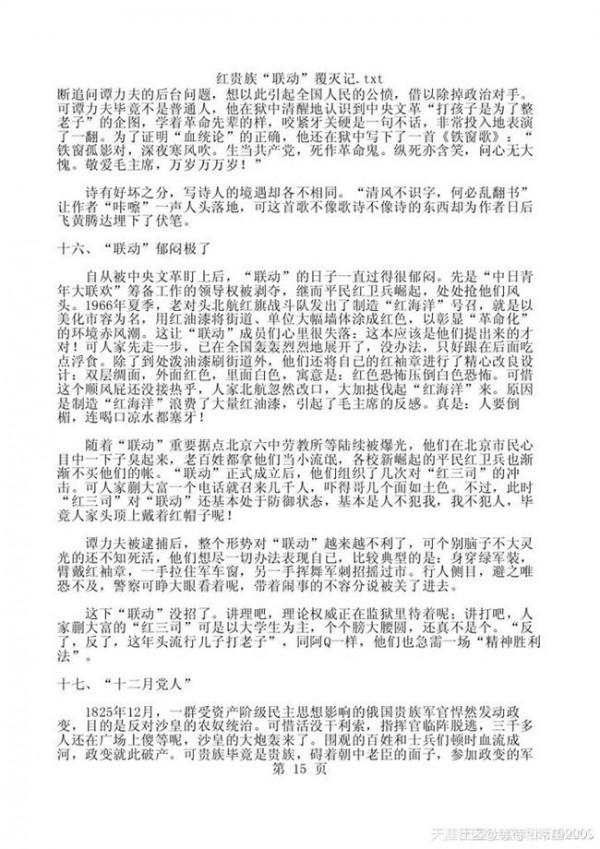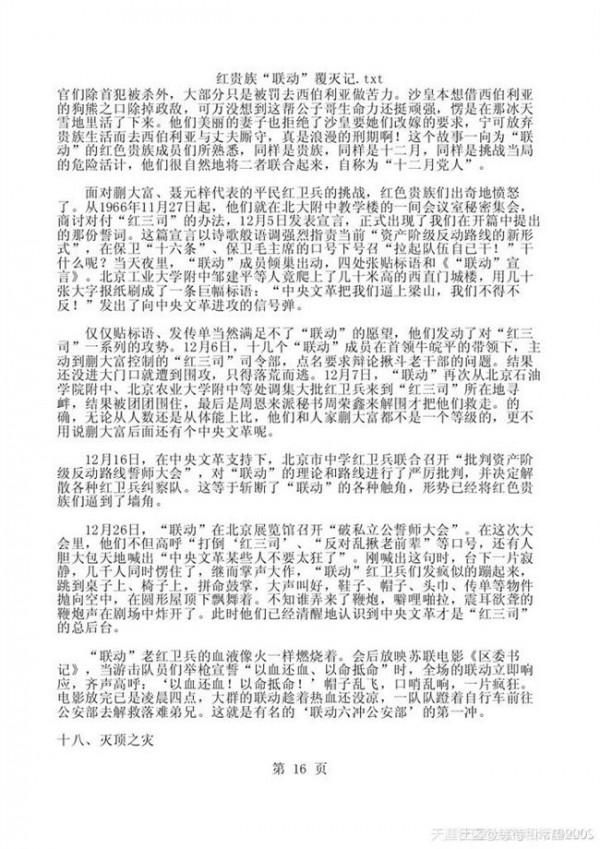阳和平老婆 老田访谈阳和平:文革时期在光华木材厂的工作经历
改革开放三十年,主流舆论一直宣称毛时代的国企“大锅饭养懒汉”、工人“干多干少一个样”。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则大力鼓吹产权明晰、监督机制和物质激励,认为毛时代的国企就是因为缺少这三者,所以工人会偷懒、企业效率会低下。那实际是否如此呢?本文是一个具体的个案,帮助人们理解工人在什么情况下才会想到要偷懒,以及偷懒的目的和实际需要又是怎样形成的。
阳和平教授1969-1974年在北京光华木材厂当了五年工人,1974年赴美之后先后在十余家工厂打工,又当了十余年工人。阳和平在国营工厂养成的工作习惯带到了美国,结果被他的美国同事们讥讽为“傻瓜型工人”:一不会偷懒,二不会应付工头,经过多次找工作和失业的经历,他才逐步学会如何系统地“偷懒”,成为一个精明的美国工人。
美国人权运动的沉寂和中国改革舆论的刺激,使得阳有了强烈的学习经济学的愿望,此后拿到博士学位在大学任教。本文由访谈者老田综合了阳在武汉的一次谈话,后来又到北京进行追加访问形成。
68年工宣队和军宣队进学校来了,有个老工人专门找我谈话,要我别参加那些派性斗争。年底就开始上山下乡了,少数人开后门参军走了,多数学生一批批动员下乡,我也算是68届初中毕业生,同学们多数报名去山西、内蒙,还有好多人去了陕西黄陵县,但校领导不让我下乡。
那时也没有觉得乡下很苦什么的,草滩农场也是农村当然比一般农村好些,都还是能够适应,也没有想到前途怎么样,反正觉得同学们都去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也很想去就是了。
有些官员自己喜欢搞特殊,也以己度人,认为别人也要搞特殊,硬是不让我下乡。学校不让,我就去找区革委会,结果还是不批准下乡,一直找到市革委会外事组还是不批。看来这种“以己度人”是很普遍的,右派以己度人说周总理媚上,说毛主席权力欲,都是这么“度”出来的。后来我的弟妹都让下乡了,去了安徽的茶场,这跟我的长期抗争有一定关系,算是对他们政策开放一点。
最后把我分到光华木材厂,厂子在广渠门外,是五十年代初期建起来的中央级企业,有3000多人,68年春节过后去上班。这个厂里造反派头头刘锡昌是九大中央委员,其实真正起作用的造反派领导人,是几个知识分子,谢富治希望选拔出身好的老工人进去中委,这样就选中了他。
我去厂里的时候,刘已经不在那里了,四人帮倒台之后他也跟着倒了,1983年整党,要求党员重新登记他没有去登记,听说他对人讲自己一生只入一次党,还是有点骨气的人。
那个时候有很多形式主义的东西,例如把街道的名字改成革命化的,例如反帝大道反修大道等,厂里搞了一段“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这大概是69年七八月份的样子,天气还不太冷。有些人就是喜欢用非常革命的口号和形式,把自己包装起来,显示自己如何革命,希图捞点政治资本。
跳“忠字舞”的时候,大伙儿都应付,但是有些“假积极”非要搞,很多人都不满意,但是都不敢公开挑战。这样的人到处都有,我记得初中时有个广播员说错一句话,就被这种人抓住不放,做完自我批评还不行,还非要开大会批判,硬说她是故意那么讲的。
而早请示晚汇报那些东西,因为表面上很忠、很革命,也没有人敢于正面对抗和反对,但私下里都觉得他们无聊,认为这些人是转移斗争大方向。
还有段时间比像章大小,前门大栅栏一带甚至还有像章交易市场所,一些人把铝合金都拿去造像章,造飞机都没有原料了,毛主席只好自己出来讲话说“还我飞机”。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些“假积极”看到没有什么政治油水可捞,自己也不积极了,“早请示”搞了个把月的样子就停下来了。
斗争方法和内容本身就是阶级斗争规律的反映,那些人目的,一是用这个为自己捞政治资本,二是用这种方式去打击别人。工厂里那些真正有历史问题的人,反而是老老实实、好好干活,木材厂有个过去国民党的兵,每次运动中间都挨斗,干部特别喜欢打死老虎,其实就是转移运动大方向,当权派尽会干这个,是非常卑鄙的计谋,目的就是找替罪羊,把自己保护起来,这种搞阶级斗争的方法也反映阶级斗争的内在逻辑。
除了那些短时间的形式化的东西之外,当时工厂里头学习很多,学习社论、政策和文件,还有参加四届人大的宪法讨论,讨论四五计划等等,这些我都经历过。一般情况下,白班是下班后学习,晚班是班前学习,多由工段、班组组织进行。
我在那里赶上讨论宪法和四五计划,讨论的时候,先是传达五年计划国家发展的大方向是什么样子,然后就集中讨论时候,大家想着怎么样发挥工厂的潜力,配合总的发展计划,讨论中时形成一个明确的感受:我们工厂是整个国家的一部分,自己干活也不是为了某个人,经济发展过程和结果不是哪个人自己的东西,而是与全国人民的利益紧密相关;在讨论了国家大的发展方向时,也联系自己的工厂,还有自己的努力方向,国家哪些方面需要发展,工厂生产上有哪些缺环,工人为此提出好多技术革新建议。
那时没有多少贫富差距,国家发展了,理所当然会有你一份,讨论之后都觉得发展前景跟你有关系。
我最开始是在八车间,生产贴面板,有了贴面板,就可以把碎木头粘在一块,然后表面贴上整块的贴面板,看起来好看。贴面板是由好几层牛皮纸侵胶后垒成模板,送进热压机里头,控制压力,蒸汽控制温度,压多长时间,也得熟悉机器的特点,掌握机器的脾气,大概学几个月就可以了,不像车工始终有个熟练程度问题。
压一次几十分钟,然后换一次,一个班要换个七八次的样子。换完板子之后,就到休息室里休息,有聊天的,也有扯开嗓子唱红灯记类的样板戏的,我挺怀念那个时候。
当时学习抓得很紧,每天都有,班前要学习一两个小时,家里有老婆孩子的工人就觉得是个负担,希望快点回家。八车间这时整改作玻璃钢,是一个军工产品,我和表姐两个外国人和另外一个华侨调出去了,1970年把我调去五车间。
到了五车间之后,领导告诉我说:你可以不参加学习;我说我要参加,他很强硬地说:你可以不参加。这简直气死我了,实际上他们是不想让外国人参加学习中央文件。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主席说不要上陈伯达一类骗子的当,提倡读马列原著,指定了六本书,还是不让我参加,我就自己去买来自己啃,最近我还找到当年买的《反杜林论》,书页里的道道都还是那时划的。
当然还买了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还有《资本论》,第一卷没怎么看完,这次的学习跟初中时学习“一分为二”和批判“合二为一”联系在一起了。
因为干部硬是不让我参加学,我就非要跟他较劲,自己努力学。当时学的东西,印象真深,回到美国之后,这个“马列”的“流毒”硬是肃不清,资本主义的一套逻辑就是没有说服力。但人跟人不一样,我表姐卡玛也学了,她回美国后的思想变化就很彻底。
普通工人不仅学这些原著,还要学文件,下来的时候有时说今天学了什么什么文件,但是不能告诉你。许多工人学习实际上不积极,组织学习又必须参加,有点无奈,也有的有怨言,说“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很多人都是希望一下班就回家去,就是因为不愿意学习和参加会议,结果在不知不觉中间丧失了主人翁地位,变成了今天的雇佣工人。早先自己不学习提高,最后就不得不想着怎么再一次去求解放了。
工厂管理中间,鞍钢宪法当时讲的很多,我看还是有不完善之处,要不然就不需要文化大革命了。改变所有制内容还不够,还有人与人关系的内容,特别是干部和群众的关系,这光靠鞍钢宪法还不行,领导层是怎么来的,群众组织是个什么地位,大字报的作用和地位怎么样,这些在鞍钢宪法中间都没有得到解决。
文革期间参加革委会“三结合”的干部,需要有群众推荐,经过群众审查同意,群众可以通过大字报或者辩论方式批评干部,这都是鞍钢宪法所没有的新内容。
我在中国当工人的五年里,认识的工人中间,痛恨文革的不多,而认为只有像文革那样的群众运动才能对付官僚腐败的却不少。文革期间,要是领导人不得人心,根本就管不住人,工厂里当干部的搞腐败可不容易,一旦被群众发现了,一张大字报贴出来,这官就不好做了。
中国历史上也有数不清的“下”犯“上”的农民暴动,但是只有文革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基本上是以非暴力的形式进行的大规模的“下”犯“上”的(也实质上是民主的)搏斗,就其本质来讲是一场提倡同以往统治阶级以武治人的做法相反的一场以理服人的“文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文革的特点,这样才能更好地落实工人民主参加管理和监督企业领导的权利。
当时我们工人都有铁饭碗,不怕干部,所以敢提意见、写大字报,虽然当时干部缺少挟制工人的手段,但工人干起活来很少有偷懒的,生产年年超额完成计划。
苏联的“一长制”还是列宁提出来的,当时因为要从无政府主义状态中间奋斗出来,而鞍钢宪法与“一长制”和马钢宪法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拉近了干部与群众的距离。在光华木材厂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按照鞍钢宪法办的,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
在美国工厂里,工人看到老板来了精神很紧张,但光华不一样,干部来了工人该干吗还干吗,聊天的继续聊天,看报的继续看报,甚至还反过来说干部:哎呀,好久都没有看见你了,言下之意是你有点脱离群众,干部反而要反过来作解释,说是什么原因才这些时没有下车间来,就跟作检讨似的。
工人那时候不怕干部,倒是干部有点怕工人,怕工人贴大字报。工人不怕干部,这才是真正的民主。美国当工人就完全不一样了,工头来了你必须表现积极干活的,你不干活就要走人,管理人员完全掌握着你的工作机会,那是非常大的权力。
当时工厂里头的问题,往往还等不到大字报出来,平时在会上就提出来了,迅速就解决了。提什么意见的都有,但人身攻击的少,大多数人还是通情达理的。有个特别能说会道的同事,俏皮话特别多,一串一串的顺口溜,跟他聊天,一天的工作都很愉快。
还有一个同事外号“大石头”,他是一个对什么都要发表意见的人,脑子里尽是点子,厂里和车间的领导特别烦他,领导安排生产他老是有不同意见;工作之余还组织球队比赛,真是个不折不扣的活动家。
他有次提出在热压机那里搞个升降机,以减轻体力劳动强度,过去车间主任也干过这活儿的,认为没有什么大不了,不太热心,因为大石头老是提,后来职工开会时讨论通过了他的建议,这样就得按照他的意愿搞。当时工人地位高,有发言权,干部姿态低,脱离群众、没有与群众打成一片就算是犯错误了,工厂内部干部与工人距离很近,虽然不是刻意要求按照什么规定执行,但实行的就是鞍钢宪法规定的那些东西。
有了工人合理化建议,生产环节整改之后就更合理了,工人确实感到是企业的主人,不需要另外制订一套制度,自上而下去把工人都捆死。
那时也有工人抱怨说,工资老是不涨,再就是对干部作风有些意见,偶尔对某个领导说点牢骚和怨言,虽然有这些意见,但都没有对工作态度造成太大影响,你观察他干活都还是很负责的。毕竟在工厂工作,投机偷懒的机会太多了,但没有多少人用这些机会,跟后来美国的工人一对比,就觉得光华那些工人都属于“傻瓜”型的,很少利用机会偷懒。
当时我感到最不合理的是倒班,白班晚班每个星期换一次,好不容易适应过来,就又换过去了。不过,要是一个月倒一次的话,习惯就更巩固了,更难倒过来,只有一个车间组织了一帮人专门上夜班,是固定的。
大的制度变革,那时候要经过大辩论,很多工人也是习惯成自然,我发出倡议希望改革这个倒班制度,但没有多少人响应。除了旧的习惯势力确实比较厉害之外,从上往下看,确实需要一个按时的规定,判断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可能有些不同,这体现了个人与全局的差别。
当时厂里没听说过职代会,有一个造反派组织大联合形成的工代会。70年预备召开四届人大,我们厂里也组织讨论宪法,参加人大代表选举,那时国家政治上什么大的东西要发下来讨论,主要是召开车间和班组会议进行,小组开会把意见集中起来。
开会有时也流于形式,有时也开全厂大会,经常涉及的倒是福利和食堂等问题。要是干部干什么大家不同意,大字报就来了,不需要形式化的程序,因为有这些潜在的威胁,干部也不敢乱来,因为不是那种干群严重对立,反应意见的渠道多种多样,都很有效。
讨论生产计划,有些事明摆着的,技术革新和人员安排该怎么办,管生产的一说,工人掌握的情况比干部少,也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还有比方说哪那儿安全有问题,你那个地方老是坏,要提请注意,日常工作就可以上去,不需要很形式化的东西。
当时工人的就业和工资是有保障的,干部控制不了,胡作非为的空间很有限。涨工资的时候,也不是干部能够说了算的,先是车间有个方案,发下来班组讨论,同意不同意,要经过班组和车间两次讨论,这个争论往往很激烈,工人中间还是平均主义意识比较浓厚,上次你涨了,这次该我了,谁年轻负担轻要让一让,某个老工人家里人口多负担重,应该考虑等等。
西方在企业中间也讲究这个,培养团队精神,后来我在AT&T工作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们那里工资升级实行的倒是大寨那种“自报公议”方式。
要是车间主任不顾工人的意愿,硬要把某个人的工资涨上去,那他以后的工作就难了,工人心里不痛快,有好多消极抵抗的办法,分配工作就说让你找谁谁去,谁谁不是涨了工资吗?干部也缺少大棒对付工人,要是不得人心真是没法领导,办事儿和涨工资都必须大多数能够认同才能执行,如果只有几个人闹,大家都不理他。
对干部来说,为了极少数得罪大多数,绝对是划不来的。
而且当时还有大字报的权力,工人就可以说出自己想说的东西,干部也没法报复。那时工人感受不到多大上面来的压力,因为干部不掌握工人的生杀权,在提升和工作安排上穿点小鞋,范围小、利益也不大,所以心情舒畅。
当时同事中间,多数老工人都很感激社会主义制度,认为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他,整个身心都扑在工作上,光华厂有的工人是从农村来的,跟农村比条件要好得多,也很满足。有个同事老家是河北农村的,他两个星期回家一次,装满两麻袋锯末绑在自行车上,骑行100多里地带回家当燃料,这个人是从农村的砖瓦厂调来的,一年四季都这样,他也是把本分工作干完,不关心厂里的事情,心思游离于同事圈子之外,自己有一番另外的天地。
还有一个外号“小赖包”的,特别消极,他除了本份工作以外,什么也不帮别人;其他人自己这边活儿干完了,你那边还忙,我去帮你一把,干完了我们一块儿休息一会儿。
赖包这样的人是极少数,他也不破坏捣乱,就是从来不会帮别人,只管完成自己本分的工作量,他有困难别人也不会帮他,自己孤立自己也没脸,人家也看不起他,给他起个绰号叫“赖包”。
虽然不是正式强制,但这种“同辈压力”是很厉害的。因为他家里是小业主出身,所以对新制度比较消极,还有些小市民出身的自由职业者的孩子,也消极一些,也是心思游离于同辈圈子之外。
除了工作条件和收入之外,人生意义追求也是很重要的,我父母离开美国毅然奔赴延安,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虽然比他们在美国时艰苦的得多,但他们自己认为穷乡僻壤的创业和生活更有意义,是值得追寻的人生意义。我父亲在那负责农场的奶牛养殖,我母亲应用它的物理学知识改良农具,设计牛场,我就是北京出生,在西安的一家国营农场并在那里长大的。我爸爸常说他们是为活而食,不是为食而活。
在工厂里头升级,从学徒工开始,两年后升为一级工,再升级为二级工,月工资38.61元,这是到了年限就升级,再要升三级工就得等机会了。那时代提倡雷锋的螺丝钉精神,我当工人时有一种一辈子当螺丝钉的想法,也心甘情愿,全副心力都放在生产上,看技术上有什么需要改进的,整天琢磨这些设备,到处看,到处观察,有一次发现热压机的底座铸钢裂了,需要修理。
只是到了美国之后,才想着要当技术工人,爬上高等级。当时在光华根本没有多想,前途是什么,以后要怎么样,只是想着干好工作,连上大学的念头都没有起过。那时物质上的东西不多,级差不明显,也许有人想要爬上去掌权,但干部和工人谁说了算,还是有得争的。
八十年代初期,改革舆论中间有一个说法叫“大锅饭养懒汉”,其实在毛泽东时代我和同事们一点都不会偷懒,是到了美国以后才学会偷懒的。回想起来,毛泽东时代的工人真的有点“傻”,总认为我们的劳动目的不是为资本家赚钱,而是为国家为自己,所以劳动上有一种自觉性,不依赖干部的强迫和监督。
真正在第一线的生产工人,他们对自己的劳动是有成就感的,有一种在劳动中间创造出来产品东西,而个人对劳动成果还有感情。当时工人在一起吃住,在一块儿劳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很好,很温暖,非常让人怀念,吃饭在食堂,住在宿舍里,还一块学习。我到了美国去以后,老是想家,想的不光是我的父母,还想着光华的工人,梦里常常都想着他们。
光华厂管理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对女工的歧视,这在短期内往往不明显,我去美国之后过一段时间回来,一起进厂的男同学提拔的就很多,女工同学都还在原来的地方生产一线,最后男工同学只有一个没有提干,而女工同学只有一个人提拔了,这还是因婚姻关系——她嫁给了一个厂级干部。
这有些是自身的原因,女工承担的家务事情多,在厂里也不积极,但也有好几个女师傅嘴巴很厉害的,干部都不敢惹,还有的也很能够团结人,也有能力的,就是不提拔她们。她们也不是为当干部而闹,有些是“刺儿头”,批评干部一点情面不留。传统的观念确实根深蒂固,男的看不起女的,认为她们话多就是爱挑刺,甚至认为是泼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