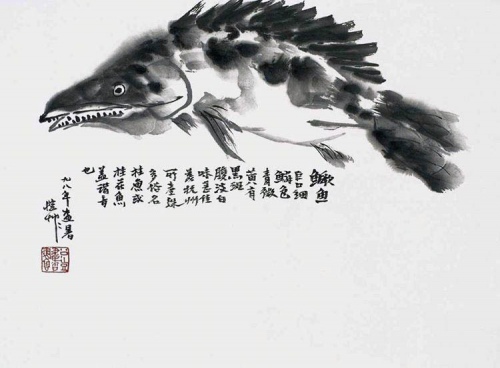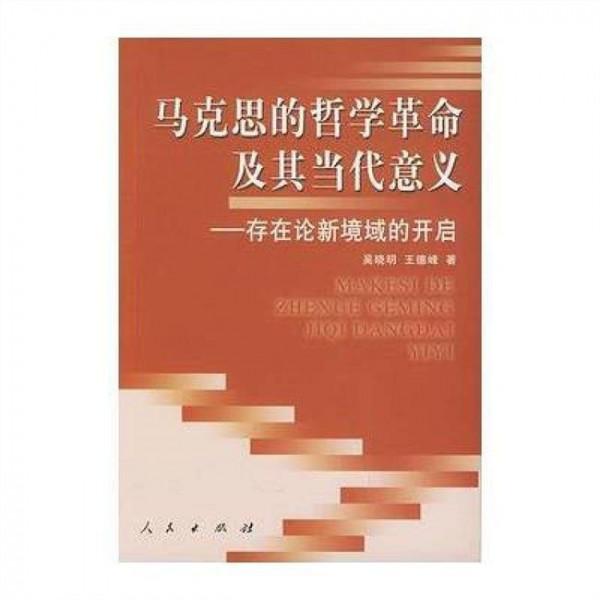高居翰教授的一个中国美术的梦想
元宵节正好是周末,普林斯顿刚刚从一场暴风雪中回过神来,蓝天白云分外的清朗,拿骚街上厚厚的积雪都堆到了路边,晚上接到普吉湾大学洪再新教授转发过来的伯克利艺术博物馆白珠丽(Julia White)的邮件,告诉我高居翰教授去世了。
2013年,为了接收和整理高居翰教授捐赠给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的私人藏书、中国美术史的数字图像和教学幻灯资料,我先后两次应邀造访伯克利小镇高先生的家,第一次是在3月份,带着两位助手范白丁和曾四凯,在他家住了20多天;第二次是我一个人,在11月的下旬,前后停留了5天,现在回想起来,点点滴滴的事情仿佛就在眼前一样。
印象中,我们第一次访问高先生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不是很健朗了,人看上去有些消瘦,但还能拄着拐杖走动,精神倒是矍铄的,说起话来声音洪亮。基本上,他每天工作两到3个小时,当时主要是在忙网络视频讲座第二部分的录制工作。白天,我们在楼上编目和整理图书,他在楼下录视频,或者坐在电脑前回复来自世界各地的邮件。饮食起居自己打理,只是隔一两天会有人过来帮助他处理一些生活的杂事。
高先生热情好客,坚持要我们住在他的家里,还常找由头请我们吃饭,记得同他一起吃过美国饭、日本饭,还有中国饭,有时,他还请我们吃他做的墨西哥饭,我们当然也做中餐给他吃。其实,我们3个人住在他家里,多多少少是有些闹腾的,但临走的时候,他一再跟我说,你们3个人是模范房客。
平日里,我们与高先生多有交流,特别是中晚餐的时候,会谈论各种话题,他乐于跟我们讲他的经历和自己的旨趣爱好,包括童年时代在伯克利的生活,这些谈话的内容如果汇聚起来,倒是有点像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美术史的学术史了。
我个人觉得,高先生在他的生命最后阶段牵挂于心的一件事是想要建立一个中国视觉艺术的图书馆或研究中心,以便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和提升中国美术的教学和研究的影响力。他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和研究中国美术。他把个人的大部分藏书以及13000多幅中国美术史数字图像资料、教学幻灯片捐赠给中国美术学院的图书馆,我想主要是为了这样一个宏伟的目标。
当然,里面也包含了这位享誉学界的国际顶尖艺术史学家与中国美术学院长期交往中积累起来的一份信任感。
他最初提出这个想法是在2013年1月份,那时,我正通过电子邮件与他商量捐赠图书的整理、编目和今后的图书馆的开放和使用的计划,在给洪再新教授和我的邮件中,他谈到多年前看过的一部印度舞蹈家乌黛·香卡(Uday Shankar)主演的电影《卡帕纳》(Kalpana),这位杰出的舞蹈家说服一位电影制片人按照他的想象来拍摄一部电影,创建一个印度舞蹈文化中心,这部电影启发了他建立一个中国视觉艺术图书馆的梦想。
那应该是一个面向有资质的学者开放的机构,为他们提供教学和研究需要的图像和文字资料,他特别希望能透过庞大的数字图像和他所录制的网络视频讲座,来促进学界对中国艺术的图像研究。与此同时,他也一再叮嘱,这个图书馆要充分开放,文字类的书籍,要允许读者借阅,让它们在人群中流通起来。
未来图书馆的定位不是纪念性的,也不只是让那些研究高居翰的人使用的,而是要让它为那些研究中国艺术和文化,研究日本艺术和世界艺术的人提供服务,它必须是一个研究型的图书馆,不是高居翰个人的纪念碑。
他的这个想法其实也是反映了他的一种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信仰和胸怀,他始终有一种视学术资源为社会公共财富的意识,而他自己首先身体力行。
11月下旬,我在伯克利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已虚弱得不能行走,人也更见瘦削,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但只要是醒着,就仍然会投入工作,写邮件,接待访客,安排事情,给我的印象是,一切事情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而这次去也正好碰上了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那是11月22日下午,伯克利东亚研究中心专门举办的向高居翰教授致敬的学术研讨会,主题是"明清时期中国的透视绘画"(Perspective Painting in Later Imperial China: A Symposium in Honor of James Cahill),由伯克利艺术史系的中国美术史教授帕特·伯格(Patricia Berger)主持,来自哈佛大学的王悦进教授、斯坦福大学艺术史系的文以诚教授(Richard Vinograd)和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的中国艺术策展人南希·伯利纳(Nancy Berliner)女士做了3场专题演讲,演讲厅里坐满了来自北美各地的高先生学术粉丝们,高先生本人坐着轮椅出席了这个会议,还在会上发表了20分钟的开场演讲。
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公开的学术演讲吧。
高居翰教授一生致力于中国美术史的教学和研究,他的著述宏富,见解独到,文笔畅达,在中国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我们跟他开玩笑说,你在中国可是一位明星啊!他听了后,爽朗地笑了,对于中国国内有那么多学者和学生喜欢读他的书,他是感到非常兴奋的。
他深以自己的观画能力为自豪,依靠眼睛工作,以敏锐细致的视觉形式分析,形成包容广阔的中国视觉艺术史的新图景,因为是有所跳脱,因为是具备了一种超越地域局限的世界眼光,所以,他对中国美术史的一些传统话题就会有不同凡俗的想法。
他跟我们讲起他曾鉴定过一件出自张大千之手的模仿董北苑的山水画,这张画被其他一些行家说成是比较早期的高仿品,因为据说是很有当时的笔墨气息,但他却依据这件作品空间构图方式,断定是近代作品。
他说,在这件事情里面,有意思的不完全在于原作与伪作的一般区别,当然,真伪问题也很重要,因为涉及到市场的因素;而他更感兴趣的是作伪这种现象,或者说模仿的现象,即画家如何模仿前代的艺术大师,如何通过模仿来确立自己的位置,这是中国美术史上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23日早晨,我到他的房间跟他告别,他躺在床上,我坐到边上,先跟他说了前一天下午他的研讨会的事情,大家的反响普遍很好,会后,我与他的一位助手植田了裕、盖蒂研究中心的博士后刘礼红、伯克利艺术博物馆策展助理陈芳芳和其他一些参加研讨会的中国研究生聚餐,一起聊到了很晚,他听了后很高兴,说真希望自己也能参加。
另外,我也告诉他,他的数字图像和第一部分的视频录像数据都已下载好,捐给学校的幻灯片也寄回国内了,他的图书馆设计方案已基本定稿了,下一步就要准备施工,我明天就回去了。
他想了一想,然后说:你是知道的,在宋代,中国的艺术和科学的成就在世界上是十分辉煌的,但是近代以来,日本走到了前面。我第一次到中国是在1973年,那时中国刚刚打开大门,而到现在是见证了中国这些年的发展的,也感到很欣慰。
我是坚信这一点的,只要艺术和科学持续发展,中国文化就一定能够重现古代的那种辉煌。在返程的路上,我一直在回想他的这番话,我觉得这是一位把一生都奉献给中国美术史教学和研究的美国学者对中国艺术与文化的世界性价值的一种坚定信念!他的信念对于我们中国的学者而言也是一种激励和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