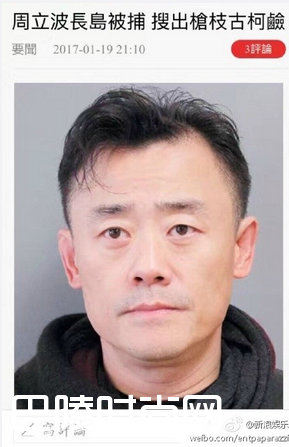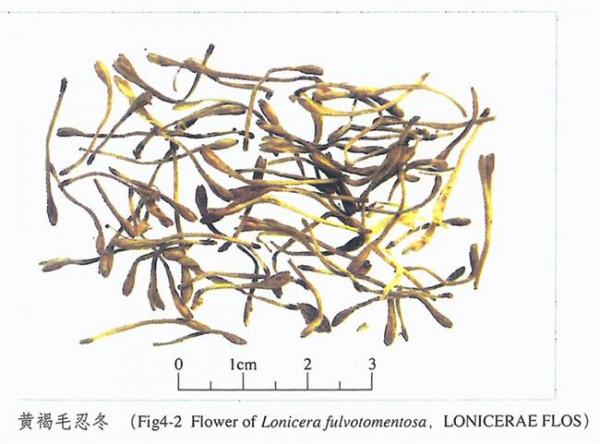章立凡被捕 章立凡母亲曾因家暴与马廷英离婚 后与章父结合
台北青田街七巷六号,是一所日式风格的旧居所。
每个礼拜,马国光都会抽出一天时间到那里当义工,带着慕名而来的访客参观父亲马廷英的故居。这是他从5岁起的家,直至被父亲赶出家门。琼瑶处女作《窗外》改拍电影时,曾在这里取景。《巨河流》的作者齐邦媛初到台北,也曾在此借住过一段时间。
1948年,马廷英在这里,决绝地拒绝了前妻孙彩萍复合的心愿。
对只知李四光的多数大陆人来说,马廷英是个陌生的名字。然而,他却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地质学家、中国海洋地质科学的重要先驱者。他早年从事珊瑚生长节律之研究,是"古生物钟"的最早发明者,后致力于"古气候与大陆漂移"的研究。
1930年代,马廷英已是日本颇有建树的华人学者。因拒绝归化,军政府对他的博士学位授予一直多加阻挠。导师一怒之下,把他的博士论文寄到德国柏林大学,对方立刻把学位颁给他。如此,日本方面也立马批准了帝国大学的学位颁发。他成了日本的4位华人理科博士之一,也是首位华人地质学博士。
回国后,在丁文江"三顾茅庐"之下,他出任实业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技士兼中央大学教授。
1945年,他奉命赴台接收台湾帝国大学。在法币和金圆券全面崩溃的1940年代中后期,他和台大光复后第一任代理校长罗宗洛、陆志鸿,以及后来加入的苏步青、魏建功,仅用一年时间就恢复重建了台湾大学。随后创办台大地质系,出任第一任系主任。
光复初期,岛内民族情绪激昂,大部分台大师生强烈要求驱逐所有日本师生。马廷英和罗校长认为,学术水准来之不易,不可因政治因素而降低。两人顶住压力留下了优秀的日本教授,"以谁再闹事就处分谁"的强硬态度,维持住了台大的教研水准,使其没有沦为一所二三流学府。
台大重建过程中,"接收大员"们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与陈仪为首的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的周旋上。每当罗校长和陈长官因事起摩擦,马廷英就充当调和的第三方,代表校方和陈仪沟通,好像每次都能搞定。
罗宗洛曾在日记里称赞马廷英:"马到成功,真福将也"。罗后因不满于国民政府对台大的支持不力,愤而辞职回到大陆,在"文革"中受尽折磨。马廷英则从1945年赴台后,再也没回过大陆,余生都献给了台大。
1947年2月28日,以陈仪为长官的台北政府人员与民众发生冲突,引发岛上本地人的抗争。蒋介石从大陆调来援军镇压民众,估计有一千至一万五千名台湾人被捕后遭屠杀,这就是台湾史上著名的"二二八事件"。
陈仪后被撤职。1949年1月,他策动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一同投降共产党,被汤告发。陈仪遂被押解至台湾基隆,1950年被台湾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对于这位台湾本省人眼中的刽子手,马国光从父亲那里听到的评价是:"陈仪不是不讲理的,也从来没拿过不该拿的钱。"
1947年,齐邦媛到台大做助教,曾借住马家。马国光叫她齐姐姐。那时,一个叫罗裕昌的青年正对她展开攻势,常来拜访。每当两人单独在房间里待着,身为长辈的马廷英都会大吼一声,"把门开着!"罗后成为齐家夫婿,齐邦媛也常拿这段往事和马家姐弟打趣。
1964年,著名华人计量经济学家刘大中受聘"中研院",返台帮助制定经济政策,规划了税制和退休制度。后一项制度波及岛内包括马廷英、苏雪林在内的一批知名老教授。他们被强制退休,政府仅以一次性发放几十万台币退休金作补偿。
当时马廷英已再婚,膝下新添3名幼子,经济上愈发雪上加霜,连儿女的学费都支付不起。他早已把青田街的私宅捐给台大。那一代的学人极重面子,他不好意思向已成年的儿女开口,更不愿为自己的权益向政府争取。
1979年,马廷英被查出癌症,一直住不进台大附属医院里条件稍好的病房。一名记者以他为例报道了一些知名学者的凄凉晚景。新闻见报后,蒋经国、严家淦等政要纷纷到医院探访。在大人物关照下,他立刻被安排进头等病房,一时成为"红人"。
3个月后,马廷英在台大附属医院逝世,终年80岁。弥留之际,他口中还念叨着地质学名词。
按马国光的理解,父亲是穷死的。"武人哪里懂得敬重读书人!不过,和大陆一比,就强太多了。"
北归:父子残局
"可能是大陆最文雅的男子"——这是马国光形容他对弟弟的第一印象。
一提起这个,章立凡"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他当我是红卫兵。"
事出有因。1988年,马国光到大陆寻访母亲,经停香港时,画家刘国松告诉他:你要小心啊,你那个大陆弟弟肯定是个红卫兵。
作为一位活跃于公共话语空间的历史学者和作家,现实生活中的章立凡和他的微博、著书呈现出三种不同的面目:微博上,是和毛左死掐的"五毛公敌";回忆录里,是悲悯温情的记录者;面对面,则是一个散淡、轻易不流露情感的冷静男子。
"我从来就不激烈。"他说。早熟的个性,源自家庭的一系列变故和个人的遭际。
1957年,父亲章乃器和罗隆基、章伯钧一同被钦定为"右派"时,章立凡才7岁。组织上逼他们母子表态。母亲事先教给他几句话。随后,他上台讲了那几句,大意是:右派分子章乃器虽然是我的父亲,但我还是要反对他,和他划清界限。台下掌声雷鸣。下台后,有人和他热烈握手——那是曾受过他父亲恩惠的人。为避免政治压力,同年9月他进小学读书时,改用母亲的姓,直到"文革"结束。
自1958年被撤销粮食部长一职到"文革"爆发,章乃器一直在北京东城灯草胡同30号的宅院中闭门闲居。从1930年代著名的"七君子"之一,到创建近代史上著名的救国会和民主建国会,性格倔强的章乃器一直是一位"只认真理、无畏权贵"的学者。
从孩提时代开始,父亲就是章立凡的偶像。学校里,他听老师校长讲一套,父亲在家里又和他讲另一套。
"父亲留给我的最宝贵遗产就是独立思考。所有问题他都要让你反着想一想。在那个年代,这太不容易了,许多家长已经不敢和孩子说真话了。"
1963年,章立凡考进清华附中。一次,美术老师布置家庭作业——"我的家"。他回家请父亲坐在书房里当模特儿画了一幅速写。老师将其作为示范在班上展示,画中的人物、陈设、藏书立刻引起同学们的议论。后来,有同学还造了一个词"Capitalist's son"来取笑他,"他们还不知道,我的出身比资本家要糟得多。"
"文革"初,清华附中成为红卫兵运动的发端之地。出身高知家庭的学生和出身干部家庭的学生成了两个彼此竞争、对抗的阵营。1966年,章立凡在校园里贴出一张大字报反对校领导,因他的特殊身份,一时引起轰动。
对于清华附中的年少岁月,他曾写过一篇长文回忆,其中有一段未正式发表的文字,他写道:"我不断忏悔以往对师长的伤害,我不再记恨任何无知者的伤害。人们可以相互原谅以往,但历史从未宽恕过任何罪恶。"
1969年,19岁的章立凡因"反革命"罪入狱。
在监狱里劳改时,他织过袜子,当过钳工,做过图书室管理员,余下时间都用看书来打发。在失去自由的近十年里,他前后读完了五六百本书,其中有不少马恩列斯毛著作,母亲来探监也会给他带一些英文书。因为书得来不易,他看得很仔细,"很多内容过目不忘"。
40年后,每每和"毛左们"网上辩论,他随时能从"红色著作"里引经据典,以彼之矛攻彼之盾,毛泽东如何说,列宁如何说,马克思又如何说等等,这正得益于这段岁月的修炼。
1976年,他从北京第一监狱被转押出。当时毛泽东刚刚去世,政局动荡不安,监狱里风传要枪毙一批"反革命"。他的忽然消失,让狱友们一度以为他已被枪决。
等转押到延庆监狱,章立凡才明白过来——这算"人才引进",当时延庆监狱需要一个编内刊的囚犯,就把他这个有文化的小年轻给调过来。
回忆监狱10年,章立凡一副置身事外的淡然,仿佛在讲一段与己无关的过往:监狱里的管理还算正规,"不像现在,没有什么躲猫猫、喝凉水死";狱友为老弱病残,其中有一队全是疯子……"人经历多一点也是好事,各种各样的日子都会过。"
这和他儿时的"小愚姐"、章伯钧之女章诒和形成对比——两人同为民主党派人士和"大右派"之后,同在浩劫中被打为"现行反革命",黄金岁月入狱10年。章诒和以她在四川监狱的经历为样本,写出一系列凄烈的女囚小说(《刘氏女》、《杨氏女》等)。
"这大概就是文学家与史家的区别吧。在我们搞历史的人看来,这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在过去都发生过。"章立凡淡淡地说。
他的几部回忆录的手稿,因为政治原因,在大陆还出版不了,"放着,我不急。"
章乃器的长女1949年后留在台湾。其女到大陆探亲时,曾和舅舅章立凡提及母亲说过的一段秘史: 章乃器1948年曾秘密到过台湾,"是老蒋请他去的,但是,两人谈崩了。"
一段有公开记载的历史是这么说的:1948年金圆券崩溃时,陈诚建议蒋介石启用章乃器,蒋说,"我是想用章乃器的,但他不为我所用啊。"
"我大姐对她女儿讲的这一段,究竟跟我父亲说的那一段是不是同一件事,我现在还证实不了。不过,到最后阶段,中间力量就变成站队了。你必须在国共之间选择,要么选择南渡,要么选择北归。"
对父亲,章立凡也有批评。"其实,他不懂中国政治,只是一个专业型人才。"
南渡之二:亚细亚孤儿
1960年,台北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案件:一名15岁的眷村少年连捅7刀,杀死了女朋友。以此为蓝本,杨德昌拍出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这一年马国光18岁,和这起案件相关的几位"外省二代"都是他的伙伴。自儿时起,他常跑到青田街附近的眷村看电影。
那时,马国光是大人眼中的"坏孩子"。功课差,不做作业,逃学,留级,离家出走,常挨父亲、姑姑和姑父打骂。他在街头闲逛,认识了不少人,有流落台湾的老兵,朝战中到台的"反共义士",偷卖走私货的南洋侨生……
那时,整个台湾都打着激昂的"战斗"鸡血。中小学里布置像《我的理想》一类的作文题目,大家就写"反攻大陆"。"写明年就回南京吃月饼,我们终于又怎么样。也不一定得高分,因为人人都写,属于瞎扯。"
直到有一天,一位江浙口音的陈老师在升旗仪式结束后上台讲话,叮嘱大家以后作文千万不可再把"我的志愿"写成"反攻大陆",因为——"反攻大陆等你们还了得?"这位陈姓老师后来做过"中华民国"的教育次长。
1960年9月,《自由中国》刊登了殷海光执笔的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3天后,第一发行人雷震被捕,后以"知匪不报"和"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的宣传"等罪名,被处以有期徒刑10年。
马国光在周记里写了对雷震的同情。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说小孩子不要谈政治。"我很气那个老师,我们为什么不能谈政治?长大了才知道,是老师替我担待了。"
艺专毕业后,他在中广断断续续打零工。因为觉得自己对社会有很多意见,就写了一摞文章寄到台湾各大报纸。后来,《中国时报》刊发了他的评论,主编辗转找到他,邀他写专栏。
马国光一写就是30年,从蒋介石时代一直写到蒋经国执政、李登辉上台。
在台湾"动员戡乱"的年代,写时评很难不惹上麻烦。有一次,他在报纸上一再呼吁政府放开30年代左翼作家的书。警备总部遂向余纪忠主持的《中国时报》提出正式抗议,并提出约作者"来吃一顿饭"。
"我说,我不来,你们那个地方都有卫兵站着,一个招待客人的地方不是那个样子。你们如果要跟我谈,我们可以约在外面。"
马国光是一个坚定的"统派",属"亲蓝"阵营。
1990年代,台湾开启民主化进程。因为口才好,语言有感染力,他被国民党党部拉去做"文胆",也曾做过大选助选人。"两三个人分工,在家里(替李登辉)拟演讲的稿子,旁边有文工会的小姐先生坐着等。没意思,等出来,也就只用上你写的几段话。"
有一年,他到高雄助选。当时,民进党候选人余陈月瑛和国民党候选人黄八野争夺高雄市长之职,两人势均力敌,战况惨烈。
赶到地方党部的下午,马国光看到一张让他很不舒服的宣传照片,拍的是余的公公的坟,坟上长满野草,大意是说余家后人如何怠慢先人。
晚上,他们来到决定选举成败的大票仓凤山。马国光先上台讲,讲完了下来,轮到其他助选讲。待主角黄八野上台,"他开始讲他被人中伤,多么倒霉。他为了要票,就下跪了,老婆、女儿、助选在台上一起都跪下了。"
"你是要跪下来为民服务么?哀求老百姓为民服务吗?这不是扯淡吗?不入流!"他一言不发,立刻叫了计程车到火车站,当晚回了台北。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涉足政治活动。
一谈到台湾的政治传媒生态,马国光很容易动气。他抨击民进党不争气,说台湾没有一个像样的反对党。当记者问为什么"人人都骂马英九",他的怒气又蹿了上来——"马英九是个君子。骂他,你不吃亏;肯定他,你倒会惹麻烦。"
"不过,现在看来,台湾还是走对了路子。"稍稍平静后,他又肯定道。"什么时候两岸能统一呢?就等到大陆人不再羡慕台湾人,时候就到了。"
马国光坦言自己喜欢美女。年轻时在中广打零工,他追到了台里有名的美人、西洋音乐节目女主播陶晓清,她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台湾民歌之母"。
母与子:台湾的主人翁
19岁时,声音清澈、典雅的陶晓清就成为中广《热门音乐》的主持人。
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极度崇洋,年轻人戴着蛤蟆镜,弹着吉他,哼唱西洋和日本歌曲。那时,陶晓清在节目里介绍披头士、滚石乐队等欧美流行音乐,受到青少年的追捧。
1970年代起,台湾在国际舞台开始节节败退,先是被赶出联合国,接着美国和中国建交,过去的"邦交国"一个个都断交了。岛内,一种极为复杂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新一代知识分子中萌发、酝酿。
1975年6月,在一场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上,陶晓清的心一下子被歌手杨弦唱的余光中诗作《乡愁四韵》击中。在"唱我们自己的歌"的冲动之下,她在自己节目中播出演唱会的现场录音。意外的是,来信如雪片一般飞来,要求她多播一些中国的民谣。
受到鼓舞,陶晓清开始搜集音乐圈朋友的作品,在节目中推介了一批本土的原创作品和歌手。台湾各地音乐人纷纷把作品寄给她。那时,一个歌手只要作品在陶晓清的节目中里播出,离大红大紫就只是一步之遥了。
1976年新春,在中广的支持下,陶晓清组织了台湾民谣的第一次演唱会,取得空前成功。这一年被视为"台湾民歌元年",陶晓清也渐渐脱离单纯的广播人身份,成为"台湾新民歌运动"的最重要推手。
她联合媒体界与音乐界,与诗人余光中和滚石唱片创始人段氏兄弟一起,共同策划举办了多场"中国现代民歌"演唱会。这是台湾的音乐原创力量第一次有组织地展现,杨弦、李双泽、胡德夫、杨祖珺、吴楚楚等开始走上前台,成为台湾流行音乐早期的生力军。瑞安街的马家寓所,也成为闻名台北的"民歌客厅"。
从70年代到90年代,台湾新民歌运动的许多大事都在这里起头。吴楚楚、胡德夫、苏来,还有之后的李宗盛、蔡琴等等,常坐在榻榻米上,无拘无束地聊音乐,开座谈会,组织和策划音乐演出,接受采访。 陶晓清是音乐沙龙的女主人,活动的策划组织者,也是爱护、关照他们的"母亲"。
1980年,一脸青涩的李宗盛首次被朋友带到马家客厅,自卑地躲在一角听大家唱歌,是陶晓清发现了他的才华,把他带进自己组织的很多音乐活动中。蔡琴性子急,容易得罪人,陶晓清就帮她和别的音乐人搭起沟通的桥梁。"孩子们"肚子饿了,她就到厨房里给他们做蛋炒饭、牛肉烩饭。
在陶晓清引领的现代民歌运动影响下,台湾两家本土唱片公司先后创办"金韵奖"与"民谣风",商业力量开始接管现代民歌,齐豫、潘越云、黄韵玲、庾澄庆等音乐人走上前台,台湾流行音乐从此迈上正轨。
90年代后期,陶晓清渐渐从话筒前淡出,但她依然是台湾民歌的支柱,从创办"民风乐府"到"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她一直在出力。2000年,她获得台湾金曲奖"特别贡献奖"。
如今,马家第三代马世芳接过了母亲的旗帜。
1971年生的马世芳有"台湾头号文艺青年"之称。他是台湾知名DJ、乐评人和散文作者。在叔叔章立凡眼里,"无论是按台湾的标准,还是大陆的,都是一个优质好男孩"。
从小在父亲的书堆和母亲的卡带、唱片堆里长大,他早早就与音乐和文字结缘。就读台大中文系期间,他主编《台大人文报》,同时在母亲开辟的中广"青春网"介绍经典摇滚乐。毕业前夕,他联合几个同学合编了《1975-1993 台湾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这本校园印刷品,后被视作台湾音乐史的经典文献。
2000年,他创办"五四三音乐站"。2006年出版的散文集《地下乡愁蓝调》,获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最佳书奖"。
一说起儿子马世芳,马国光是满心的骄傲。有着旧文人气的父亲,听的是京剧、昆曲;一身休闲装的儿子,迷的是鲍勃·迪伦和摇滚,致力于台湾本土流行音乐的整理与推介。
在马家,父子之间有一个甚少触碰的话题——政治。作为台湾"六年级生"人,马世芳对台湾意识、两岸关系有着完全不同于父辈的认知。
撰文回忆台湾流行音乐史时,他常会谈起罗大佑的两首歌——《亚细亚的孤儿》和《未来的主人翁》。他说自己这些年曲曲折折,忙忙碌碌,只因心里记着《未来的主人翁》的歌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