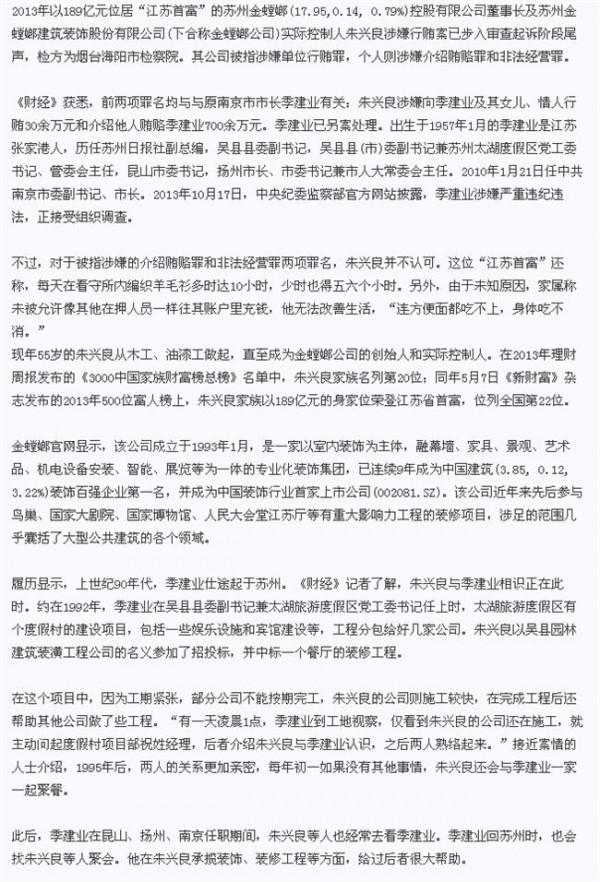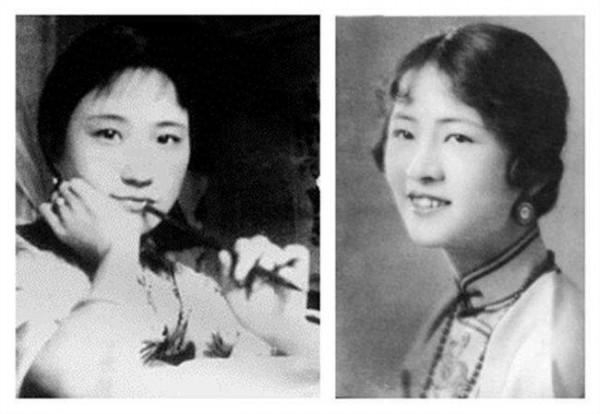木凸陆天明 [木凸] 陆天明 文字版 pdf
木凸陆天明序三十年了。我的文学创作又走过了三十年的路。是“一竿风月”,还是“一蓑烟雨”,抑或是“波涛万顷”?上小学三年级时,写作文:《我的理想》。我说我要当“作家”。我上学早。写作文的那年我七岁。我那个被多年的肺痨病已经折磨得几乎要对生活失去希望的父亲,看到我的那篇作文,非常欣慰地说:“好啊。
我儿子也想当作家了。”他年轻时的理想就是要当作家。但不幸的是,他是巴金笔下“觉新”式的人物,一个大家族的长房长子,终归屈服于生活的压力,为了顾全家族的生活“大局”,无论哪方面,都“痛苦”而又“自觉”地放弃了他个人的理想。
三年后,他死了。还是死于肺痨。死的时候才三十岁。在此之前和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并不知道他曾经想当一个作家,并不能体会那天晚上他站在写作文的我身后,所发出的那一声喟叹里所饱含的全部伤感意味。
也许他活着时,觉得我太小,就没想到还有那个必要跟我细细地说说这些。又过了十年,我离开上海,离开母亲,要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战天斗地”。
母亲为我准备行装。全部的行装就是一个旧帆布箱和一个旧铺盖卷。她却把父亲十九岁时发表的一些小说和诗歌,还有抗战时期他流亡昆明一路上写的日记当作唯一的“遗产”放进了我的行李里。
我这才知道自己和毕生经商的父亲在精神上一度是多么的接近。两代人的文学梦,两个世纪的挣扎生涯,让我觉出许多的心酸和沉重。所幸我迅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社会变革的大洪流中去了。我可以活得和父亲不一样。
虽然,我也曾得过肺结核(是父亲传染给我的?说不清),但我可以不再用一个“旧时日肺痨病人”和“只属于一个大家族”那样的苍白软弱和绝望去处置自己的一生,去处置自己的文学梦。大西北农场难以想象的艰苦贫瘠,不仅让人同样难以想象地彻底治好了我的肺结核,还给我心底铸进了西北汉子常有的那种倔强和愚拙。
大概就是因了这种“倔强和愚拙”,农场十二年,我一次又一次主动放弃了种种充满另一类诱惑的人生选择,执着地在那戈壁荒漠上做着文学梦。
一九七三年,在到农场的第十个年头,我终于写出了平生第一部“大作品”,一个知青题材的四幕话剧《扬帆万里》。这部作品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关注。西安电影制片厂要将它拍摄成电影。上海要发表它。兰州北京西安乌鲁木齐以及东北和别的一些地方的大大小小的剧团将它搬上舞台演出。
其实那时候,我一共只看过三个国产的剧本:《槐树庄》《第二个春天》和《年青的一代》。只看过一个话剧演出,还是那个永远激动我的《年青的一代》。
那还是在离开上海前看的。后来在农场宣教组仓库里,翻拣到一本契诃夫的戏剧集,半本易卜生的剧本集。记得当时反反复复地读,一直到把它们读破。也就是像罗兰·巴特说的那种“抬头阅读”,读一段,抬起头来默想细究,“将其切割,亦因迷恋,又将其恢复,并从中汲取营养……”我的倔强和愚拙,同时也体现在:我写作,只是觉得自己心里有话要说,要对这个世界表白什么。
我要叫喊。要喊出属于我的那一声来。在底层的十多年生活,面对这个世界,我总觉得自己心里有太多的话要说,有太多的声音要发出。
总是直觉到,这个世界需要这样一种声音。这愿望,这直觉,这冲动和向往极其真诚而又无比强烈。甚至强过初恋时的那种可以说无与伦比的冲动和向往。
至于这样喊出的“声音”是否时下或教科书上界定的那种“文学”,我不管。也许正是因了这种愚拙的真诚,我的这第一部“大作品”在当时确实打动了不少的人。后来,也是因了这部作品,我才被北京一个专业文艺团体看上,把我全家调进北京。
我也因此开始了自己三十多年的专业创作生涯。但我创作上真正的新生,却开始于“四人帮”倒台。“四人帮”倒台,让起步于“文革”期间的我,有可能开始一场彻底的“蜕变”。这对我个人,对我这一代人来说,在精神上,具有哈姆雷特式的“绝对意义”:“是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道必须跨过去的大坎。
当文学艺术的春天重归人间,文学艺术创作将充满艺术个性地回归到它的本真意义上来。因为时代使然,我们这一代人曾经一度失去过,或者说忽略过自我和艺术个性,而要重新找回自我,谈何容易!
要重新确定自己的艺术创作个性,同样“谈何容易”啊!我们必须要像幼蛇蜕变那样,从紧紧包裹束缚着自己的“旧壳”中蠕动挣脱出来,必须先用锋利的“手术刀”细细地解剖自己。
需要认真地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人”。而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恰恰是认识自己和认识“人”这样一种最复杂又最完美的“东西”。是自己拿着刀,一刀一刀地切割自己的肌肤。
是舐食自己的血水,以此去重新获取新生的力量。我用整整一年的时间彻彻底底地沉到一个钢厂里去生活。每天跟着工人三班倒,春夏秋冬、日日夜夜,以重新获得普通人的生存感觉,站在普通人的立场去重新认识眼前的这个世界,借此来摆脱那个旧我。
同时又大量阅读能找到的新小说、新理论著作。并且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桑那高地的太阳》,用它来回顾自己这一代人是怎么失去自我的,以从容告别过去。然后又写了那个《泥日》,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