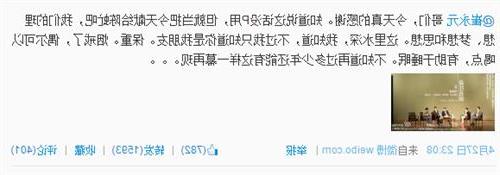央视陈虹 央视制片人陈虻是一个怎样的人?如何评价他的功过?
2002年病好了以后,我回来做《小崔说事》,抱着混一混的心态。我也干不动了,也没心思干了,糊弄糊弄就完了。我已经完全掌握电视的规律,知道怎么回事,那节目25分钟,我要讲3件事,三七二十一,每人7、8分钟,观众刚一疲倦就换一个人讲故事。
那个节目收视率极高,永远排在新闻频道前三名前两名。其实是投机取巧。他们问我怎么做到的。我说要给我一个15分钟的节目,我能弄得收视率更高,让观众来不及换台就播完了。 我内心里其实是看不上那个节目的,一辈子做那个东西,收视率再高也没意义。
陈虻那个时候已经当副主任了,他审我的片子,很不满意,但他体谅我,知道我生病,还去看我了。 片子里现场观众连连爆笑,他坐在那儿一点表情都没有,我就知道他心里怎么想。
他不希望我这样,但又不想给我太大的压力,也不知道怎么和我说。每次去找他签字,他还问我身体怎么样。我说挺好,然后就走了。其实我很难受,我也知道这么做不好,但我当时没能力了。 我非常在乎他的评价。
我精耕细作我的《电影传奇》,别人也会顺势夸两句好,做了一年他也没表态。有一天他说,你知道这叫什么?这叫作品。什么叫作品?兄弟,这是一年只能做10集的,你做成了周播节目,了不起!所以我和我们的编导说,你们干的是作品,别拿着当个活儿干,别想着编一集挣几千块钱,咱们要对艺术负责,要对良心负责。从今天起就好好完成我们的作品,不必再去管什么收视率。
我一直佩服业务领袖,佩服那种具有船长气质的人。陈虻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对电视的把握实在精准,并且具有前瞻性。陈虻想出来的那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其实是那个年代《东方时空》很本质、很精髓的表达。那不是一闪念冒出来的,那是他长久思索,在某种启示下得来的。
他本人是那样一个干净而浪漫的人,对人的态度、对人的眼神,都让人觉得干净。他做的事,无论动机还是方式都是干净的。有才华的人很多,有才华又干净的人很少。这两种气质混杂在一起,很动人。在我心里他是知识分子。不是念过大学就能称为知识分子的,有的人就是拿到博士学位也不算知识分子。
陈虻对电视非常非常执著。他是为电视而生,为电视而狂,可能也是为电视而走。他的很多想法没实现,走得不愉快,是个悲剧人物。离开那天,时而昏迷时而清醒的交替中,他对一直照看他的好朋友、《社会纪录》的制片人李伦说了一句:“话语空间。
”李伦告诉我的时候,我心里就像涌起滔天巨浪,一下就被打蒙了。他病了两年了,怎么最后还想着这样一句话。 一想到他走了,我心里就凉凉的。我们的队伍开始减员,我们的势力开始削弱。不是帮派势力,而是那种志同道合、惺惺相惜的力量在削弱,这是一种很悲凉的感觉。
突然间身边的战友倒了一个,让人害怕深想这意味着什么。这是你不愿意,不相信,甚至不敢去面对的东西。大家心中可能有某种情绪,有对那个纯粹年代的追忆,对现状有埋怨,又不知道去埋怨谁。
我们的痛苦和感伤不仅仅因为失去了这样一个好哥们儿、好同事、好朋友,而是他的离去,忽然把生活叫停,让我们停下来追忆。怎么说呢,就感觉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也远去了。 陈虻离去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他太寂寞了。以前我当制片人的时候,每个月都会把我喜欢的书、读过的书选个两三本给组里的人买,也会留几本给他。每次他都会跟我交流,他一直在看。后来我辞去制片人的职务,他常跟我开玩笑:“哎,怎么不送书了?”我一笑。
其实后来我挺后悔的。他要的是书吗?我这几天一直在想他跟我说话时的表情。那是一个非常寂寞的灵魂,他希望交流,他有太多的想法了。 你想想,他能够让《生活空间》横空出世。1998年5月1号的《读书》杂志,第一篇文章就是讲《生活空间》的,当时给了我们很大的振奋。
突然你看到电视除了娱乐功能、影响力外,还有社会和文化的价值。《东方时空》之前,电视是有收视率、有影响力的,但很少会赢得这么大的尊重。现在回头看,那个时代当然值得怀念。
我在这个院里跟他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你怎么还没吃饭啊!”我经常见到他中午一两点了还在那儿跟人家讲节目。我就着急,你怎么还不吃啊?偶尔,中午两三点了,在食堂看到他,永远坐角落那张桌子,吃一盘饺子,周围又一堆人。他是爱思考的人,讲话非常有趣,任何时候都精彩而绝无重复。拿录音笔录下,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好文章。
讨厌的是,他永远是对的。 八年来,我始终跟他较着劲,他说什么我都顶回去,吵得厉害的时候,电话也摔。 今年教师节,我给了他发了一条短信,说“好吧,老陈,我承认,你是我的导师,行了吧?节日快乐” 在精神好的时候,他的短信回得很长,说他在深夜里好象能感觉得到舌头上细胞一层层滋长出来,头发荏子拱出头顶,说“饿的感觉真美好”。
一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也一直大睁着眼睛,没有麻木和畏缩过,他跟我说过“人可以被打死,不能被吓死”。
是他要求医生不要抢救的,他想有尊严地离开。与他告别时,我握住他的手,温暖柔软。这是八年来,我第一次与他如此亲近。 在这个混乱不堪的世界上,他始终向真而生,没有泯灭过自己的心灵,并非因为他的道德,而是因为他对世界的认识和对生命的热爱。他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标准和灵魂。 他的丧失,我们将要用漫长的时间来体会。 但是,只要我们心存对他的记忆,陈虻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