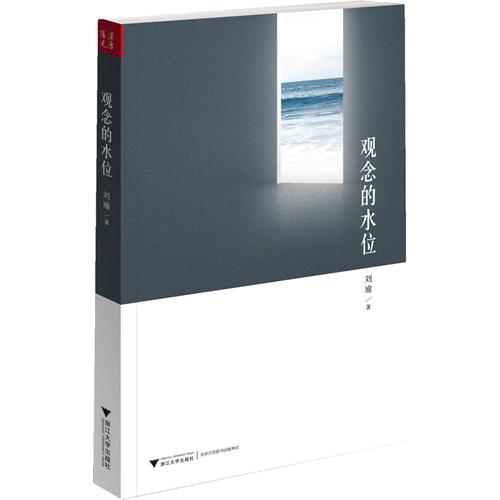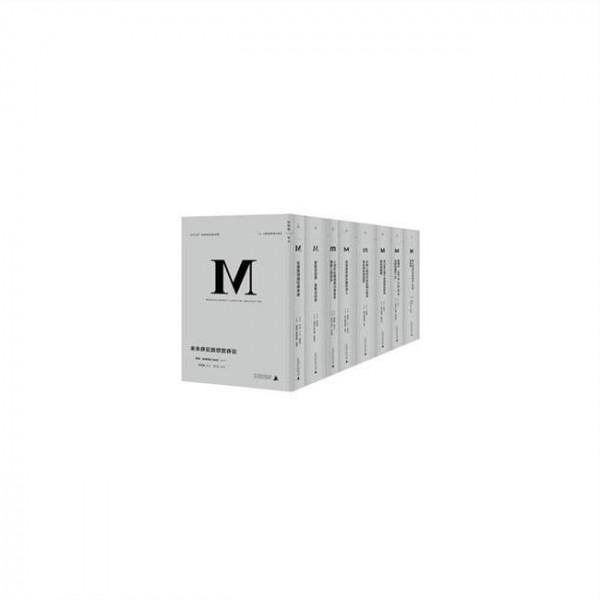评价刘瑜 民主及其半径——刘瑜评《民主的阴暗面》
民主化之所以可能加剧冲突,原因在于民主内置的“多数原则”——“多数”对这一原则的滥用,以及“少数”对这一原则的恐惧。如果一个“少数”群体在威权时代还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的话,“多数原则”就意味着前统治集团被扫地出门。
迈克尔•曼的《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如果与R.J. Rummel的《权力杀戮:民主作为非暴力的一种方式》同时阅读,将是非常有意思的阅读体验。同样最初出版于2005年,两本书所传达的意思却截然相反:前者试图论述“民主化加剧族群冲突”,而后者想说的则是“民主缓冲社会的暴力程度”。何以两个学者对同一制度的暴力后果判断截然相反?哪一种判断更接近事实?
《民主的阴暗面》讨论现代化危机
曼的观点模糊印证了我们一些印象式认识:比如2001年美军入侵之后,阿富汗死于战乱的人数达4万多;而2003年萨达姆倒台以后,伊拉克死于战乱的人数则高达17万左右。此类众所周知的案例显示,贸然“移植”民主带来的可能是灾难,而非“公主和王子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然而,盲人摸象摸到象腿后还要继续摸下去,否则看到的只是“局部的真理”。据统计(参见“重大政治暴力事故”数据库),阿富汗在2001年被卷入民主化进程之前,死于塔利班时期和之前苏军占领时期战乱的人数高达100万;而伊拉克在“被民主化”之前,上世纪60年代以来死于库尔德冲突的人数就高达15万,死于宗教派系斗争的人数是2万-3万人,而死于两伊战争的人数是50万,第一次海湾战争则导致10万人死亡。
可见,至少就伊拉克和阿富汗而言,似乎专制时代也并非莺歌燕舞的人间天堂。单就死亡人数而言,甚至专制时代“完胜”转型之后,虽然近年这两个国家的“半吊子民主化”也的确乏善可陈。
那么,曼为什么将族群屠杀归咎于民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民主”这个概念做了非常广义的解读。在他的书里,不但“自由公正的定期选举”(当代学界对民主的主流定义)被视为“民主”,纳粹的统治和斯大林主义的阶级专政也被归入“民主”范畴;不但选举前后的暴力被视为民主的问题,围绕着“伪选举”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发生的选举所发生的暴力也被视为民主的后果。
由于现代社会几乎所有国家都借用“民主”的话语建构其合法性并组织某种形式的“选举”,因此某种意义上,几乎所有现代社会的大规模冲突都能与“民主”挂上钩。如此宽泛的定义当然能引出“指哪打哪”的结论,但是过于宽泛的定义也造成对结论信息量的稀释。
仔细阅读,会发现曼所讨论的,与其说是民主化的危机,不如说是现代化的危机。所谓现代化危机,首先是指“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的挑战——各种组织、派系、族群在角逐暴力垄断权过程中爆发的冲突——这一过程几乎不可避免地引发暴力冲突,无论它是否指向民主化。
无论是前南斯拉夫地区上世纪90年代的冲突,还是德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崛起,或前溯到英国在克伦威尔时期对爱尔兰、苏格兰的征战,或甚至再前溯至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其暴力有效垄断程度而言,被福山称为最早的“现代国家”),“国家建构”一般来说总是伴随着血腥暴力,这一点并不以“国家建构”之后到底建立了什么性质的制度为转移。
与分封制下的王国、教区、自治城市等“产权模糊”的前现代政治单位相比较而言,现代国家的“排他性”主权观念注定了通向它的道路是一条血雨腥风之路。“率土之滨,莫非王土”,肯定不是举国民众摇着鲜花、铺着红地毯所开拓。
现代化危机的另一个层面就是所谓“富国强兵”的挑战。这几乎是“国家建构”进程的必然逻辑。一旦政治竞争以“国家”为单位展开,“落后则挨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投射到国际体系当中,以集权为特征的国家主义就有了生存意义上的辩护。
为了“祖国”的强大,任何对个人权利的计较都显得过于布尔乔亚。这一点在后发展国家中格外明显——“挨打”之后的奋发图强总是格外悲情。“富国强兵”成功了,一不小心可能变成军国主义(德国、日本);不成功,则对内专制变本加厉——打不过外敌,回家“打老婆”总还有力气——瓦解中的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就是实例。
因为“国家建构”与“富国强兵”的挑战,几乎所有国家在成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都有过血腥一页。这种血腥之所以常常体现为“种族清洗”,多半是在建立“我们-他者”的过程中,种族是最便捷现成的人群区隔方式(想想划分“富农中农贫农”的组织成本)。
我们常常惊异,图西族和胡图族外形如此相像,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人语言十分相近,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基因上几乎是同一个人种,何以打斗起来如此你死我活?或许重要的,不是到底一个族群和另一个族群有多么不同,而是国家建构需要并奠基于那些想象的不同。
悲剧之前奏常因权力解除有效制衡
那么,专制或民主,与现代化过程中的这种冲突过程是否存在联系?是否一种现代化路径比另一种路径更可能加剧族群暴力?这个问题之所以很难回答,原因不仅在于经验现实本身的多样性,而且在于在“冤冤相报”的历史逻辑中,研究者难以分离专制的后果与民主的后果——一个杯子摔碎了,到底怪那个撞到它的人、还是怪那个一开始就没放好它的人?布隆迪1993年第一次大选后,发生了种族大屠杀,但是此前的专制时代,有过规模更大的种族屠杀,账到底从哪里算起?
这也是为什么相关的实证研究很难得出一锤定音的结论。从逻辑上讲,专制常常恶化种族屠杀与清洗,原因在于缺乏制衡。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一般总会将社会的多元性投射成政治的多元性,而多元性构成制衡。如果当年成吉思汗的蒙古包像1968年的白宫那样,前面站着成千上万的反战游行示威者,多半蒙古军横扫欧亚时的各种屠城也难以发生。
理论上,当然可能全民嗜血,但是如果没有精英操控的环节和信息屏蔽的环境,全民“失心疯”的状态似乎极少出现。而精英操控加上信息屏蔽,就意味着专制本身。所以,哪怕希特勒经由民主选举上台,他也需要在取消国会与选举、实行言禁党禁、摧毁公民社会之后才可能完成如此血腥的种族屠杀。
从史实上而言,二战结束以来最血腥的内战,也往往的确发生在专制体制之下:从柬埔寨的屠杀到苏丹达尔富尔的屠杀,从安哥拉内战到乌干达阿明政权的暴政,血腥悲剧之前奏,往往是权力解除任何有效的制衡。Steven Pinker观察到二战以来全球暴力冲突规模显著减少,这与同时期全球民主政体的爆炸式发展亦步亦趋,或许并非巧合偶然而已。
即使观察曼在书中举到的例子,我们也会发现,从纳粹德国到卢旺达,从亚美尼亚到前苏联,不管激进民众在仇恨的煽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最恐怖的政治暴力往往由“国家”组织完成。任何一个社会都有族群或阶级冲突,这种冲突常常引发暴力骚乱,但是只有政府的有组织参与才会使这种暴力骚乱升级到屠杀式清洗的程度。
这未必是因为政府比社会“更恶”,而是在施恶的过程中政府比社会“更能”。这一点曼在分析为什么印度没有出现屠杀式清洗时也曾指出:族群暴力骚乱在印度此起彼伏,但是为什么没有酿成卢旺达式的屠杀?答案在于,哪怕是“拉偏架”,政府最后总是以调解者而不是屠杀组织者的身份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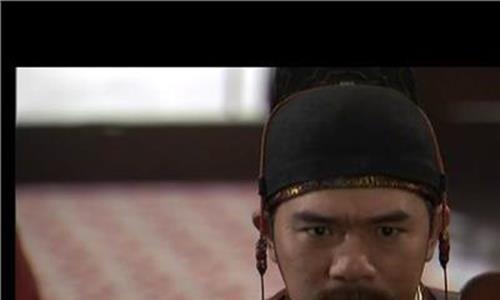
![观念的水位刘瑜 [一种声响]刘瑜对谈慕容雪村:观念的水位增加一毫米](https://pic.bilezu.com/upload/3/99/3995187d952748e79749feba4848466a_thumb.jpg)
![观念的水位刘瑜 [一种声音]刘瑜对谈慕容雪村:观念的水位升高一毫米](https://pic.bilezu.com/upload/d/81/d818d8221da11955d242a2e23fabab5e_thumb.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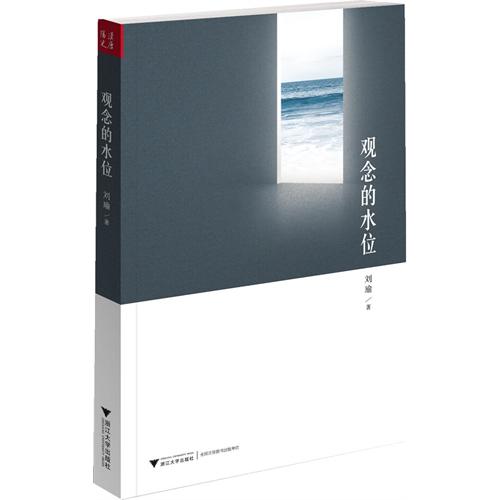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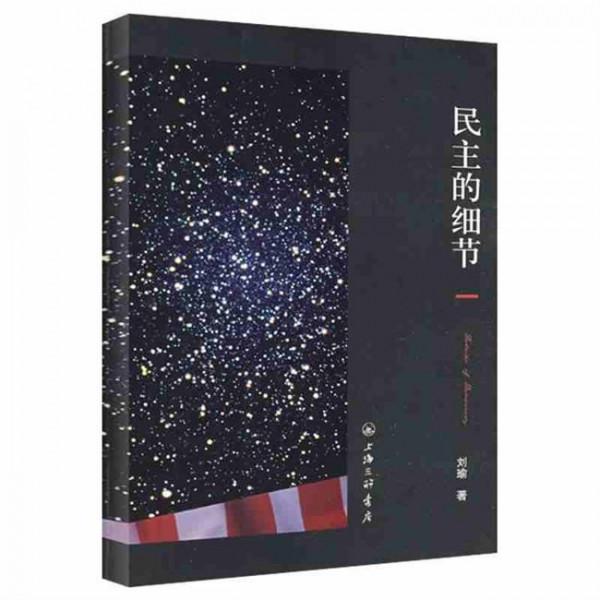


![>刘瑜当当 观念的水位 (《民主的细节》作者刘瑜新作)[当当]](https://pic.bilezu.com/upload/f/d5/fd5c0d73854f0ea1a77401683dc90c4f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