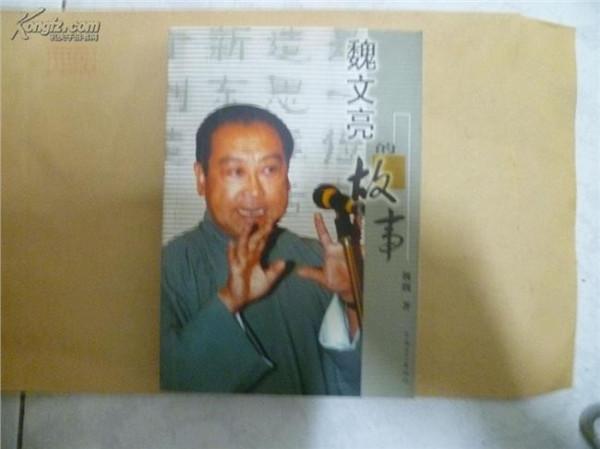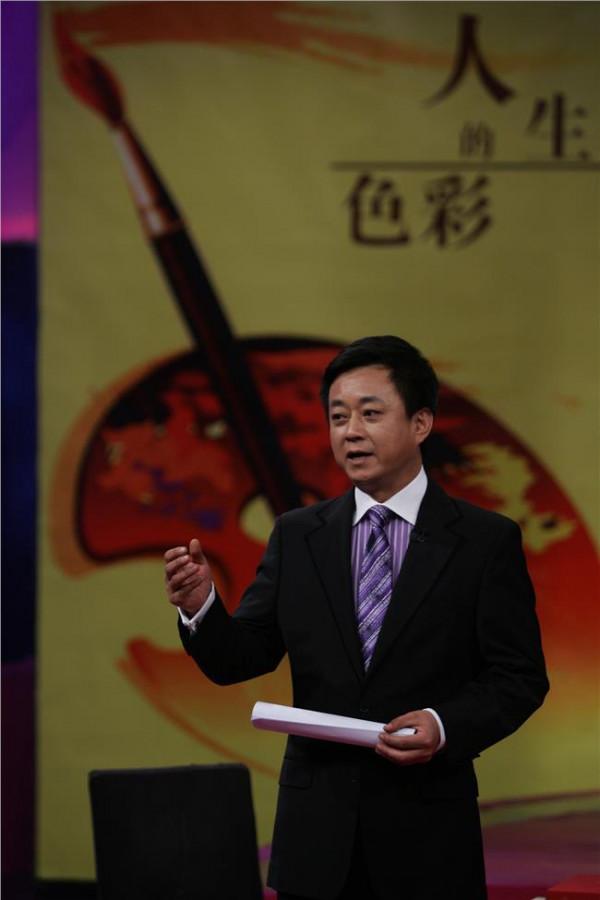魏文亮的艺名 魏文亮的艺术人生
记得儿时每到下午5点钟,当家家户户的烟囱里飘出袅袅炊烟的时候,打开收音机,《每日相声》节目总能让我从每天晚炊那段平淡的时光中,享受到相声给我带来的快乐。也是从那时起我熟识了魏文亮和他的相声。
萌生为魏文亮先生做专访的念头来源于单位领导的几次勉励,可一次次却总没有找到魏先生的联系地址。好事多磨,今年年初无意中浏览网页时看到了魏文亮先生的单位电话,打过去找到团长室,几经周折得到了魏先生的宅电。电话找到了,我的顾虑也来了,作为一位闻名全国的相声演员,每天的演出等事务繁忙,不知人家是否愿意接受采访?两天后,我终于怀着忐忑的心情拨通了电话。
“我是《天津日报·今日东丽》的记者,因为知道您是东丽区走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想对您进行一下专访?”“是的,我是东丽人,……”
一句我是“东丽人”释怀了一切的顾虑,尘埃落定。在一个阳光充足的早春,我走进魏文亮先生普通而又温馨的家。魏文亮、刘婉华夫妇俩热情地接待了我。稍事寒暄之后我们便直入了主题,与舞台上活跃、幽默的形象不大一样的是,采访中的魏文亮更显亲切与平和。
访谈进行了三个多小时,随意而又自然,不像是采访,倒完全像是在进行着一场随适的唠嗑。最后当我说到前些天看到你们夫妻做客《津夜嘉年华》的表演时,一直在一旁相陪的刘婉华女士还优雅地摆了一个表演白毛女时做的动作。
提到东丽,魏文亮总有说不完的感慨:“东丽区这么多年来的发展很快,在我的印象里应该是比哪个区的发展都快,作为东丽老家人我们脸上有光彩啊!据父亲讲,当年东丽是相当贫穷的。我的老家在东丽区赤土村,那里最早叫赤碱滩。
听听名儿你就能想到,种什么,什么不活,因为碱大啊,所以当时是有名的穷村。我父亲从20多岁时就从家里出来了,因为父亲当年出天花,病毒攻到眼上了,结果视力越来越弱,以至到20左右岁时就完全看不见了,成了盲人。
在老家,我父亲一共哥四个,大大爷给人帮忙盖房时被树桩砸死了。三大爷被日本抓了华工,最后死在东北。剩下一个二大爷,一直生活在村里,他是个雇农,比贫农还要穷,常年给地主扛活。在那个年代,农民没有文化很苦啊!
因为父亲眼睛不行,在农村根本没法生活下去,所以最后父亲想来想去,决定出来。这样就独自流落到市里。开始时是和一个算褂的先生学算褂,以此谋生。过了几年,他觉得这个行业实在是骗人,在良心上过不去,就说什么也不干了。好在他在学算褂时学了一点三弦,于是就在这方面下功夫,给天津的时调、小曲、老鸳鸯调演出伴奏,这样就算是走进了文艺行当。”
魏文亮介绍,他的父亲在村里的魏氏宗族中的辈份是很高的,早年间他陪父亲回去时,村里许多年长的长辈见了也要喊声四爷。说到这,魏文亮的眼睛里露出了一股悠悠的回望:“二大爷死时应该八十多岁了,他一生都生活在赤土老家,靠务农为生。
因为老哥四个只有魏文亮一个男孩子。所以他去世时我是帮着他的抱子魏其海一起料理的后事。”说到这,魏文亮的夫人赵婉华说:“老家的亲人不多了,所以自从二大爷去世后就回去的少了。但每次听到老家的消息我们还是很关心,尤其是这些年知道东丽的发展迅速,更是从心里高兴。
”当我介绍了现在的赤土村和周围的十几个村都迁进了华明示范镇的新楼房时,魏文亮啧啧地称叹着,“你瞧瞧,发展真是快啊!当年记得二大爷去世时还是三间小土坯房呢……”
艺术道路上的探寻者
6岁出道的“小怪物”
魏文亮出生在一个艺人家庭,父亲魏雅山是一位弦师,母亲张墨香则是一位老鸳鸯调演员。据魏文亮介绍,新中国成立之初,母亲曾得过天津市曲艺表演一等奖。新中国成立前,大多数艺人们都是穷困潦倒。魏文亮一家也不例外。
生活实在维持不下去了,父母决定闯关东,去锦州投奔一位亲戚。到了锦州,亲戚没找着,全家人只好住在一家小旅馆里,在街头卖艺为生。巧的是北京通州的相声艺人张文斌也流落到这家小旅店里,他一眼看到魏文亮,觉得这孩子精神,根基不错是个说相声的料,就要收魏文亮为徒。
魏文亮的父母知道后特别高兴,于是魏家人和张文斌凑到一起包了一顿饺子吃,算是魏文亮正式拜师了。不久,魏文亮不仅学会了《返七口》、《打灯谜》等适合小孩说的相声,还很快学会了《报菜名》,学会了这些段子之后,他就开始和师父上街表演了。
魏文亮岁数小,个头矮,头大,脖子细,戴顶小圆帽,留条小辫子,在台上站在板凳上说相声,人们看到这孩子长得“逗”,就起了个“小怪物”的名。于是“小怪物”的名声便在锦州传开了。随后还被一个大棚的老板请去说相声,魏文亮和其他的艺人当时是拿同样多的钱。
《贼说话》笑走了劫匪
不久之后,张文斌和魏文亮一家为躲避战乱,决定徒步走回天津。由于迷路,再加上本来有的一条小毛驴在山上受惊跑丢了,所以一行人连着走了一个半月都没能回到天津。这天刚刚上了一个小山坡,前面就是山海关了,一群劫匪跳了出来将他们劫住了,魏文亮的妈妈兜里多少有点钱,本来是准备给一直独身的张文斌娶老伴儿用的,这次劫匪非要把所有的钱都交出来。
就在大家心惊胆战之际,一个劫匪突然喊了一声:“这不是说相声的小怪物吗?这小子说相声可逗了。
”原来这个劫匪看过魏文亮说相声,站在一边的匪首不知道什么是相声,就说,“相什么声?要是真能把我们相乐了,就放你们过去。”那年魏文亮才10岁,什么也不懂,但初生牛犊不怕虎,他过来就给劫匪们说了一段传统单口相声《贼说话》。
这段相声本来是魏文亮从大棚里听来的,词都记得不全,谁知这相声刚一说完,土匪头就乐了,冲着他们说:“我这里还有二万块,你们也拿着,走吧,走吧。”一行人暗乐这成谁劫谁了,最后魏文亮的母亲说什么也没要,一行人才有惊无险地躲过一劫。
没想到,张文斌没等回到天津就生病去世了,魏家人出钱安葬了他。魏文亮当时是身披重孝为张文斌送的葬。
找上门来的师父
1950年正是魏文亮魏文华姐弟俩在秦皇岛“雨来散”走红的时候,一封从天津赤土村老家寄来的信从此又改变了魏文亮的命运——“母亲病危,速回”。
回到天津后,魏文亮一边上学一边继续学说相声。一次,母亲因为生病没办法登台演出,魏文亮临时决定和姐姐魏文华上台为母亲赶场,谁知一出《汾河湾》演完后竟被相声名家武魁海发现了。武魁海是北京的镶黄旗人,早年随李文彬学艺,后来走红津京一带,本来武魁海在行里有个规矩是不收徒弟的,可是看到魏文亮的演出以后就再也抑制不住了,亲自来到魏家,对魏文亮的父母说:“我要收你们的两个孩子为徒,你们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
”就这样,魏文亮成了武魁海的徒弟,并在剧场里举行了非常郑重的拜师仪式。天津市的不少相声演员,张寿臣、尹寿山等都纷纷到场祝贺。从此,武魁海每周日都早早地来到魏家一句一句地教徒弟说相声,魏文亮一句句地学。
如果说张文斌是领魏文亮走进相声行当的启蒙师的话,武魁海则是将魏文亮带入艺术殿堂的引路者。对这两位老师魏文亮都是言听计从,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般,并且这两位老师还都是四十多岁了仍没有成家,基本就都吃住在魏家,所以感情上就又增进了一层。
魏文亮说,“两位老师对我也是真好,我的这些本事,做人也是两位老师一言一行教的。那年年三十了,人家的孩子都跑出去放爆竹。我却仍躲在屋里背贯口,前面还要放一张白纸,唾沫星子还不能溅到纸上。后来这两位师父百年之后都是我发送的”。
说到这,魏文亮谐趣地说,“我这一生打幡儿也是过瘾了,打了四次。两个师父,父母”。武魁海老师去世后,他有个哥哥,对魏文亮说你是他唯一的徒弟,这一切的后事你就操持着去做吧。你花十块钱办我不嫌少,花一百块钱我也不嫌多,那时我给师父买的棺材是沙木十三圆。老人们都知道这棺木是很不错了。后事办得很圆满,我是身穿重孝给老人送的终。
说到这刘婉华补充说,“魏文亮可真是少有的孝顺,那时我们刚刚认识不久,还没结婚,经常是买一斤绿豆糕魏文亮就拿纸包着和我一起捧着给送去了,刚刚下来的草莓用荷叶包着给师父送去了,不过师父也是真教给他东西了”。
两次刻骨铭心的教训
采访间隙,魏文亮无意中看到我采访提纲里的一句话,笑了。“谁要拿观众当傻子,谁就是傻子。”我问,这话是您说的吧!魏文亮点头,“没错,是我说的。观众是永远骗不得的。你达到什么样的精神境界,就会得到什么样的回报,每次演出我穿的服装一定是干干净净的。我常说,我们每次就二三十分钟在台上面对着观众,你有什么理由不用一副干净整洁的形象来面对我们的观众呢”。这严谨的台风据说来源于他早年学艺时的两次教训:
那是1954年的春天,魏文亮和尹寿山搭档在谦德庄的文富茶社说相声。当时已是晚上十点多了,魏文亮在说到一半时打了个哈欠。尹寿山瞪了他一眼,当时魏文亮没有意识到,紧接着又打了一个。这下尹寿山抓起扇子来就狠狠地打了他一下,然后转身下台走了,将这个只有14岁的孩子晾到了台上。
当时将魏文亮窘得简直是无地自容。还是台下的观众宽容,出来喊住了尹寿山重新回到了台前。这件事之后不久,一次武魁海领着魏文亮和魏文华姐弟俩在河东的立通书场演出,无意中魏文亮抠了下鼻子。
下台后武魁海批评他说:“在台上抠鼻子,观众看了多恶心啊,以后要改。”魏文亮答应了声:“改!”可是第二天他又情不自禁地抠了下鼻子,下台后武魁海就又批评了他几句,可魏文亮这回却顶了嘴:“抠鼻子碍了什么事,包袱响了不就行了。
”这句话可把师父武魁海气坏了,他“扑通”一声给魏文亮跪下了,扇了自己两个大耳光:“我教不了你了,你是我师父!”这可麻烦了,师父坚决不要魏文亮了。魏文亮的母亲知道后马上拉着赵佩茹去找武魁海,可是武魁海就是不原谅。最后还是请出张寿臣出面后,魏文亮给武魁海磕了几个头,表示以后一定不会再犯了,武魁海这才回心转意。
但自从这两件事后,台风这个概念就像是刀刻一样印到了魏文亮的心中。正像表演艺术家葛存壮说的:“我每次在你上台前都坐在那等你上台。我看你的手一撩那帷幕的一瞬,就感觉你对观众的感情就像是多年没见到亲人一样,一个两三千人的剧场,你上去用不了两三分钟就可以和观众建立一股亲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