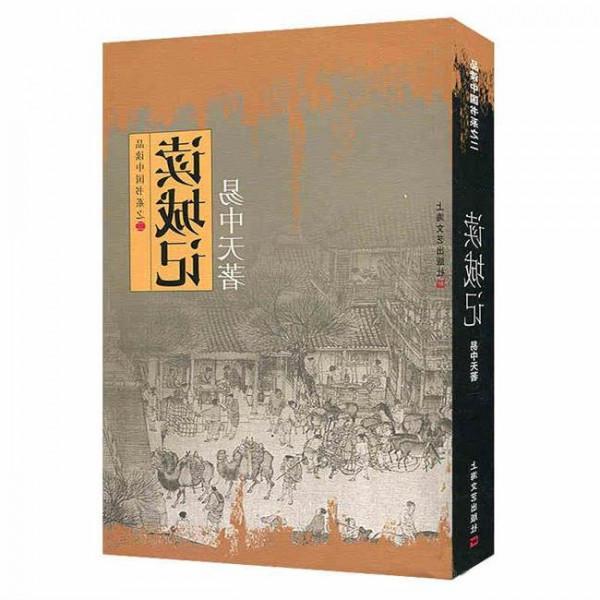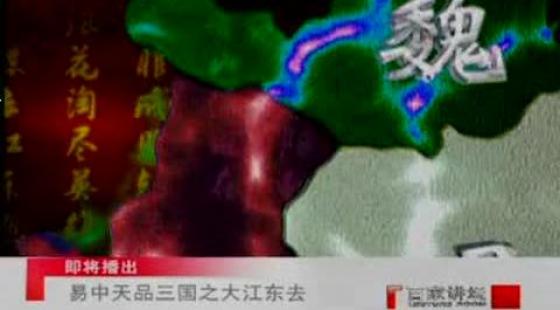张远山易中天 吴励生:至知无知 天道无极——张远山《庄子奥义》解读
读过有关《庄子奥义》的不少评论,较满意者是丁国强先生的《精神氧吧里的自由呼吸》[1]。起码丁先生对庄学本身有相当的兴趣,对解庄者(如王夫之、胡适、冯友兰、任继愈和张恒寿等)有一定的了解,评论起来方能说到点子上。
当然历代解庄者太多,即便现当代更著名的就有章太炎、刘文典、闻一多和陈鼓应等,当然不是说一定非得有比较才能下笔,但有比较显然更能发现张远山的贡献重要或不重要,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能离开张远山的《庄子奥义》文本自说自话。
实话说,有效评论张远山的作品并非易事,除非自我感觉良好的“小知”和“大知”,除了给远山徒添笑料外,评论有效无效似乎倒在其次。这我深有感触,多年前读过张远山的小说处女作《通天塔》,当时那“狗咬刺猬,无从下口”的情形记忆犹新。
张远山的学养、品位极高,其与人合作署名“庄周”的《齐人物论》便是明证。反复品味《庄子奥义》,不敢说我的评论可能有效,但确实如鲠在喉,而今是不吐不快了。让人特别吃惊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家几近绝迹,有文无学早已成了常态,而今张远山却多少有点石破天惊地“凤凰涅槃”。
尤其不可思议的是,那已经飘零了多少年的国学“绝学功夫”竟然如此了得地在张远山手上复活。
也许,就像丁国强先生指出的那样,“其实,学界对郭象本的质疑一直未断。辨伪是《庄子》阅读者无法绕开的工作。”但无须讳言,试图颠覆一千七百年来由儒生郭象一手篡改和遮蔽庄学奥义的旧庄学,并力主重新解释和彰显庄学奥义的新庄学,张远山的理论气魄不可谓不宏大。
即便暂且撇开其诸如贯穿始终的“庄学四境”思想范式的解说,对“支离其言”“晦藏其旨”义理的透彻辨析与还原,对“卮言”、“寓言”“重言”的诸多互文、变文、转辞的反复揭示与立体阐释,对“道极视点”的回返提澌与“人间视点”的逐层观照等等不论,而只跟当下学界热闹着的所谓“回到经典”的诸多主张略加比较,我们也能清楚看到远山的理论抱负甚至直指到了文化的重建,用他自己的话说:“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启全球化时代至今五百余年,异邦人士最先接触的是儒学,异邦大知哂笑不已,殊不知儒学仅是供奉在庙堂上层的古典中国之文化小境。
异邦人士稍后又接触了老学,异邦大知笑容渐收,‘东方神秘主义’之名由此产生,因为老学是沟通庙堂上层与江湖下层因而若隐若现的古典中国之文化大境。
异邦人士接触全球文化视野内独一无二的庄学尚须时日,因为庄学是深隐于江湖底层的古典中国之文化至境。”[2]不客气地说,单从那些所谓“回到经典”的主张来看,起码就有两个重要问题没有解决好:回到怎样的经典?怎么回?而远山对此并没有过明确主张,却又用实际行动特别有力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在我看来,回到经典绝非盲目解释经典,既忽视历史语境又忽视当下问题,就已经不是回到经典而是消费经典的问题了。
需要提请注意的是,远山在解读庄子“内七篇”之前和之后,用了较大篇幅写了两篇“绪论”和三篇“余论”,前者便是为了回到当年的历史语境,后者则为当下问题的反思。前者不仅仅是为了说明庄子“内七篇”的理论根据,更是为了说明庄子身处那样严酷的历史环境(战祸连绵、危机四伏以及专制强权)著书立说为何“支离其言,晦藏其旨”;后者的理论锋芒尤其尖锐,对文化/造化、儒道/儒术、悖道文化/顺道文化、文化/文明、文化相对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相关重要范畴,均做出了颇具远山个人特点且确实有点高屋建瓴的界分和辨析,比如:“任何民族都有可能率先发现并顺应科学真理、人文公理,从而使该民族的文明程度暂时领先于其他民族。
然而没有一个民族能发现全部科学真理和全部人文公理,因为科学真理、人文公理的探索发现永无止境。
每一民族的文明与人类总体文明的关系,就像五大洲每条河流与地球总海洋的关系。不同民族的广义‘文化’河流,其历史流域、辐射范围尽管不同,相互之间也曾隔绝、陌生、误解、对抗、交流等等,但无一例外均或多或少贡献了文明之水,最终汇入人类总体文明的知识海洋。
”在远山那里,所有悖道文化均遭到迎头痛击,所有顺道文化均得到竭力弘扬,似乎泾渭分明还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复杂:可普适性的是文明,而文化总是独特的,尽管悖道文化可能因为民族文明程度暂时获得相对领先的情况下,“就会凭借文明强势,主动推广其悖道的劣质庙堂文化,迫使文明程度暂时相对落后的其他民族接受,甚至被其他民族盲目崇拜,从而受害。
这种受害在其最初,也许不被异民族视为危害,反而误以为是慕效高级文化,但错误不可能长久,迟早会随着该民族的文明停滞和异民族的文明进步而终止。而且随着重新获得文明觉醒,该民族自己也必将抛弃悖道的劣质庙堂文化,哪怕专制强权为之戴上‘传统’、‘主流’、‘经典’‘权威’等虚假光环,也无法挽救其没落”——比如日本,比如中国,尤其比如日本和中国——然而,“每一民族的顺道文化,同样常常与其他民族的顺道文化迥然不同。
与悖道文化是人为造作一样,顺道文化也是人为造作;然而悖道文化违背造化规律、科学真理、人文公理,顺道文化却不违背造化规律、科学真理、人文公理。顺道文化不同于对造化规律、科学真理、人文公理的‘发现’,是对自然造化的丰富性、补充性、提升性、超越性‘创造’。
正是凭借顺道文化,人类才成为万物之灵长,造化之奇迹。”按我的理解,远山的意思似乎是只要能够从善如流,顺道文化必然战胜悖道文化,但常常事与愿违,反而常常是悖道文化围剿顺道文化,甚而至之:“为了增加迷惑性,悖道的‘文化相对主义’常常假扮成民族主义的‘文化相对主义’,悖道的‘文化保守主义’常常假扮成民族主义的‘文化保守主义’,先是有选择地赞扬一些对悖道文化不具威胁的顺道文化,当这些伎俩蛊惑了民众头脑、骗取了民众支持以后,就开始瞒天过海地为悖道文化及其意识形态辩护,以便维护其既得利益和政治特权。
”在远山看来,两种不同顺道文化尽管未必可以交融但能相安无事,只有两种悖道文化之间才会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悖道文化的死敌并非顺道文化,而是其他悖道文化”,因此他必须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进行修改,按远山的逻辑,两种“文明”只会交融,两种“文化”才会冲突。
科学真理与人文公理是唯一裁判,但“文明只是普适手段,科学、民主、法治、公正、平等、财富,都是手段;文化才是独特目的,每个人的独特自由、独特幸福、独特快乐、独特享受、独特审美,才是人类的终极目的。”
通过上面引述,我们可以清晰地领略到远山为何回到经典以及当下问题的制高点的。他不仅无意于“向后看的反专制”(就像索尔仁尼琴或者新儒家们那样),而且干脆以为所谓“三代之制”本身就是专制政治的源头[3],当然远山兴趣在于文化讨论,而并非“文明”,也即所谓“大国崛起”之类:在古儒那里,中央集权常常被解释为“理势”;当下新儒家们,一如金雁、秦晖所指出:“世界上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都有很强大的,唯独贵族林立的‘中世纪状态’尽管好像温情脉脉,但的确很难在今天的世界民族之林立足。
”[4]所谓“三代之制”既失魅力,宗法五服的“尊尊亲亲”的家天下即便如何改造也难以有说服力,因此“制度创新”、“理论创新”的鼓噪与主张者,寻找的仍然是专制大国的思想资源,终究是远山所鄙视的悖道文化罢了。
况且远山甚至明确以为科学、民主等也仅是手段——哪怕而今大国崛起离开了这些手段几乎无从谈起,同时人文公理本身也极需要积极探索——远山跟金雁、秦晖的看法其实如出一辙,即悖道文化(专制帝国)会凭借一时“文明”优势输出文化(所谓强大)。
因此,我以为远山的制高点在于“向前看的反专制”。即便如此,远山仍然对“儒道”而不是“儒术”给予了相当尊重——事实上,孔子以及之后比如朱熹等人创建的儒学道统,以道德理想对抗皇权等资源颇值借鉴——这便是所谓“庄学俗谛”与“庄学真谛”的关系,远山指出:“‘尧既黥汝以仁义,而劓汝以是非矣”:黥为刺面之刑,劓为割鼻之刑。
庄子借直观易解的‘人之身刑’,转喻难以直观的‘人心之刑’,终极指控‘仁义’伪道戕害人之真德,仍以唐尧为始作俑者。江湖章尚以‘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为‘仁义’的变文婉词,此处则不迂不曲地直斥‘仁义’属伪道,伪道俗见之‘是非’属伪‘是非’。
《齐物论》业已贬斥‘仁义之端,是非之徒,樊然淆乱’,指出‘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其所言者特未定’,断言‘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因而主张‘和之以天钧’。《德充符》也主张‘是非不得于身’,《杂篇·天下》又说庄子‘不谴是非’。庄子仅仅不谴伪‘是非’,但必谴真‘是非’。”
在这一点上,远山跟当代学者陈鼓应的看法相近,基本撇清了旧庄学以来对庄子哲学的相对主义误解。然而,与大多数解庄者不同的是,远山特别旗帜鲜明地提出庙堂文化终究是劣质文化而且是悖道文化。用丁国强的话说,“庄子的智慧是同专制制度不合作的智慧,庄子哲学是在不自由中寻求自由的哲学”,丁氏甚至以为庄子是“中国最早的自由主义者”。
尽管后者的说法大可商榷,也尽管如陈鼓应对庄子的自由哲学也一样倍加重视,但这种“自由”或者精神自由,实际上并非自由主义者的自由。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有关儒学乃庙堂文化、庄学乃江湖文化的明确定义,张远山几乎也是第一个说破者——说破并非容易,非尖锐到一定程度是说不破的——比如从纯艺术的角度看历代中国艺术家的自由精神均能在庄子那里找到源头[5],又比如从俗文学角度看武侠小说或游侠精神源头可追溯到司马迁的《史记》以及陶渊明的“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咏荆轲》)[6],再比如中国的唯我式个人主义的源头可追溯到庄子之前的杨朱之学或者中国式的自由其实就是江湖侠客的自由[7],等等,众多理解应该说都是相当精到的,但也许因对庙堂文化未必采取完全拒斥的态度,对江湖文化就难以像远山这样给予如此高度评价(也许只有陈平原曾经别有幽怀)。
而事实上,章太炎先生当年对庙堂文化的拒斥大概可跟远山一比[8],只是由于对严复、梁启超的国家主义叙事的警惕,章氏最后把“社会”甚至“个人”的合法性都颠覆掉了[9],其基本依据也是庄子的“齐物论”,让人倍感遗憾。
所幸远山的政治主张与章太炎所距甚远(此容后详议),而在学术精神上却几乎如出一辙。尽管“社会”也好“个人”也好,需要全新的对顺道文化意义上也即齐物论意义上的天道自然建构,并重新确立科学真理与人文公理探索的全方位价值,从而重新建构现代性民族-国家等等,极为重要,但首先让学术具备有独立品格,遵循学术本身的运作逻辑发展,在当下则更加重要。
也便是在这个意义上,远山极力推崇江湖文化并把庄学境界视为文化至境,显然有着特别重要的价值:在建构出真正健全而健康的社会体制之前,最好的个体选择大体仍为体制外的生存与自由。
两千年前的庄子做过短暂的漆园吏之后,尤其是众所周知的庄子对列国纷争的战祸连绵、危机四伏的社会环境有着极深刻体验和感受,从而彻底洞穿并穿越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的结构性存在,其所热切向往并彻底揭示的精神自由从此也成了历代文豪人杰取之不尽的不竭泉源,一如远山所指出:“先秦老庄真道,作为中华文化的根本命脉,此后不断受到庙堂打压,命悬一线,不绝如缕。
概而言之,西晋嵇阮遗风,秘传至东晋陶渊明。东晋陶渊明遗风,秘传至唐代李太白。唐代李太白遗风,秘传至宋代苏东坡。
宋代苏东坡秘传至明代刘伯温。明代刘伯温遗风,秘传至清代金圣叹。”如果我可以补充一句的话,是否可加上:清代金圣叹遗风,秘传至清末民初的章太炎;清末民初章太炎遗风,秘传至而今的张远山。否则,远山似乎没有完整的理由“庄子与我,相视而笑”。而且,章氏贵为民国元勋声称“功盖孙中山”却拒绝做官,为学乃一代宗师也拒绝出任任何一所民国大学教授,远山的个人行为逻辑以及本土逻辑认知与章氏确实颇多相似之处。
甚至,在远山的具体解庄过程中也能约略看出其与章太炎的某种渊源关系,这种渊源我以为便是上文已经指出的中国大陆本土已经久违了的小学(即文字学)功夫——可能恰是由于此,远山又完全区别于包括陈鼓应在内的诸多当代解庄者。
尽管陈鼓应先生以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我对庄子的评价可能是最高的一个”[10]。但事实上,远山对庄子的评价之高远超陈鼓应。假如不揣冒昧,我以为远山的解庄用心之深也远超陈鼓应。而诸如“用西学裁剪中国文化”或者用西方哲学范畴解释中国思想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