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才亮律师再谈“城市拆迁”及其法律问题
王才亮律师再谈“城市拆迁”及其法律问题
(原载于2009年12月28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导语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逐步推进。但与之配套的法律法规却不健全,或者相关法律法规严重滞后,或者相关的法律法规在立法之初便偏离了合法、公平、公正的原则,导致城市化发展与保护公民合法私有财产权两者关系被扭曲……12月7日,北大法学院5位教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建议书,提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拆迁条例》)与《宪法》《物权法》关于保护公民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原则相抵触,提请立法机关对其审查并修改。
而引发学者再次上书的深层原因,则是各地不断发生的拆迁血案: 从2003年南京市民翁彪第一次自焚以表达对拆迁的不满之后;朱正亮、潘蓉夫妇、唐福珍以及12月14日刚发生的北京席新柱自焚案……都无一例外地控诉着《拆迁条例》的恶行。
《拆迁条例》罪在何处?拆迁,何去何从?拆迁血案,能否终止?……也许,并不是一个“拆”字可以解释得了的。为此,本刊记者再次就有关拆迁的现状和法律问题,采访了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才亮。
聚焦《条例》
《拆迁条例》罪三宗 修改迫在眉睫
关于《拆迁条例》罪在何处?王才亮律师着重提出了三点:
1、政府拆迁滥用自主权,淡化“公共利益”,违宪、违法。
不论是2004年3月的现行《宪法》第四次修正案,还是2007年3月公布施行的《物权法》,都规定了对土地、房屋的征收、拆迁补偿仅适用于“为公共利益”。即只有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地方政府才能依据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
但修改于2001年的《拆迁条例》规定的拆迁事由,则是城市拆迁必须有利于城市规划和城市旧区改建,被拆迁人必须服从城市改造,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搬迁。
《拆迁条例》和《宪法》《物权法》相抵触的地方,就在于没有区别对待“为了公共利益需要”而进行的征收拆迁和“为商业利益”而进行的协议拆迁:征收拆迁由政府自主权决定,无需征得被拆迁人同意;协议拆迁则应由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双方平等协商,由其决定是否拆迁以及如何补偿,是典型的合同行为。
由于《条例》不加区分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的拆迁性质,导致执法过程中拆迁活动“四不像”:首先,地方政府根据城市规划,利用自主权直接决定拆迁。此环节,看似出于公共利益需要的征收拆迁;但《拆迁条例》同时又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就补偿方式、补偿金额等订立协议——而此时的拆迁人则是“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而非国家,这里拆迁双方又居于平等地位,看似又像是协议拆迁。
然而这种看似平等主体之间的协议拆迁,却往往徒具民事协议之名而无平等协商之实,开发商被给予高出被拆迁人许多的各种法律保护。主要表现在政府往往利用公权力迫使被拆迁人接受房地产开发商提出的不平等拆迁条款。
因此,《拆迁条例》中政府的拆迁自主权被人为扩大,结果侵害了公民的合法财产权。
2、 现行拆迁条例中,政府的社会角色错位。
王才亮律师提出:1991年,为了与《城市规划法》配套,国务院公布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该条例的立法思想,原本是通过旧城改造、房屋拆迁,来改善城市居民的住房条件。当时的城市建设主体都是国有单位,并且也由政府主导整个拆迁过程,所以政府在拆迁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明确,拆迁性质也单一,并不区分公共利益和非公共利益性质的拆迁。
“1994年我国开始第一次‘房改’,当年《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出台,房地产开始市场化,房地产开发商成为城乡建设的主力军,同年,中国开始推行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开始逐渐倚重土地财政。
此时的拆迁模式变成了:拆迁决策主体依旧是政府,具体的拆迁人却是商业性房地产开发商。这样,原本简单的政府征收居民房屋并应给予经济补偿的行政行为发生了裂变:政府把自己应当承担的拆迁补偿义务转嫁给了开发商,同时,也把自己独有的带有主权性质的征收权大部分‘让渡’给了以牟取高额利润为目的第三者——房地产开发商。
“由于地方政府倚重‘经营土地’拉动当地的GDP来树立自己的政绩,自然要和房地产开放商形成利益共同体。但反过来,政府也通过各种行政权力积极配合开发商的利益最大化。而开发商为了谋取高额利润自然要极力压缩成本,甚至不惜暴力拆迁,从而引发拆迁血案不断。
“探究血案发生的原因,政府对开发商暴力拆迁的纵容和对拆迁户依法求救的漠视,不能不说政府社会角色的错位是原因之一。
“依据《宪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国家依据公共利益需要,在依法补偿的前提下,对单位和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实施征收。因此,征收、补偿法律关系完全是行政法律关系,必须遵守依法行政的要求。现在,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让政府角色归位,拆迁过程中由现在的政府、拆迁人、被拆迁人三者之间的行政关系夹杂民事关系,变成由政府作为国家征收人和被征收人之间的单一行政法律关系。”
3、拆迁补偿程序倒置,被拆迁人处于被动的不平等的法律地位上。
在出于公共利益需要进行的征收拆迁中,按照《宪法》和《物权法》的规定,补偿是征收合法有效的构成要件,应当在房屋拆迁之前完成。而在《拆迁条例》第三章“拆迁补偿与安置”的具体规定中,补偿与征收切割开来,补偿从征收程序的一部分变成了拆迁程序的一部分,这实质上将本应在征收阶段解决的补偿问题拖后到了拆迁阶段。
依照现行《拆迁条例》规定,征收房屋和土地决策由政府做出,而实施拆迁和进行拆迁补偿由商业性企业执行。这种权利义务相分离导致的严重后果,是拆迁决策过程完全由政府和拆迁商人单方面做出,而现有的房屋产权人和土地使用人被排除在外。
而且,由于拆迁决策主体与执行、补偿主体分离,补偿标准的谈判和讨论也被推迟到拆迁决策做出之后、拆迁开始实施阶段进行。而到了这一阶段,被拆迁人的合法利益往往处于被置于一旁,执法机关的监管流于形式,被拆迁人往往只能以血肉之躯来和开发商讨价还价了。
律师建议:
完善法律体系,改革相关法律
对于修改《拆迁条例》后能否彻底总结拆迁悲剧的不断发生,王才亮仍旧有自己的看法。他提出:“即使将来拆迁条例被废除,地方政府也只是失去了一个以公权力介入民事活动的依据。
虽然可能减少悲剧的发生,但要真正维护公民的房产权,终结拆迁悲剧的发生,仅仅修改或废止《拆迁条例》是不够的, 而是应该对整个涉及拆迁的法律制度进行修改。因为,《拆迁条例》的许多谬误是当前拆迁矛盾的源泉之一,但绝非全部——其他法律法规中也有违宪和直接侵犯被拆迁人的规定。比如:
“《城乡规划法》第31条,将‘旧城区的改建’‘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也列入拆迁的法定事由。该法实质上是规避了宪法和其它法律对‘拆迁范围’的限制,旧房不是危房,它的存在并没有妨碍不特定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如果要拆除旧房,必须在征得房屋所有权人同意拆迁和接受补偿标准后才能进行。
而危房的修建的权利和义务的第一主体应当是产权人。但事实上,《城乡规划法》第31条被滥用,许多城市的旧城(村)改造成了商业开发,其规模之大,甚至包括开始拆迁本世纪才竣工的小区。
“《土地管理法》第58条也违背《宪法》和《物权法》关于只有公共利益需要才能收回单位、个人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规定,在规定“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的”的情形之外,又规定 ‘为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需要调整使用土地的……由有关人民政府土地主管部门报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事实上,许多地方就是依据这一条款,未经法定程序擅自收回土地使用权进而实施大规模的违法拆迁。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22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土地使用者未申请续期或者虽申请续期但依照前款规定未获批准的,土地使用权由国家无偿收回’。这一规定与《物权法》“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到期后自动续期”的规定明显冲突。但是,一些地方仍然借此与《宪法》《物权法》立法精神相矛盾的条款,将土地使用权无偿收回、同时实施拆迁。
“至于农村的拆迁更是混乱,越权制订的红头文件比比皆是,且执行力度远远超过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尤其是江苏、浙江的一些城市政府有关“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管理”的规范性文件对抗《立法法》第八条和《物权法》42条的规定,群众对此是求助无门,导致上访如潮和血案频发”。
“除了上述现行法律、法规、甚至地方文件之间存在违法、违宪情形需要统一立法原则之外,在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的良知也是考量拆迁问题能否合法、公平、公正履行的关键。比如,唐福珍自焚事件,就是执法机关人为恶意选择性执法的结果。”王才亮说。
“唐福珍渉案房屋,早在《城乡规划法》出台前10多年就已建造,依照当时规定是合法建筑。在执法机关对其做出违法建筑的认定和处罚决定时,《城乡规划法》也尚未生效。但为了获取拆迁中的‘利益’,相关执法机关便选择性地适用《城市规划法》,以此界定唐福珍的农村房屋是违法建筑、不予补偿。
“然而依据《城市规划法》,拆迁执行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同样,为了避开司法审查,执法机关在执行唐福珍渉案房屋时又选择性地适用了《城乡规划法》—— 因为《城乡规划法》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强制执行的授权即可。
“合法与违法的标准,不再是依据事实和法律规定,而是任由执法机关自由选择的时候,公平和正义就演变为人的良知的发现或泯灭。法治社会更是无法谈起。”
王才亮律师认为,当前已经不仅仅是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按照学者们的意见修改,而是以对整个拆迁制度进行修改作为突破口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他呼吁:当前尽快要做三件事:
“一、废除现有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而制订符合《宪法》《物权法》规定的房屋征收与拆迁补偿法律制度,同时对《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乡规划法》进行修改,彻底消除地方政府通过拆房卖地牟利的渠道。
同时,今后的立法要提高操作性。例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对违法拆迁的处罚就没有操作性;又如《行政许可法》36、46、47条虽然规定了听证的要求,但并没有规定未经听证的行政许可即为无效,所以规定听证与否没有意义。
“二、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政治。如果能真正做到让人民在政策和法律的制订、官员选拔的任用上有话语权、监督权,干部们的权力将受到制约,就能减少贪官酷吏产生的土壤,减少拆迁扰民现象的发生。
“三、落实科学发展观,联系实际,坚决废止土地财政和‘政府经营城市’的理念。这就需要在‘精兵简政’的同时改革财税制度,使基层政府减少财政压力带来的拆迁冲动,使多数公务员能洁身自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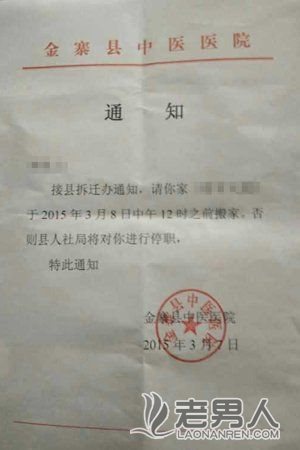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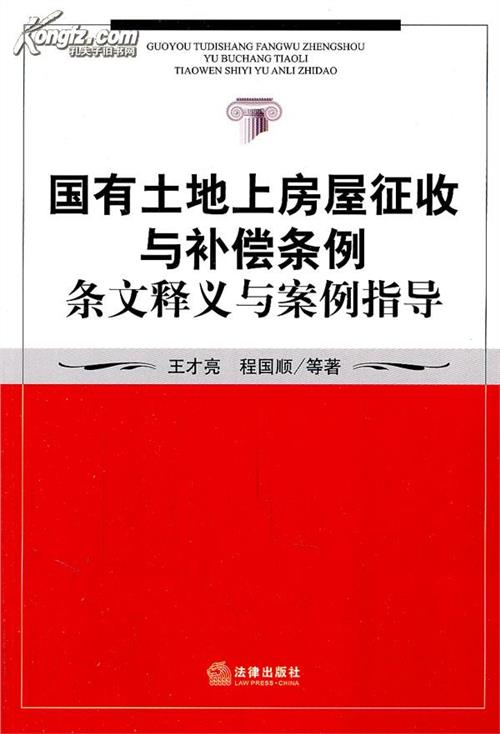





![>汤灿被执行死刑后照片]歌手汤灿被执行死刑](https://pic.bilezu.com/upload/e/64/e64e25269c7d24ed43b8bff9f7a0be7d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