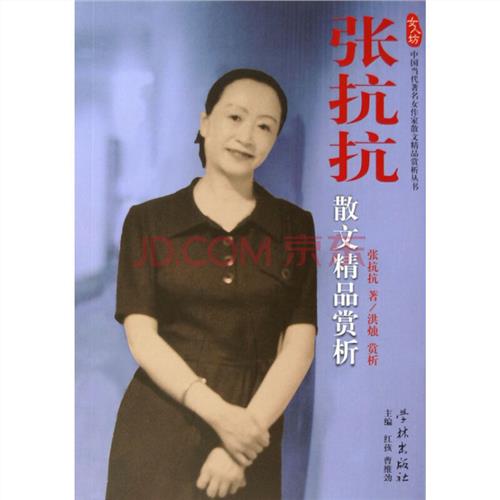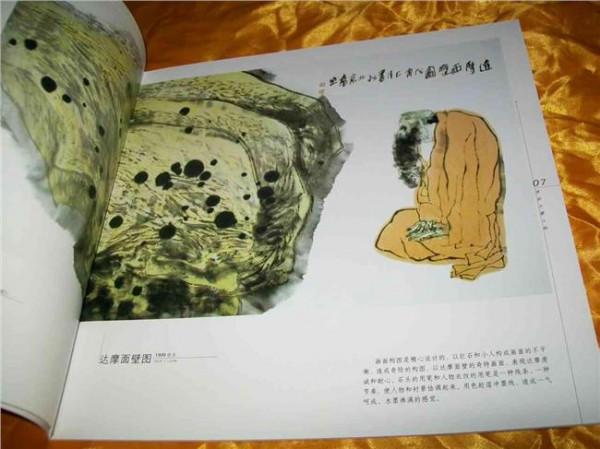忻东旺透明 中国当代著名油画家忻东旺绘画艺术探索透视
这些年来,忻东旺以笔为旗,始终保持表现人类精神品质的传统,以他迷恋的乡土情结,作为一种文化复合体,补偿或平衡着中国农民阶层的文化象征。他的审美理想与情趣,在感性与理性的交织中,既有外在体态容貌的时代特征,又有内在民族德性的文化内涵,在中国新一代画家中更加凸显,给人一种独占鳌头的气势。
尤其进入后经济时代之后,他对应运而生的民工潮的深切关注,从那幅《适度兴奋》埋下的伏笔,到进入二十一世后的“康保人”群像,几乎囊括了他对中外艺术运动和文化思潮的理解力,不仅跨越了现实历史的迷障,而且超出了技巧、形式、方法与表现。
他如此痴心于对农民命运的关注,以及在这关注中注入反讽意识、文化符号和哲学意义,很少有人能达到他的人性深度和精神高度。
超越现实主义给定的艺术视域
统观忻东旺的绘画作品,可以看出他展示的弱势群体的心象性和边缘性,既富于历史性的时代特征,又弥漫着风俗化人性的荒诞感,给人一种最富于生命力的震惊。然而,对他的作品进行深层次文化性的剖析,则涉及到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开放社会的消费主义风行,意识形态的异化现象,使中国农民日益边缘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忻东旺以农民命运和时代思潮的不确定性,作为艺术创作的关注目标,折解农民形象的表层结构,放弃世俗化的逻辑整合,不断地超越现实主义给定的艺术视域,像一个沛恩百姓的乡村心理医生,似乎很无奈地把病入膏肓的民心,当作实验性意向的礼物,交给期待已久的观众,让观众以足够的耐心,去抚摸中国农民的粗糙躯体,品尝人性的温亮与裂变的滋味。
伴随着现代过程而形成的世俗化趋向,中国美术已经走向了实验化、行为化、波普化和拍卖化,画家们往往用各种新技法,展示个人的独到思想,赋予当下的生存境遇,以优先的文化身份疏远理想,拒绝崇高,摈弃精神层面的终极关怀。
对许多画家来讲,面对中外艺术史,想获得突破性的艺术成就,无疑是在果实和果实之间做荒凉的美梦。相对于蔑视理性的玩世心态,标新立异中的无可奈何,忻东旺所体现的价值取向和意义追求,已经表征了更复杂的精神维度。
尽管他的创作原则与意义世界本身,也存在理论和历史的局限,但在理性与意义面临挑战的今天,对于维护中国农民的尊严,无疑具有警醒作用。他笔下闲置的农民群像,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尤其作为意识性的人类心智产品,在客观上离不开人本身,也离不开社会的内在现实和外在现实条件。
基于此,他早年的挫败、个人经验的积累、艺术嬗变和内在发展,曾受制于艺术圈子的各种心智游戏,也受制于社会意识形态、政治文化、经济条件、文艺运动等文化潜在性的影响,更受制于他本人的人格结构。因此,他所展示的农民心性和意义关怀,可以引发人们致力于意义世界的守护,正是在这方面,他的绘画艺术蕴含了历史性内在的生命力。
毫无疑问,就在中国画家们为经典焦虑困扰时,忻东旺渐渐意识到,中国艺术的母体文化血液,在一片散沙中从容地流逝,而忧伤不再给他带来麻烦,扯不断的乡愁使悠闲的生活匆忙起来,不死的民间使他备感亲切。他知道商业风把以食为天的农民,从祖传的田园梦中吹醒,诱惑他们以一错再错的情态,纷纷涌进城市,惨遭生存焦虑的折磨。
经过多年的创作实践,忻东旺找到了自己的艺术领域,步入恰如其分的文化背景,探索出贯穿中外艺术的乡土中国文化母题。
事实上,忻东旺对中国农民的集体命运,赋予同情和深切关切的同时,充分展示了中国农民的异化现象,但这种情怀区别于一个乡村野老的参与热情,而是带有隐喻性的反讽意味,以更悠远绵长的文化意义,具备了走向未来大师的轰动性,也更符合中国儒家文化培养基的内涵。
严格地说,在人类精神史上,任何艺术家的创作过程,都是一个极具奥秘性的问题。对忻东旺也不例外,所有的农民形象可能都是他价值重建的幻影,在鱼龙混杂的美术界,从文化母体怀里,突然露出画布上的精神侏儒,一张张孤独无援的嘴角,像弱智孩子要求精确的身份。
忻东旺知道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因此他既与艺术创作的始源性、时间性、文化性、政治性、历史性和未来性难舍难分,又与他的人格理想和心灵结构会通。对如此富于奥秘性的创作过程,任何单学科的解读,恐怕都是不堪重负的,而美术评论家不是怀孕的透视镜,他们极为有限的判断能力,以及美术理论的单元解释范式,自然也是不容乐观的,不可能解读商业性刀尖上谢幕的母体文化之乳。
实际上,无论是国家的旗帜下,还是农民的灵魂里,忻东旺都用一种温和的声音,告诉人们他的深思所得:任何一个画家的创作,在本性上就是一个跨学科的问题,既需要作出历史的探寻,科学的求解,又需要作出哲学的思索。
在这个层面上,解读忻东旺的绘画艺术,评论家们要回避“必闻其政”的颂歌模式,不要取其一匡九合之功,应该在相互观望与彼此吹捧中,为自己的社会良知哀嚎和拯救,更要具备科学性和现代性的目光,公正地把忻东旺放在比米勒、阿特逊和勃鲁盖尔更远的位置上,就不会偏颇地认为这是一种无根的文化移植。
可以这样说,中国油画自身的文化渊源,并不是在一片灰烬中投抬,注销了本土性的灵魂,而是艺术家的心理基因,尤其是母体文化的血缘力量,支持着中国油画越过了一个世纪的沧桑。
尽管百年政治风云变幻,经济起伏跌宕,文艺流派纷呈,各种学术思潮亦可谓乱花迷眼,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乡土性母题,依然源远流长,沉潜于艺术发展史,始终没有断裂,这种渗透到民众意识内部的文化品格,已成为不容忽视的一个研究课题。
忻东旺使用“静态”和“呆板”的概念,替代了抽象意味的国民心态,所以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他笔下被迫的孤寂,加倍的坚忍不拔,仅有的幸福,有别于车尼尔雪夫斯基式对现实主义的盖棺定论,而是采用现代性的隐喻方式,来展示他的观念和思想,由经忧伤的生存欲望,骚动的心,悲痛的芬芳,勾勒出当代农民的传统品格和时代性情。
这些隐喻不是貌合神离的比附,也没有停留在揭示风俗习惯与人物表象的相似性,而是指示本质上重要特征的模糊性。
他的画笔直入人心,不求解意义的明确性、确定性和精确性,但他赋予极其丰富的含义,启发人们去思索和想象,让审美语言感到遗憾。他正视现实人事,一直把复杂的社会问题,隐匿在祖传的精神圈里,潜心编织文化印记的分判线索,让人想着梵高的耳朵,从窄门窥视人性的尾巴。
更确切地说,不了解现代性隐喻,就难以阐释忻东旺艺术创作的内在流程,也不懂得他的思想意义所在。在更深意义上,他的冥思性和自发性,无疑透视出中国农民未经修饰的文化心理,本真地反映出人格结构的镜中瑕疵,以及隐匿于文化心理背后的国民性,这一切外力背后的传统文化内质的坚硬程度,对艺术强韧的渗透力量,在忻东旺的绘画作品里得到了更加深刻的展现。
站在当代立场,如何体现中国社会和文化传统的乡土性,对人文历史所包含的现代性进行时代的阐释,无疑是一件切身紧要的事情。正是乡土性,展示了忻东旺的理想之境,内含了评价准则,凸现了祖国特征,并作为稳定的思维定势和创作趋向,预示着深度考问的演进过程。
他没有追随现代艺术狂飙,也没有把画室搬到市场,而是从暗褐色的乡间小路,到温馨的农舍,从一张张敦厚的农民脸上,发现了观念形态的文化系统,总是以价值观为其内容的。从价值体系看,忻东旺的绘画艺术固然包含多重向度,他从惯常的农民日常生存活动中,发现的不是人性的绿叶、鲜花和晨光,而是从农民群体内在的心理异变,到外在的社会关系和生存活动,捕捉了隐秘的心性,这犹如少女幽会前的暗喜,奠定了他的艺术观,使国民性和文化性得到了更深刻的阐发。
对中国画家来说,一直未能摆脱乡土性的纠缠,而在每一个新旧世纪交汇处,这种似乎与生俱来的尴尬和矛盾,都能得到最强烈的体现。从徐悲鸿、林风眠、刘海栗、蒋兆林、李可染、吴冠中的无可挽回的失意,到靳尚谊、詹建俊、高虹、何孔德、罗尔纯的抵不住冲击的感伤,以及到陈丹青的苍茫与凄怆,在修辞艺术的商业社会迎面驰来的速度里,在个人作为传统的血缘社会易位的物质空间里,历史反复让画家们体味出割脐带般现代的疼痛。
现实中渐次退隐的价值观念,使忻东旺在艺术创作实践中,祈祷着中国农民的饥饿、自由和禁锢,祈祷着父老乡亲的百年孤独,祈祷着长城的暴戾和黄河的呻吟,祈祷着一张脸上的中华民族,祈祷着民工幸福而苦难的心史,因此他获得了别人难以拥有的辉煌,搅扰着乡土中国的民本思想,他将常胜不衰的一系列传统的文化命题,在争执与递承中串联起来,承担起集中反映社会转型期,也是世纪转折点国民心态的使命。
孕育人间的社会公德与个体美德
以乡土情结作为切入点,忻东旺得到了一种进入绘画语言的最佳定式,当他喝着法国咖啡,手执画笔,站在清华大学的画室里,避开赏心悦目的事情,关注农民工的日常生活,留心观察他们的出没之地,想到他与他们彼此生生息息时,他再次发现自己还是灵气十足的乡村孩子,在成败难测的艺术圈子里,画一幅农民肖像的目的,也突然发生了奇变。
他把崇高化和理想化的艺术理想,仿佛浓缩成看图识字的儿童乐园,所有的人都变成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而这个世界何患无词,没有一个不会说话的嘴巴。这促使水天中、贾方舟和殷双喜等艺术评论家,客观地肯定了忻东旺的创作成就,他们都将忻东旺的人性关怀,列为中心的论题,达成了一致的审美结论。
按水天中、贾方舟和殷双喜的观点,就内在的艺术德性而言,他们给忻东旺对弱势群体关怀与同情,在理性、情感和意志等诸方面之间的合理定位,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水天中在《现实主义风格的探求与扩展》一文中说:“忻东旺对他们都怀有充分的理解和同情。
当我们即将被泛滥于媒体中的打情骂俏或者故作深沉的时髦男女淹没的时候,反倒会为忻东旺画中人物的沉重和茫然感到一种欣慰。忻东旺的笔触带有不加掩饰的笨拙和滞重……”贾方舟在(《感受生命》——忻东旺的绘画艺术)中,对忻东旺审美界定为“对人物的‘缩身’和‘矮化’处理,更强化了人物的边缘、弱势、甚至卑微和自私的一面。
”殷双喜在(《人性的光辉》——忻东旺近作解读)中认为,忻东旺的作品“将其观察的目光,聚焦于城市的底层与边缘人物,其中以农民工为主体,还有那些生活在城市底层的弱势人群。
由于经济地位的低下与教育水平的局限,这些人群对于个人权利与价值理想的表达,处于一种无声的状态,面对各种侵害他们的强权与暴力,他们是一群‘沉默的羔羊’。”
人们不难发现,这都是根据富有人情味的态度,来解读忻东旺绘画艺术的。对忻东旺绘画艺术的整体观念,做进一步求解和论证时,最值得注意的是反讽与戏拟,既要确认忻东旺自身的心灵结构,又要通过作品的本质属性的相互确认。
忻东旺的绘画艺术总是指向群己关系,以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为前提,想达到个人的价值关怀与人格理想。从他作品的表象看,几乎每一幅作品都蕴含着对低层群体的关怀,体现出他对民众社会的责任意识。从他的创作构想分析,他展示出社会上处处都能得到一种情趣,不是冷漠、对敌和算账的样子,尽管农民没有自己的权利,甚至惨遭利益集团的压迫和奴役。
忻东旺基于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以孩子的视角给中国美术界以挑战式的启示:维系人与人关系最重要的因素,是彼此维护人格和尊严,当前最迫切的道德问题,是孕育人间的社会公德与个体美德。
忻东旺从煤矿做临时工,到晋中一个印刷厂做设计员,以及他曾“惊叹于欧洲艺术造型的精妙,更醉心于汉俑、宋塑的浑然意趣”,足以表征世间一切事象与学问,只是一部与人类生命有关的历史。他所塑造的弱势群体形象,诚然有其历史的复杂性。
从童年到少年的成长经历,使他克服了时障和地障。对于当代农民的异化现象,忻东旺在方法论上,跨越了许多人无法去考察的境况,他体悟身边所发生的一切,面对物理世界的纷繁,哲学的玄想,史实的榛莽,他所能凭借的只有绘画艺术。
对史实典籍的尴尬回顾,对中华民族命运的隙望中,他以低层人的生存状态为轴心,以国人自强不息的动力,以农民的品质和特征为对象,把社会历史转换成风俗化与人情化的心象。因此,他笔下的农民是疤痕体质,像这个国家的旧梦,他们瞪着病态的目光,直愣愣地望着脑空想出的蓝图;男人既有播种的豪情,又像一群精神阳痿的人,女人的身体丰满,没有一丝倩盼美质,也没有欢声笑语,却以孤独滋润的柔情,渴望城市的抚摸,不顾城市的欺骗性,仿佛城市里隐藏着远古的幽情。
面对贪婪的世界,他们也善于退居一隅,安贫乐道,不思考索取与给予之间,有过什么样的落差。
如果从文化倒错的现象,去考问忻东旺的理想主义色彩,就发现他的艺术视角,从乡村向城镇和都市的扩展趋势,表证出乡土文化的对应性、层次性、延异性和普遍性。事实证明,民工作为背井离乡的人类集团,以食为天的处世态度,相互依赖的生存方式为特征,进一步显现出压抑的文明,虚伪的礼俗,不只是单纯的社会问题,而是审视人性因素的一面镜子。
忻东旺找到了自己的创作良途,构筑了当代中国美术界最不可忽视的景观。不仅如此,他信仰的中国乡土母题,以不容忽视的文化姿态,以更为丰富的哲学内涵,表露出他对民族人格重建的艺术良知。
这就意味着,忻东旺从乡土文化入手,一下子切入到民族文化结构的深层,揭示了农民集团的历史心象,由此浓缩出一系列人性裂变的时代精神,将国家与民族、政治与宿命、国史与心史、命运与心性的相契与悖反结合起来,并在时代演进流程的丰繁里,展示了农民阶层的人生百态,同时也表征了他本人的人格理想。
也就是说,相对于传统中国文化心理结构而言,忻东旺更注重基层历史,因此他把农民作为参照系,对观察到的一切做出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的综合透视,尽管现实中存在倾轧性、欺骗性和黑暗性,尽管民工集团被各种强权控制,具有被新贵们统治的意味,农民依然被忻东旺描绘成孩子一样天真无瑕,满足于乐感文化的追求,他们超越纷乱世事的心象,为维护社会公众意识和行为规范,提供了具有理性色彩的精神依据。
忻东旺不掩饰钟情现实主义艺术的雄心,既展示出农民的道德善良,人性的温亮,又暗示了他们的压抑感,失衡的时代姿态,无奈的文化心态,以信仰在乡俗民情之上的力度与质感,阐扬着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情怀,由此构筑出一段中国农民伤心史。
理解了这层,便不难想象中国农民史,以永远长不大的孩子的意识与观念,完成着自身的循环与推演,而忻东旺将中国农民的沧桑与心性,以隐藏在乐感文化背后的母体热血,标识出历史无可绘画艺术的本质属性和文化寓言
忻东旺对弱势群体的亲近与好感,源于他对写实主义的信心,这不是“绘事后素”所追加的装饰,而是展现出艺术精神的本质属性,引导他对国民心理与民族文化内涵倾注了极大兴趣,揭示出物质文明背后的灵魂骚动。在“以人为本”的文化土壤上,中国农民未能摆脱血缘的锁链,以及文化记忆的乡土性,后现代经济文化强大的束缚力,使民工变成了理性的工具,被利益集团控制,被城市文明操纵,成为物质时代的牺牲品。
忻东旺展示了这一底蕴文化的多元性,他的《适度兴奋》喻示的正是这一实质,如果不考虑性活动的暗示,而《明天,多云转晴》则表露出人性关怀的历史性矛盾,他渴望在乡土中国文化这一长长的幕布上,出现温暖人心的阳光,也暗示了阴霾的存在,以及都市文化和乡土文化的冲撞,乡土文明与商业经营的对立,他的绘画艺术的本质属性,已把现实文化的转型趋势,推到了一个更为深远的历史背景。
概而言之,忻东旺的绘画作品,像另类乡村广播员的历史旁白,给当代农民命运罩上了一层文化的神秘,也使乡土文化体系有了寓言式的结合。他笔下的人物健壮如牛,红色的脸颊,像一枚方形私人印章,腿脚似乎长错地方的木桩,当人们面对他笔下变形的“康保人”群像,越过口口相传的美言,去确证它的起源和联系时,禁不住产生一种痛快的感觉。
这说明所谓的历史,是一种能把意义变得隐晦的奇怪力量,因为历史本身就是文化寓言。对商业时代的文化侵入、精神的征服和血缘的蔑视,农民们一如既往原始地承受着,当独立性、自主性和个体性被利益集团阉割之后,他们带着不自觉的生存本能,成为集体无意识的文化游民。
由此判断忻东旺的作品,确实含有集体无意识的外衍,为了寻求文化位置和艺术功能,他从农村走进城市,造成确认文化身份的两难,他必然承受改换心态的苦痛,但农民永远是他血脉的祖先,也是他精神的文化祖先。
对于这种生命哲学的特征,忻东旺把当代农民视作文化符号,把好恶藏在画布背后,在不露声色的创作中,透露出割不掉的精神胎记。因此,初看忻东旺的作品,让人感到心中刮起一阵疾风,吹去深切的感叹,接着有一缕光线移开,令人感到生命昏暗了些。
他的“康保人”肖像系列,如此粗糙笨拙,犹如枯萎的青草,没有生动的表情,看不出有什么不同,但他们憨厚健壮,把痛苦纳入内心,所有的压抑感被意绪上的温情所代替。这给人造成古歌曲终的不安,这种焦虑所携带的严峻和孤单,喻示了当代中国农民人格深层的悲剧性分裂,文化的历史轨迹如此错杂,以致只能以人性关怀来弥补文化的缺欠,解决困惑与忧惧并存的矛盾。
由此意义回视,不难理解忻东旺《适度兴奋》的苦心诣旨,让人联想到有什么东西比农民更加壮美。
面对社会控制势力,利益集团的暗算,权利欲望的膨胀,真理的模棱,正义的缺席,乃至整个世界在他孩童视域中浮现,由经文化喻示所具备的悲悯之情,以及平视的客观性,阐述的冷漠性,把性冲动的暗示与利益属性和道德属性巧妙置换,描绘出开放时代的一系列社会心态和心灵内部的窘态。
忻东旺的“康保人”列传,以孩子的视角对当代农民的生存情状,赋予了高贵的品质和影象,他用不留余地的坦率,所构筑的生存图景的真实性,依然是寻求一种更大力量的价值渴望。这说明了乡土中国传统文化的粘附性,已成为忻东旺的心理风土和创作取向。
一切人类的现象都从自然的到文化的,从本能的到智慧的,从个人的到社会的。忻东旺是否能够延续这一创作态势与状态,顺乎自然地精神突破,已经远远超出了艺术评论家的期待,对于已经暗示的一种转折现象,任何预言都是无力的,任何告诫指导,也将是荒谬和多余的。
进一步说,他跨越或摒弃了传统反思的文化层,直接步入更遥远的价值关怀,从对原始生命力的低层人群与事物描绘中,达到求解现代文化的孱弱性和畸形性,透射出一种曲折的人文关怀,以画笔高歌蓬勃的生命力,粗犷之上涉及到一种对民族凝聚力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