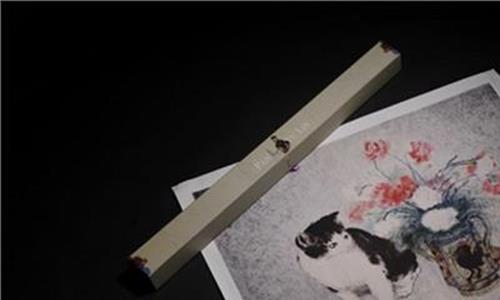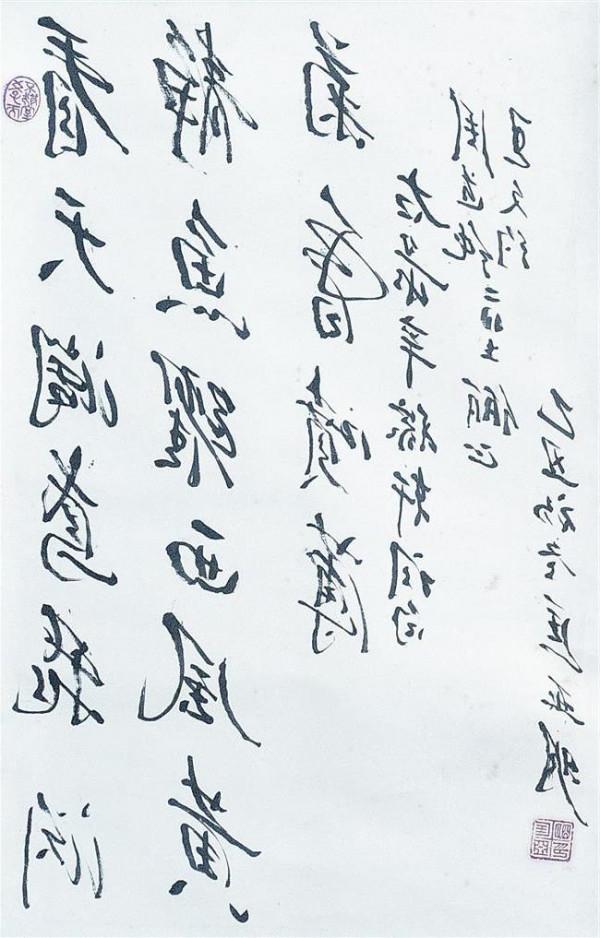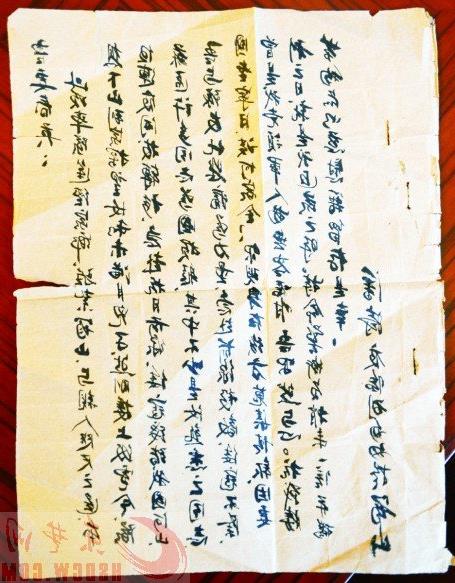潘际銮的妻子 潘际銮:老院士黑白分明的焊接人生
北京清华大学宿舍荷清苑住宅楼内,有一个普通得甚至有点简陋的家:积灰的家具把整间屋子挤得满满当当,沙发罩随意地用两只别针固定在靠背上,几个行李箱堆在客厅正中,主人喝水的杯子,就是一只原本装速溶咖啡粉的玻璃杯。
外人只有看到被随手撂在茶几上的《院士春秋》等“大部头”、院士集体照,才能大概猜到,这家主人,有点来头。
主人是位87岁的老人,他叫潘际銮,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实用型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的焊接顾问;融入亿万国人生活的高铁也和这位老人有密切关系——他曾在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穿着厚棉袄,站在南京段的铁轨边上,在深夜里测定钢轨的焊接工艺,那一年,他已经年过八旬。
1951年,当潘际銮投入新中国从零开始的焊接事业时,当时的女友、后来的太太李世豫写来一封不乏怨艾的信:“周边的人笑话我说:‘你男朋友学焊接?学焊洋铁壶、修自行车干吗?’”
53年过去,潘际銮筹建了清华大学焊接专业,为中国焊接事业攻坚克难,在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的焊接馆里,“潘际銮”三个字高挂在门厅的墙壁上,居于一堆名字里最顶头的位置。
但这位老人对自己过去的成绩毫无谈兴,谈及手头的两个尚未攻克的“世界难题”,他才来了精神:一是中国核电站的制造工程,焊接是核电站实现绝对密封、绝对可靠的关键;二是“高超超临界”煤电工程,如果能成功地把火电高炉的燃烧温度从600℃提高到700℃,一座总装机容量600万千瓦级的火电站一年能节省5000万吨煤。“想解决这些问题。”
让潘际銮兴奋的另外一个话题,是教育。他是西南联合大学的1944级生,目前担任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会长。和其他高校以“位尊年长”为推选标准有异,在西南联大,这位院士其实不算“出类拔萃”——这所中国教育史上的传奇大学,在抗战硝烟与动荡中办学仅8年,在这里任教的既有陈寅恪、朱自清、冯友兰等文科大师,也有吴大猷、叶企孙、华罗庚、吴有训、曾昭抡等理工科大师;培养出两院院士166人;诺贝尔奖获得者2人;“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8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4人……
“校友选我是因为我年轻、能干活!”潘际銮哈哈大笑。这位世界级焊接权威,把QQ、微博、微信用得无比熟练,他不仅是西南联大的铁杆粉丝,更尝试着把西南联大的学术精神和自己的教育实践“焊接”在一起。“宽严并济、自由创新的精神,是西南联大的魂,也同样适用于今天的中国大学。”而说起当下纷纷扰扰的学术“热闹”,他只说:“我是个‘过时’的科学家,对那些不感兴趣。”
院士的平淡生活
“我的看法对不对,你听一下?”这是潘际銮的开场白。
到潘际銮家拜访,刚到7楼,电梯门打开,记者惊讶地发现,潘老已站在家门外迎客。这位近一米八的老人,略略弯下腰板,笑眯眯地伸出手相握,温暖、谦逊,“欢迎欢迎!”采访完毕,他又偕夫人将记者送出门外,电梯门关闭的那一刹那,还能看到夫妻两人笑眯眯地挥手告别。
璀璨的院士光环,潘际銮已经“戴”了34年,但他眼里,这光环仅等同于“老中医”。“他们愿意来找我解决问题,和病人找医生看病是一个道理。信任我、挂我的‘号’,我就尽力帮他们解决问题。这么多年都是这样,比如说核电站新出一套设备,有关部门会打电话来问我,‘潘院士,您觉得安全程度行不行?’我看了,说‘行’,他们就比较放心,人家看中的是我经验丰富,仅此而已。”
潘际銮的生活也和繁华绝缘。每天上午8时30分,在家吃完老伴儿准备的早餐,他就蹬着电动自行车,一阵风般飞驰十多分钟,到清华大学焊接馆上班,带着20多人的团队干活;傍晚6时,他又蹬着自行车回家,老伴已经准备好了晚饭;晚上上网、回回邮件,一天便过去了。
电动车是他80大寿时一位学生孝敬的“舶来品”,他很喜欢,还常常载着比他小4岁的太太飞驰去菜场,“直到后来出了点小事故,别人说你别这样,两个80多岁的老人,出了事不好办。”他才停止“载客”生涯,现在老伴儿买菜便坐公交车。
不过最近他有点犯愁,车子用了7年,电池老化快报废了,却配不到新电池。“一个学生说可以帮我改装一块电池,我有点担心,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如果车子坏了,潘际銮就得步行1个半小时上下班,“毕竟年纪大了,有点走不动。”
“您是院士,难道不配专车?”记者不禁诧异,要知道,明文规定,院士参考副部级待遇!
“清华有五六十位院士,大家都是这样、没车。”潘际銮说。
潘际銮也有过专车。当年在南昌大学担任校长10年期间,一辆留学生捐赠给学校的老旧尼桑“蓝鸟”跟着他。下属们劝他换辆好点的车,“您是我们的校长,出去是学校的代言人。”他不听,觉得没必要。10年届满离开南昌,那辆“蓝鸟”也正式报废,他又过回了自行车上下班的日子,“没啥不习惯。”
院士的收入有多高?潘际銮说:“万把元一个月,比我老伴儿高——她是北大的退休教授,退休金5000元/月。”当听说社会上不少“金领”年薪百万时,潘际銮惊讶得瞪大了眼睛:“这么多啊!”并不羡慕。确实,在他家里,最贵的也就是两台台式电脑,他一台、老伴儿一台,其他要花钱的地方,不多。
痴迷联大的
“宽严并济,自由创新”
随着年纪渐长,潘际銮喜欢回忆往事。对于自己的丰功伟绩、对于已经当了34年的中科院院士,他没啥谈兴,他最喜欢和徒子徒孙们“叨”的,是他的西南联大。
谈起西南联大,他的话匣子关不住,“我是当年的会考状元,一进联大就当头一棒,最喜欢的课程期中考试却不及格,五雷轰顶。”
这门“普通物理”由著名物理学家霍秉权教授讲课。霍教授是我国首批研究宇宙射线和核物理的学者之一,上课风度儒雅,同学们有什么问题,他都很耐心地解答。霍教授上课的教材是《达夫物理》,但讲授的理论知识很前沿,常常一边讲课,一边和学生讨论自然现象及它背后蕴涵的科学原理、哲理。
潘际銮中学时是物理尖子,大学会考又是云南省状元,对这门物理当然很有信心,没想到首次期中考试,他竟然不及格!要知道,这一门课是基础课程,如果考试不及格,联大没有补考而必须重修,重修通过后才能学后面的课程,相当于留级一年。
年轻的潘际銮静下心来分析:原来,联大的考试与以往的中小学考试有很大不同,考试内容不仅限于课堂内容、也不限于平时的习题,但凡涉及这门学科的内容,都要考!潘际銮找来了和“普通物理”相关的所有参考书,埋头苦读,融会贯通,终于“学活”了这门课,在期末考试中顺利过关。“联大‘逼’出了我的自学、治学能力,受益终身。”
潘际銮认为,宽严并济、自由创新是西南联大成功的关键。
宽松的环境。联大学生实行选修制,一个学期最少修16个学分,最多修32个学分,松紧由人;一门课好几个老师开,风格各异,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行选择;可以自由转系,甚至休学暂停学业,因此,同一年入读的学生,往往有3年就毕业、有8年才毕业。
学得好的学生,甚至不来上课老师也不会怪罪。潘际銮曾有一门课自学得当,很少上课分数也很高,老师点名时发现他不在,“这个学生成绩这么好,怎么没来上课?!”但期末打分,老师一样给了高分。
严谨的治学。联大没有补考,不及格就重修,基础课程不通过就不能学习下一阶段的课程。但老师们却没有因此而“放水”,一方面要求高,学生得融会贯通相关领域的许多知识,活学活用;一方面打分严,许多课程的不合格率高达1/3。
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王希季,也曾经因为拉计算尺(电子计算器的前身)弄错了一位,在机械系的刘仙洲老师手下得了零分,王希季说:“他的严格,对我们学工程的非常有教育意义——不能丝毫疏忽或大意。后来我从事航天事业,兢兢业业,很得益于刘仙洲先生。”
联大当年学习环境简陋,校图书馆仅有200个座位,为了读书,潘际銮、汪曾祺等人常常就抱着一沓书,去校门外的茶馆里买一杯茶,从早读到晚。当时甚至上课的桌椅设备也不齐全,上课去晚了就没地方坐。所以,每次上课钟声响后,就会看到男男女女满院奔跑去抢座位,一旦抢不到座位就只能站着听课、记笔记。
联大8年,学生入读8000多人,真正毕业的只有3000多人,除了抗日、革命、因故休学的同学,不少人就是过不了关而拿不到毕业证。但就在这3000多人中,出了100多名院士、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教育的焊接
潘际銮痴迷联大,也努力将联大的治学精神“焊接”到教育实践中。
1993年,潘际銮应桑梓之邀,担任江西省南昌大学校长,当时江西是个“三无省”——无重点高校、无学部委员、无博士点,潘际銮是去“救火”的。时任江西省长吴官正向外表态:“我不懂教育,一切问题听潘校长的。”压力,都在这位当时已经65岁的老人身上。
潘际銮和老伴有饭后散步的习惯,当他看到傍晚校园里,南大学生学风涣散,忙于跳舞、打桌球、谈恋爱,考试“60分万岁”,这位性格随和的老院士显出了“牛脾气”:他要把联大的治学引进来,彻底改变南大的学风。
他在南昌大学推行本科教育改革,“学分制”、“淘汰制”和“滚动竞争制”,这些当年让国内高校同行瞠目的制度,有浓厚的联大烙印:对各学期未修满规定学分数60%的学生,要求缴纳全部培养费,并跟班试读一次,仍未修满学分数60%以上者,予以退学;对公费生和自费生实行滚动竞争,学习不好的公费生可能转为自费生,而学习好的自费生则可以转为公费生。
“教育就像一个人游泳,只要能游到对岸就行,谁来游、什么姿势都可以,这样才能出人才。”
很快,南昌大学学风陡转。1996年,南昌大学“211”预审通过;2002年,南昌大学不仅成为江西省唯一一所“211”重点大学,还成为江西省唯一一所由教育部与江西省共建的大学。
狠抓教学和科研的同时,潘际銮并不直接掌管学校的财务和人事。“他是个放权的校长。”潘际銮在南昌大学的一位同事说。
有人觉得潘际銮“傻”,他说,“我知道管钱和管人,哪怕只是管分房子,都是很大的权力。”但是,他不亲近这些权力,“教授治校,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按照教授的学术思想来办教育,因为教授就是个学者,对教育很了解,学校应该怎么办他们很了解。教授治校的目的不是教授要权力,而是保证学校能按教育规定办下去,教育思想能贯彻到整个过程中。”
南大10年,潘际銮亲近的学生和下属也没有跟着“沾光”、得到“实惠”。
学生张华在南大任教,并没有“获得更多资源”,相反,潘际銮跟他说:“你就默默无闻地干,自己去争取课题,别指望在学校拿钱。”曾经给潘际銮做了6年秘书的徐丽萍,在潘上任时是正科级,直至潘卸任、自己离校,职级都没有改变。
对名利不敏感,对学术界“怪现象”旗帜鲜明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用这句话来形容院士评选并无不当。2010年举行的中国工程院第十次院士大会上,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徐匡迪在工作报告中坦言,院士增选工作受到的干扰有所增加,如候选人或其所在单位“助选”、“拉票”行为以及“集成、包装”现象等。
对于这些纷扰,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的潘际銮说,自己是“后知后觉”的。“当年就填了一张表”,简单地写下完成的工程成果,而且“也没发几篇论文”。后来,他被告知,“评上院士了”。
“我所获得的荣誉,都不是我追求的结果。”潘际銮说。时至今日,他既没有行政头衔,也没有秘书。
不少接触过潘际銮的人一致评价他,“对名和利,不敏感”。
对好处不敏感的潘际銮,对于“涌”到眼前的学术界一些“怪现象”,则旗帜鲜明地持反对态度,“得罪了不少人”。
“SCI写不出《红楼梦》!”
对于目前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纷纷以SCI论文发表篇数作为考评老师和科学研究者的方式,他不以为然。
“袁隆平从1964年开始培育杂交水稻,6年没有出成果,更没有写几篇论文,还不是一样养活了几亿人?”
潘际銮回忆,早在10年前,他就已经呼吁不能“唯SCI”。“若干年以前,中国还不知道有SCI这个事,南京大学统计了一个SCI,说自己‘全国第一’。这下清华北大不就着急了吗?你难道就走到我前头去了?清华大学马上出来一个政策,每人都要求出两篇SCI论文,出一篇奖励8000元,所以清华的排名一下子就上来了。
现在我们的报纸都在宣传,说我们国家的SCI论文已经世界第一、超过德国。但是技术上,我们好多技术还是从德国买回来的,论文超了德国有什么用?真正的还是要看你的创新能力和实力。这都是浮躁情绪。”
对于自己手下学生和老师头顶上悬着的SCI“达摩克利斯之剑”,潘际銮有些无奈,“我只能说,你们不要看重论文,要看成果和你的工作成效。但是学生跟我说,‘老师,我不写论文我毕不了业呀’。老师也很苦,论文出不来就提不了职。
你有什么办法?现在要他们静下来写一本著作、搞一个大成果,这不太容易啊。所以我提倡两句话:‘谦逊治学,宁静致远’。安安心心地研究学问,才能走得很远。没有这两点,中国小成果可以出,很难出大人才。对吧?”
“我喊了10年,没用。现在还是SCI称王,所以我说,我过时了。”
对于评选院士的怪现象,潘际銮也不大关心,但对于铁道部原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当年“冲刺”院士一事,他是院士中少有的公开发声者。“我们都是学者,明白谁也不可能两年时间写两本专著。”
2007年,潘际銮最后一次参与增选院士的投票(2009年因年满80岁成为资深院士,不再参与投票),张曙光那一年恰好第一次“冲击”院士头衔,以在职博士的身份成为候选人。“这个是很罕见的,你博士还没有毕业,说明你还不具备博士水平,你怎么能够来选院士呢?”潘际銮印象很深刻。
院士大会投票期间,针对张曙光所提交的学术成果是真是假,院士们争议很大。潘际銮说,当时,不少院士的疑惑是:他平时抓工程那么忙,哪里有时间和精力写专著?
“我们又提出,能不能把草稿拿出来给大家看看。最后,稿子也没能拿出来,大家心里就明白:这不是张曙光自己写的。”潘际銮回忆,这个要求最终没有得到张曙光本人的回应。最终,张曙光冲刺院士头衔告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