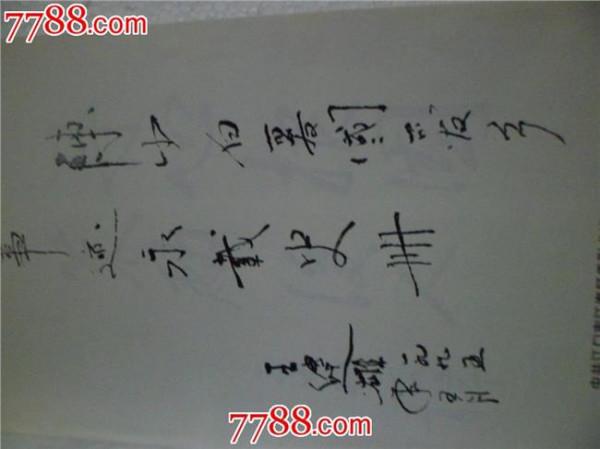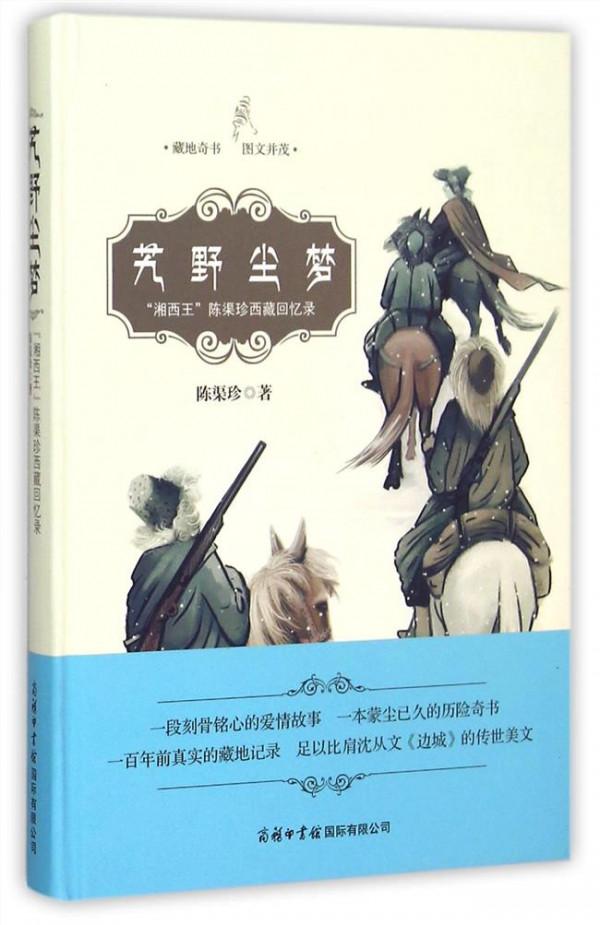陈白尘的女儿 陈白尘女儿回忆父母半个世纪的爱情
陈白尘女儿回忆父母半个世纪的爱情
“嫁给你是我自愿的”
那是1939年,爸爸陈白尘(1908~1994)因养伤,来到重庆歌乐山中一个名叫高店子的小镇上——
……主人杨英梧年纪不大,却已有了一儿一女。他的妻子叫金淑华(这是妈以前的名字,跟爸结婚后改名为金玲,是爸给她起的),不多言不多语,吃饭时总爱用那双深邃的大眼睛时不时地对着新来的客人瞅上一眼。
“这个女子真单纯,真年轻,就像是一名刚刚迈出校门的女学生!”——这是这家女主人给我爸留下的第一眼印象。
“你今年多大了?”一次杨英梧不在家,我爸忍不住向她开了口。
“21岁,属马。我们是父母之命!就连高中都没有让我读完……”“女学生”的那双大眼睛黯淡了下去。
我爸一下子慌了:“真对不起,我看杨英梧还是很爱你的。”
“不,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爱情!”“女学生”脱口而出,竟令我爸大吃一惊。“我向他提出过好几次离婚的要求,他都不同意!”
后来,我爸终于一点一点地了解了她的身世——她是江西九江人,父亲为当地一位资产颇丰的商人。由于姐姐欠了镇江姓杨的人家一笔人情债,便动念要把自己的妹妹许给人家作媳妇。
“陈先生,不瞒你说,你写的剧本《虞姬》,我在初中时就读过了。”“女学生”的眼里闪出一星光亮,但很快又黯了下去:“杨英梧心里只有钱,而我也只是他的生儿育女的工具……”
这样的谈话一直断断续续地进行着,但我爸那只木箱子里的书却被“女学生”一本又一本地读完了……
后来,便是妈不顾一切地从杨家跑了出来,吃了很多苦,终于嫁给了我的爸爸,一次她对爸说:“嫁给你是我自愿的,吃苦受穷也是我自愿的……”
“七年中我俩的家书一千多封”
妈这辈子最大的懊悔是什么呢?直到我读完她写的《祭白尘》后才明白——
“文革”中,你被揪去干校,关进牛棚,从此我们天各一方。在离别的七年中,我们只有每天通信,若有一日接不到信,你我都会焦虑万分。你每封来信中,不仅告诉我你所受到的遭遇和迫害,更重要的是在这人世间你有了一个诉述苦闷和烦恼的知己。7年中我俩的家书加起来该有一千多封,然而懊悔的是,当时为了怕抄家,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每封信的末尾都写上“看后即焚”,竟是一封未能留下……
爸是1966年的9月11日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从南京揪回北京的,从此之后竟连通信的自由都没有了——不仅每一封信都要经过专案组的审查,而且还每每在信封上打上几个黑××:“你的老婆居然还称你为‘同志’!——你要明白自己的身份!”
这一年妈才48岁,由于此前文艺界已被折腾出了一场规模不小的“文化小革命”,不仅爸被发配到了金陵,妈也受到株连,被迫办理了退职手续……就这样,整整7年的光阴,我们一家人孤零零地生活在南京。——没有钱,妈不怕,她变卖了所有值钱的东西;但没有爸,妈撑不住了,她整日忧心如焚、怅然若失。
我没有看到过妈给爸写的任何一封信,但我看到过妈每天等盼邮递员时的焦虑身影——倚着门,伏着窗,一动不动,如同石雕一般。
妈此时的苦,不仅是思念,更是无法传递这思念。——爸给妈写信,可以寻找机会避开造反派的视线,将信掷入路边的邮筒里;但妈给爸写信却难了,既要能够顺利地通过检查,又要能够让爸读懂其中的意思。我不知道她用的是什么方法,直到有一天——
……那天其实也很平常,大妈在厨房里烧饭,妈推门走了进来。她掀开锅盖,小心翼翼地撇出一小碗米汤,浓浓的,泛着泡沫。大妈说,妈身体不好,权当补充一点营养。不料回到卧室后,妈却关上了房门,拉上了窗帘,举止极为诡秘。我忍不住扒着锁孔向里偷看——只见她先是拿出一张报纸,继而又取出一根竹签,然后蘸着那碗米汤,在报纸四周的空白处匆匆写了起来。
“妈,你在干什么?”我猛地撞开了房门:“这也不是墨水,怎么能写得出来?”妈抬起头,望了望我,不仅没有丝毫的责怪,反而是一脸的神圣与庄重。“只要拿酒精一涂,就能显现出来。这是解放前你爸干地下工作时教会我的……”
“妈!”我的心狂跳不已,既为偷窥到了一项绝密的工作,又为发现了妈的一个重大秘密——隔不了几天,她就要给爸寄去一张报纸,说是上面有重要的社论,让他认真学习。
整整7年的离别,整整7年的相思,爸究竟从妈的去信中获得了什么?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孙××将南京寄来的包裹当面拆开,检查无讹后方交还于我。返回宿舍,立即从“机密”处寻到玲的附信,读后心潮起伏,不能自已,大呼:“玲知我!玲知我!”
这是1971年的事情。爸的“问题”升级了,《红旗》杂志登出了批判他的文章,干校接着也“狂轰滥炸”了起来。他愤怒,他无奈,但身边没有一个可以倾诉的人。妈在南京也看到了这篇文章,她同样气愤,同样无奈,但她明白这时的爸最需要的是支持,是理解。于是她又动脑筋了——必须要写一封长长的信,一封能够逃避检查的信,将心中的一切表述出来。
那晚,她手中拿起的不是竹签,而是缝衣针。她亲手为爸缝制了一件中式的棉袄,不为别的,只为在那个衬有袼褙的硬领里藏匿起她的家书——一封足足写满了六张信纸的家书!妈的女红实在不敢恭维,针脚歪歪斜斜尚且不谈,手上更是扎出了不少的针眼。
最后还是叫来了大妈,在她的帮助下,总算做成了这件衣裳。我不放心,悄悄地问妈:“爸怎么会知道棉袄中的秘密?”妈只回答了我一句话:“心有灵犀一点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