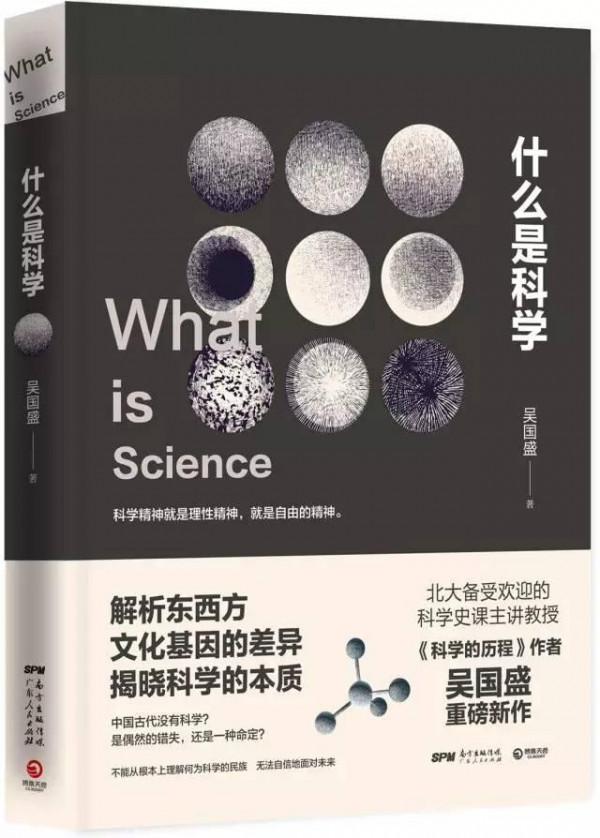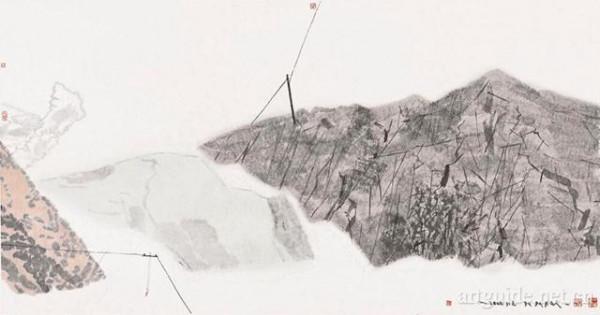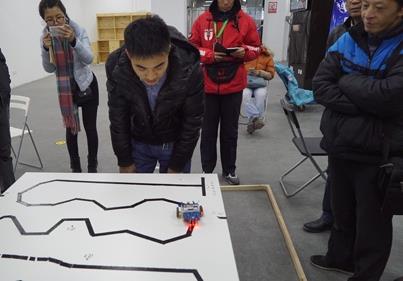吴国盛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教授吴国盛:“科学”最初是无用之知
在偶像被一一请下神坛的时代,科学仍是人们喜爱和崇拜的事物。也许正是敏感到这一点,很多鸡汤手和骗子们,口吐莲花前,总喜欢冠以“哈佛大学教授某某说”“研究成果表明”之类的前缀。
入瓮上当者还不少。
为什么会这样?
一个“有点大”的解释是,“科学”概念广为普及,不等于科学精神深入人心。
精神的培育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它涉及文化、教育,种种因素。科学精神是求真较真的精神,要耗费智力体力,不容易坚持。科学精神各地都有,但在个别地方特别浓郁,成果最繁盛,派生出成熟的体系。
吴国盛是中立研究者,但我猜他在爬梳古希腊经典时,一定会为那种古典的、纯粹的,只为真理哪怕无用的执着深深打动。
“中国不是科学的故乡”,这观点一经抛出,激起千层浪,五位学者聚首北京激辩。质疑者提出,不能认为只有古希腊才有科学,也不能认为中国古代完全缺失数学、逻辑和实验。
中科院大学教授孙小淳,更是抓住吴国盛的软肋,指出他把“科学”定义成了与“现代科学”一样的东西,“要是这样的话,那不仅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世界上任何古代文明都没有科学,包括古希腊文明自身”。
这看法很犀利,也很在理。吴国盛承认,尽管他对于“什么是科学”有着自己的理解,这里仍涉及一个如何定义的问题。他并不指望通过一本书,就给出一系列自洽而完备的定论。
他更在意提出有价值的问题,譬如:中世纪在现代科学演变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数学为何及如何用于现代科学,现代科学为何是求力的科学,现代科学如何造就“无情”之社会和人心,等等。他不仅提出问题,也给出“闪烁着思想火花”的回答和洞见。
包括“李约瑟之问”在内,难题仍将是难题,争议仍将会继续。所幸的是,从古老但并不久远的某天开始,智慧与科学的真爱已然出现,迄今仍在向各个角落扩散。 文/刘功虎
中国古代无“科学”,是因为生活理想不同
记者刘功虎
古希腊科学的发生是一个谜
读 :在你看来,“科学”并非横空出世,它从一开始就是特定文化的产物,怎么理解?
吴国盛:过去我们有一个错误的看法,认为科学与文化无关,是普遍有效的,代表着人类这个物种最先进的生活形态。其实,科学对于人类的基本生存并不是必需品。
历史上大多数时期、大多数民族,没有科学。科学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化现象,或者准确的说,科学是西方这个特定的文化传统中产生的特定文化现象。
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人文传统,会孕育出不同的知识类型。在西方,这个知识类型就是科学,而在我们中国就不是科学,而是礼仪伦理。
读 :最早的“科学”,为什么会发端于古希腊?
吴国盛:历史学家大致认为,不同于中国的农耕文明,希腊多山的地形导致粮食不足,海岸线发达导致贸易盛行。他们发展出一种不同于“熟人社会”的“生人社会”,不同于血缘文化的地缘文化。他们更强调契约,不同背景不同出身的人走到一起,生活在一起,需要定一套规则。比如说,要开会就好好坐着,把手机关掉,不要讲话之类。
如果说我们中国人的核心人性理想是仁爱的“仁”,那么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就是契约和自由。所谓自由就是“由自”,由着“自己”,按照自己和大伙协商的逻辑、规则来办事。什么又是“自己”呢?这需要去认识,“认识你自己”。
从认识自身出发,希腊人推出了“理念”这样一个东西。什么是理念?以圆为例,我们可以说瓶盖是圆的,但是你仔细量一量会发现,那个瓶盖并不真的圆。真实的圆,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希腊人就问,真正的圆在哪里?他们的回答是,在理念世界。
毕达哥拉斯做几何证明,不拿尺子量,从头到尾都是概念、逻辑起作用。古希腊科学一开始走的就是推理、论证、证明、演绎的道路。
读 :古希腊科学还有什么鲜明特色?
吴国盛:古希腊科学不追求有用。在我们中国,在世界上其他很多地方,人类的知识都是实用型的,但在古希腊人看来,你学的如果只是一些有用的知识,那是低级趣味。只有无用的知识,才是高尚的知识,真正的知识。
讲理,讲死理,就理论理,成了古希腊科学的一个基本特征。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他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读 :你刚才提到的“地理决定论”,我感觉还有些不满足。希腊人那么早就有那么发达的抽象思维能力,原因究竟何在?
吴国盛:这是一个谜!
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从古希腊发端,是一件很罕见、很偶然的事情。就像披萨就是披萨,大饼就是大饼,他们是不同的东西,不同的特产,我们没法抹平他们的“出身差异”。
长期以来,人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古希腊人那么爱想事,我个人给出的破解就是,古希腊人很早就强调个体自由、契约精神,而不是把人伦秩序视为核心人文价值,从而开掘出了科学传统。他们就那么选择了,科学就那么生长了。
现代科学:把自然抓起来,关到实验室里去
读 :那么,科学后来是如何从无用变到了有用呢?
吴国盛:古希腊科学作为没有用的科学,时间没有持续太久,随着希腊文明的衰落而衰落。文艺复兴之后,欧洲人重新发扬光大古希腊的科学传统,并且酿造出另外一种科学类型,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现代科学。
现代科学追求有用,两个人很关键。一个是培根,他讲“知识就是力量”。他一语道破现代科学的特征:科学应该成为力量型的知识,成为有用的科学。培根批判古希腊人都是孩子,爱玩儿,不懂得把科学用来造福于人类,改善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
培根说要对自然界有一种新的态度,要利用它。培根还说,要征服自然必先顺从自然,欲顺从自然必先了解自然,了解自然不是一般的了解,应该把自然界抓起来,拷问它,让它供出自己的秘密。所以培根的思想实际上为实验科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哲学依据。可以说,现代科学一开始就走上了实验的道路。
读 :另外一个人是谁?
吴国盛:笛卡儿。他有句名言,“我思故我在”。这句话被认为是近代思想的第一声号角。“思想”、“理性”不再是“神”的思想,而是“我”的思想。“我”不是笛卡儿,而是我们所有大写的人。
以人为本,人成为时代和世界的价值核心,从今往后一切要按照人的目光去打量世界。这就是笛卡尔的作用。
读 :现代科学跟古希腊科学,最显著的差别是什么?
吴国盛:现代科学是从古希腊科学发展而来的,二者是源与流的关系,但现代科学提供了新的维度,力量、征服、实验。古希腊科学不做实验,认为动动脑筋就可以了。
现代科学是一个攻击型、进取型的体系,你也可以说是侵略型的。侵略谁?自然界。把自然物抓起来,关到实验室里去,让它处在一个非自然的状态之中,考察它们在不同的非自然条件下必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这就是实验。
只有到实验室里面来,让自然处在高温、高压、高浓度、高密度、高磁场或者是低温、低压、低浓度,总而言之在一种非自然状态下,自然的因果规律或许就能够显露出来。就跟驯马一样,你捅它一下看它有什么反应,如果你掌握了这个马的所有的刺激反应规律,那么这个马你就驯服了。现代科学的理想就是驾驭自然界,掌握自然规律。
中国古人走的是另一条道路
读 :依照你的逻辑,科学最初是古希腊的特产,因此古代中国无科学?
吴国盛:对,我是这么看的。
读 :为什么会这样?
吴国盛:我说了,中国文化是一种血缘文化,建立在自然农耕经济之上,以血亲为文化基因。中国文化是个亲情文化。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情是最高的东西,情感至上,理和法次之。
《论语》里讲一个故事:一个学生问孔子,为什么父母死后要守孝三年,为什么不是两年半,为什么不是三年零一个月,一定要三年呢?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但孔子没有正面回答,因为没法回答。孔子的方法是,通过唤醒他的幼年时的回忆,让他重温父母养育的恩情,让你逐步感觉到,问这个问题本身就不对,你不应该问这个问题。在情感的氛围当中,问题被消解了。
中国的文化以儒家仁义文化为主导,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关于理想人性的基本规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伦理学一直是我们这片大地上至高的文化理想,其他都不是很重要。古典中国有知识、有学问,这没有问题,但是没有西方那种知识、那种科学。
读 :为什么伦理先导的实用主义文化,很难发展出古希腊式的科学?
吴国盛:我给你举个例子。《论语》有个提法很有名,叫“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父亲犯了错误,儿子不要声张,不要举报。这跟古希腊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完全不同。他们把真理置于亲情之上,讲“理”讲到极端。前者从人伦角度没有错,但会妨碍求真;后者是极致的求真,但我们会认为不近人情。
读 :如果说中国古代无科学,有人心里会有点难过。如何排解这种心结?
吴国盛:没关系的,中国古代无科学,因为科学指的就是古希腊人的知识类型。中国古人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不丢人。我们不要对传统妄自菲薄,更不要污蔑自己的祖先。任何一个伟大的文化,都具有丰富的多样性资源,有自己的内在张力。
读 :那么,可以认为现代科学比古希腊科学更“先进”吗?
吴国盛:我要说的是,我认为现代科学对古典科学有所背离,而这是造成现代社会诸多问题的根源之一,需要有所矫正。现代科学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自由精神和科学精神本身。科学无限征服自然,但问题是,我们本身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征服和控制了自然,同时意味着对自己的征服和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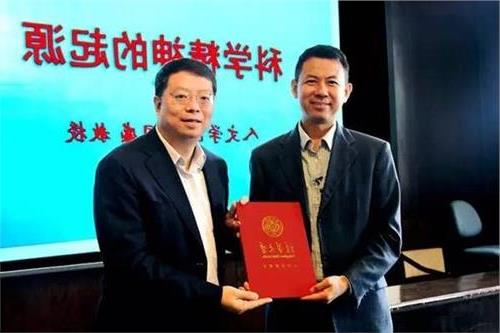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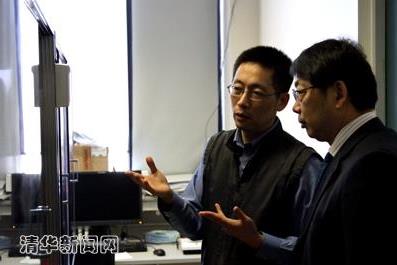


![>清华高鸿钧 高鸿钧[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https://pic.bilezu.com/upload/7/43/74321564f207431a4ea5823b8711099d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