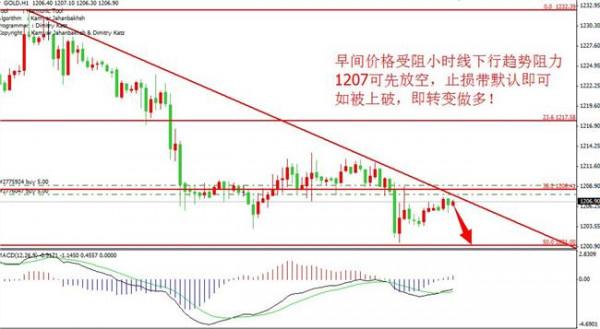白淑湘家庭 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中国第一只“白天鹅”著名舞蹈家白淑湘
白淑湘(1939~)中国女芭蕾演员。国家一级演员。1939年11月18日生于湖南省耒阳。1952年参加东北人民艺术剧院儿童剧团,1954年选送入北京舞蹈学校学习芭蕾。白淑湘身体条件不算好,但她勤学苦练,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掌握了高难度的芭蕾技巧和特有的韵律,仅以4年的学历,就成功地扮演了《天鹅湖》中的白天鹅和黑天鹅,受到舞蹈界和观众的欢迎。
在中国芭蕾《红色娘子军》中,她成功地塑造了女主角琼花的形象。在《海侠》、《吉赛尔》、《巴黎圣母院》、《巴赫奇萨拉依泪泉》和《希尔薇娅》等10多部古典芭蕾剧目中,她都曾担任过主要角色。
她的表演感情真挚、动作准确规范,风格明快。1980年在菲律宾国际芭蕾舞节上,她与其他中国演员合作,共同获得集体表演一等奖;同年,被特邀参加第一届全国舞蹈比赛,表演《天鹅之死》,获优秀表演奖:1981年在文化部直属艺术单位观摩比赛中获表演一等奖。
她还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出席过全国群英会。白淑湘还曾赴朝鲜、缅甸、美国、法国、日本等许多国家访问演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白淑湘荣获德艺双馨终身成就奖
白淑湘现任中央芭蕾舞团副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舞蹈家协会理事等。
跳舞是我的生命
中国第一个在古典芭蕾舞剧《天鹅湖》中扮演奥杰塔,在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演绎吴清华的芭蕾舞演员,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白淑湘:
跳舞是我的生命但再辉煌也要下台的
天鹅,在碧波上悠然滑行,在白云间飘然飞翔,是自然界优美而高洁的象征。
芭蕾舞,则是艺术界优美而高洁的代表。在那一出最著名的、表现天鹅的芭蕾舞剧中,女主角除了优美、高洁以外,还有一种内在的坚强,有一种遭遇残酷不屈不挠的精神。
11月底,我们采访了一位同样优美、高洁而又坚强的女性,她就是现任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白淑湘。她,是中国第一个在古典芭蕾舞剧《天鹅湖》中扮演奥杰塔、在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演绎吴清华的芭蕾舞演员。然而,她的舞台生涯却免不了那个特殊年代政治风云的吹袭。
她的父亲,一个法津专家,曾是张学良的部下,在1957年肃反时被关,没经过什么司法程序,就被打成“反革命”处决了。她是演完《天鹅湖》,下了舞台后才知道的。
她自认为只是个普通演员,没有觉悟也没有胆子真的反江青。但她戴的反江青帽子却一再加码,特别是到了1965年末,就不准再上台了,只能打扫卫生。在小汤山劳动改造期间,每天早上5时就起来捡牛粪、烧开水,还要进北京城去掏人粪。在她被劳动改造期间,男朋友也来批判她……
但她坚持住了。在将近10年之久的苦难之后,她迎来了自己芭蕾艺术的春天。曾经给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表演过的她,直到50岁那年,在中央芭蕾舞团建团25年那天,才在告别演出之后与舞台告别。
我1992年随中央芭蕾舞团到台湾访问演出,见到了张学良伉俪。
记:我们在全国政协赴粤视察团中发现你的名字,就马上联系专访你这位舞蹈家。
白:我早就已经告别舞台,你们怎么会知道我呢?
记:可我们的父母看过你的演出。你是中国第一个白天鹅,第一个吴清华,你的故事一定很有意思。听说,你的父亲曾是张学良先生的部下?
白:是呵。父亲是燕京大学法律系高材生,后来是东北大学的第一任法律教授,并任张学良东北政府的财政专员。他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到湖南沅陵县当县长,在抗日时期为前线组织粮食。我这个辽宁人因此在湖南出生。7岁时生母就去世了,之后随父亲的工作变动到南京、广州、沈阳等地生活。
记:那你见过张学良先生吗?
白:我1992年随中央芭蕾舞团到台湾访问演出,见到了张学良伉俪。当时,老人家思维很清晰,他说还是在60多年前看过白俄人跳芭蕾舞。我告诉张叔叔:“您是民族英雄,在抗战期间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人民都很尊敬您。您尽量回内地看看,现在少帅府已经重新修整了,还建了纪念馆。”张叔叔送了我一本书,张夫人也送了我四本书,我将自己所作的山水画送给他们。
记:那你是怎么进入文艺界的?
白:1952年,我13岁小学毕业,正准备考中学,这时候东北人民艺术剧院去招演员。我很羡慕那种集体生活,就悄悄地报名参加了。我一进东北人艺,领导就说:“你现在参加革命了。”我从此就成了公家的人,每天练功、排练、学文化,然后演出歌舞、合唱和话剧。
最难忘的是在抗美援朝期间,我们去朝鲜慰问志愿军和人民军。那里的条件很艰苦,战争很残酷,我们在冰天雪地中坐着卡车,一到连队就在煤油灯下演出。
苦干了4个月,脚都练出血了,创造了中国芭蕾舞神速的“三级跳”。
记: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芭蕾舞的?
白: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成立,我和东北人艺的20多位同事成为第一批学员。我因为有舞蹈基础,就直接被分配到3年级,一年后进入芭蕾舞专业。我1956年才第一次真正地看到芭蕾舞表演,一下子就被迷住了,太美了!
记:是前苏联舞蹈专家伊莲娜等来表演的吗?
白:对。她们在1954年来中国培训师资。1957年以古雪夫为组长的苏联舞蹈专家小组,培训学生的基本功、单人舞、双人舞。
记:你们仅仅练了一年芭蕾,就开始排演《天鹅湖》?
白:是呀。《天鹅湖》是最为著名、代表俄罗斯风格的芭蕾舞剧。周恩来总理当时问古雪夫:“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排这么大的舞剧?”专家回答说:“能。”于是,1958年初,我们年级找了6男6女开始排《天鹅湖》,我有幸被选中。
这是我们国家排演的第一个芭蕾舞剧,服装、灯光、舞美等等都是完全陌生的,我本人在此之前甚至没怎么听过西洋音乐,《天鹅湖》的原版电影也未看过。我们这些初生牛犊有一股冲劲,日日夜夜拼命地学,就这么苦干了4个月,脚都练出血了,创造了中国芭蕾舞神速的“三级跳”。
记:除了动作、舞美等等困难以外,观念上有什么障碍吗?20世纪50年代人们看得惯这种穿得极少、男女相拥的舞蹈吗?
白:唉,学校的老师也这么担心过。但苏联专家教导我们,怎么创作角色、表现美,把我们引领到纯净的艺术天地中去。当然,我们的王子和天鹅,还真地有一对成了爱人。
记:你们第一次演出怎么样?
白:那是1958年的6月30日,在北京的天桥剧场,由我主演白天鹅、黑天鹅。中央领导周恩来、陈毅和周扬来观看。
记:你当时才19岁,演出的时候是否紧张?
白:当时并没有紧张,演完后我们才感到吃惊。总理开心地对我讲:“听专家说,你很努力很刻苦,希望精益求精,成为行家。”苏联专家后来总结道:“中国的演员有前期的表演经验,因此能在4个月里排出这部舞剧,这十分令人满意。”我个人则体会到,跳舞需要体力、耐力和技巧,但更需要艺术创作,表达出人物的个性和感情,比如在天鹅湖中就特别要刻画出白、黑天鹅的不同性格。
1958年是全国人民情绪最高涨的一年,我们就一鼓作气,又接着排《海侠》,我仍然演女主角米多拉。我感到在艺术上渐入佳境,创作的空间越来越广。1959年12月,中央芭蕾舞团成立,我就成为其中一员。
那时候人们太饿了,音乐学院好不容易有一顿鸡蛋炒饭吃,就有人一下子被噎死了。
记:你的艺术道路一开头就比较顺利。
白:算是吧,我相继主演过《吉赛尔》、《泪泉》。但从1960年起,我们和全国人民一样遭遇了经济困难。所配给的粮食很少,人们普遍因营养不良而浮肿。政府很照顾我们,给主要演员发了黄豆、古巴红糖、伊拉克枣、糖果和罐头之类的食品,但我们都处在长身体的年龄,主食根本不够吃,吃一些玉米秆磨的粉,粗得像啃汽车轮胎般难以下咽,而且吃了以后消化不良。
那时候人们太饿了,以至于音乐学院好不容易有一顿鸡蛋炒饭吃,就有人一下子被噎死了。团里就尽量减少我们能量的消耗,只练练功,不需演出。
记:这时候中苏关系已经破裂了,苏联专家怎么办?
白:就在排练《泪泉》时,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古雪夫等专家在中国工作了6年后,中国的芭蕾舞刚刚起步,就不得不于1963年撤走。他们对我们很有感情,不舍得走,但没有办法,实在太可惜了。幸亏中国的两个留苏学生蒋祖慧、王锡贤就在这一年回国,接手了编导工作。我们在1963年又排演了《巴黎圣母院》,并到南京和上海演出。
我从演公主、小姐,到表现女革命者形象,心里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记:你们的效率很高,几乎是平均一年演一部古典舞剧。
白:1963年文艺界提倡反映现实。周总理提出:芭蕾舞已经演了5个古典舞剧了,能不能用这种形式来反映我们自己的内容?于是,舞蹈界考虑了很多题材,如阿诗玛、达吉、王贵与李香香等等。当时电影《红色娘子军》正好获得百花奖,于是被确定改编为芭蕾舞剧。
记:你一开始就被定为扮演琼花,后来叫吴清花。你参与了创作,是吗?
白:是的。1964年2月,由编导、演员和舞美设计组成的一共10个人的小分队出发,其中就有李承祥、王锡贤、蒋祖慧,还有扮演洪常青的刘庆棠。我们先到广州找原作者梁信,了解创作过程,他所讲的娘子军故事真实感人。我们随后到海南,深入连队和村寨,一边创作一边体验生活。我们看到了海南人民过去受压迫的实物,也听了红色娘子军原来的冯增敏连长的亲自介绍。舞剧里活泼可爱的小女战士,是有真实原型的。
到4月份,我们回北京开始排练,由吴祖强、杜鸣心作曲。7月份,陈毅元帅等看了演出,可大家评价“像娘子不像军”。的确,芭蕾舞从来都是表现王子、公主的,现在表现女奴、革命军人,这个跨度太大,延用软绵绵的动作怎么演得出这种新形象?我们重新思考。
为了进一步体验革命军人的内在精神,我们又到山西大同的部队,跟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回来后感觉果然大不相同。原先,我们生怕不像芭蕾舞,所以动作脱不开传统的程式。比如,琼花与狗腿子老四对打的一节,按旧式的双人舞设计,两人在扶来扶去,哪里像是打人者和反抗者的关系?改过后的设计借鉴中国戏剧和武术动作,加强对抗性动作,勾勒了人物的性格和关系。《红色娘子军》的整个创作,对编导和演员都是一种创新。
记:我看这出戏的时候年龄很小,但迄今印象极深,可以看出其吸收了中国古典舞、民间舞的技巧。像“男青年钱铃双刀舞”、“黎族少女舞”,明显是运用黎族民间舞形式。还有,“射击舞”、“投掷舞”、“大刀舞”、“队列舞”等,可能在芭蕾舞史上首次有表现军旅生活的舞段。
白:是的。我自己从演公主小姐,到表现女革命者形象,心里有焕然一新的感觉。1964年9月26日演出,仍然是在北京天桥剧场,总理观看了我们的演出。他还向外宾推荐中国这部第一部芭蕾舞剧作品。毛主席在同年10月8日也来观看,他很高兴地与我们握手。周总理鼓励我们说:“革命是成功的,方向是对的,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艺术上也是好的。”
我与周总理说话都挺坦然,可江青却令我很紧张。
记:你后来倒霉与江青有关吗?
白:这个过程太多传言,直到昨天还有人问我这些事。我由于不是工农兵出身,从1963年起就陆续有些压力,被当作“白专”批评。我当时不服气,明明在学校里被评为“又红又专”,是“五好学生”,为什么一夜之间我就变成“白专”,连团支书的职务也被撤掉了?在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演出期间,我白天要接受批判,晚上要上台,心里很不痛快。
江青看了《红色娘子军》后,把芭蕾舞团定为样板团。她把这部戏当成她自己的成果,说什么“十年磨一戏”,其实她没编没演没创作一个音符。她所谓“呕心沥血”地修改,只不过是乱指挥,像强调“三突出”构思。
记:你对她的感觉如何?
白:难相处。我与周总理说话都挺坦然,可江青却令我很紧张,她还打听过我的出身。当时我一直不知道她是毛夫人。
记:江青是中国文艺界的慈禧太后,你是怎么得罪她的?
白:我之所以被定罪“反江青”,是有故事的。江青很在意别人的逢迎,可我有时没有主动回答她的问话。有一次在上海演出结束后,别人都把江青送到了车门边,而我没有。因此,“文革”时,别人揭发我在江青面前目中无人。
江青喜欢拍照。1965年的一天,她来拍剧照。我在化妆室里的时候,江青进来了一下,大家以为江青来给我化妆,实际上是化妆师化的。化好后,江青看了很不满意,就对化妆师说:“我们的合作很不理想。”她这句话就像老佛爷的圣旨,把化妆师吓哭了。
她给了我一个小时让我自己化妆。既然要重新化妆,就要先卸妆,没想到别人都说我胆子太大,连江青化的妆都敢卸。后来我挨批判时,这也是一条重要罪证。还有,江青拍剧照时,不断地让我调整位置。我当时又累又紧张,就反应不过来了。她让我往左一点时,我没想到江青在我的对面,她的左边就是我的右边,就往自己的左边动了一点,于是她就生气了,说我左右不分。后来,人们又以此来批判我,说我故意与江青作对。
记:其实都是小事。
白:可不。我只是个普通演员,当时没有觉悟也没有胆子真的反江青。可我戴的帽子却一再加码,特别是到了1965年末,就不准再上台了,只能打扫卫生。当然,这也与我父亲有关。我父亲在1957年肃反时被关,他这个法律专家没有经过什么司法程序,就被打成“反革命”处决了。我是演完《天鹅湖》后才知道的。
有人说我和毛主席握手时想起了自己被镇压的父亲,眼睛里带着阶级仇恨。
记:你父亲的事让你雪上加霜?
白:是的。我从12岁开始,就在革命队伍里成长,可从1965年起,我却被推进反动分子行列。我表示与家庭划清界限,但他们还不满意,让我从思想深处挖出什么根源来,我的日记、过去的检讨都被当作反面材料。我必须把自己往坏里讲,不然就通不过。从演《天鹅湖》到《红色娘子军》都与我搭档的刘庆棠,那会儿也说:“谁革命谁反革命,是时候出来遛遛。”
记:那是人斗人的时候,连幼儿园孩子都要自查,何况你这位大明星。
白: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过去的朋友,像同剧组、同宿舍的同事都来揭发我,写大字报骂我,将我的一言一行上纲上线,列的罪名五花八门。比如有一次,毛主席来看演出,领导告诉我们不要往前拥,于是我很听话,结果有人说我对毛主席没有感情。还有人说我,和毛主席握手时想起了自己被镇压的父亲,眼睛里带着阶级仇恨。
记:你是不是树大招风,许多人出于嫉妒?
白:那时候,我不能高兴,人家会说你不认真改造;也不能不高兴,会说你对改造不服气。我们团包括我有10多个“反革命分子”,被下放小汤山去劳动改造。那里的名人可不少,互相见面只能点点头,像音乐界的盛中国、舞蹈界的戴爱莲、蒋祖慧,还有京剧界的李少春、刘秀荣、赵燕侠。
记:你当时27岁,一定有恋人,他给你支持吗?
白:在我最倒霉时,连男朋友也不相信我。我被劳改,他也同样被戴上了帽子下来改造,可他却自以为比我红一些,也来批判我。于是,我们就分手了,我当时痛苦得麻木了。
这10年的经历给我很大的打击,我到现在也很自卑。
记:在干校干什么工作?
白:每天早上5时就开始捡牛粪、烧开水,还要进北京城去掏人粪。虽然我被批斗多了,一般也不怕羞了,但到西单一带掏粪还是觉得尴尬,当然也有些怕臭,所以冬天、夏天都戴着口罩。结果,又被批判成是“放不下资产阶级的臭名。”
记:这与你过去所表演的东西反差太大,你还想过回舞台吗?
白:哪里敢想。有一次,我干活累了,下意识地抬高了腿,就被批判为“贼心不死”。我的箱子底留了一对舞鞋,也被说成想复辟。唉,真是天无晴日,黑白颠倒,有的艺术家在那里自杀了。但周总理说的话始终在我脑子里转,就是:“相信政府,走自己的路。”所以我挺了下来。
记的有一年冬天挖树坑种树,管我的人竟然提前在我的地头浇上水,一夜工夫土就冻得非常硬,第二天我挖的时候特别吃力。别人的坑都挖完了,我踩破了鞋子也没有挖多少,他们就现场批判我的劳动态度。我完全没有了自尊。
记:这种日子熬了多久?
白:从我离开舞台算起,有9年。到1974年,周总理问起我的情况,我才回到北京。江青说是要我回团里继续受批判,我天天要在会上挨批。领导让我给江青写了认罪书,最后把我定性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于是,我这才又有机会上台。我因为跳《红色娘子军》被弄了下来,又因为它回到了台上。记得那天我握着练功杆的时候,悲喜交加地哭了,似乎积攒近10年的眼泪在一刹那都涌了出来。那么多年没练功,我的体重达到65公斤。可为了重返舞台,我在两个月中拼命地练,体重掉到53公斤,脚痛得每晚都醒,但一上台就忘了。我是不是很傻?还是我将舞蹈看得太神圣?
记:我理解,登上舞台是舞蹈家的最大心愿。
白:我后来又演了几部革命芭蕾舞剧《杜鹃山》、《沂蒙颂》、《草原儿女》。但在重要演出时,我还是不能上,只能在后台拉大幕。我庆幸我没死,但这10年的经历给我很大的打击,我到现在也很自卑。
我先生支持我、帮助我,但因为舞蹈事业,我们没有要孩子。
记:打倒“四人帮”后,你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来了吧?
白:是的。1978年,我们上演的第一个古典芭蕾舞是《花园》,邓小平同志现场观看,消息上了《人民日报》,到年底我获得平反。我在1979年重新排演了《天鹅湖》、《希尔维娅》。我42岁学法语,1982年赴法国进修了一年。从里昂到戛那,从卢浮宫到枫丹白露,我如饥似渴地汲取法兰西艺术营养。1983年以后,又接触到了丹麦、英国的流派等等,排演了《仙女们》、《堂吉诃德》。
记:你的舞台生涯算是辉煌了。
白:我曾经给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表演过。跳舞是我的生命,但再辉煌也是要下台的。我在50岁那年、中央芭蕾舞团建团25年那天,作了告别演出。
我不亲自跳了,但还是在台下做促进舞蹈事业的工作。我的个人生活也很幸福,在1977年结婚。我先生支持我、帮助我,但因为舞蹈事业,我们没有要孩子。
记:你如何看待现在的中国芭蕾舞?
白:如今已经是第6代《天鹅湖》、《红色娘子军》,一代比一代的条件好。虽然芭蕾的技术重要,站不稳、转不稳就不行,但关于人的艺术就要了解人。如今的演员基础教育不够,文化课太少,历史课取消。年轻人不懂古今中外的历史,不会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就不能准确地认识自己、表现人物、掌握艺术。比如,不了解中国传统戏曲的虚拟表现手法,就难以在芭蕾舞中借鉴。
最后说一句,我是个舞蹈者,算不上艺术家,中国的各种“家”实在是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