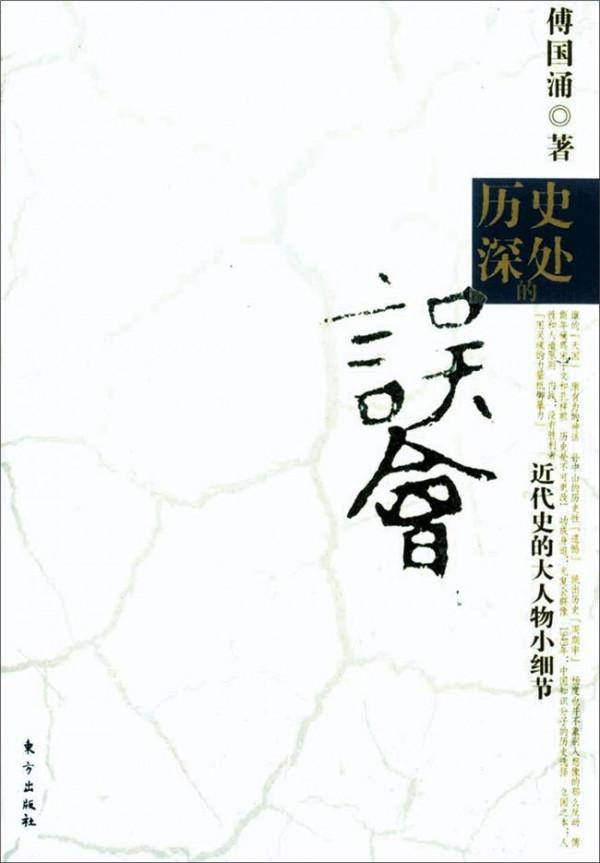傅国涌民国教育 傅国涌:民国教育的花开花落(下)
北大经济学教授厉以宁,每次在给新生上第一堂课时他都会问一个问题:你到北大来是要学什么?很多人说,我是来学知识的,他说不对;也有人说是来学方法的,他也说不对。没有学生能答对,他就说:你是来开阔视野的。教育首先给学生提供的是一个文明的视野,让他看到世界有多大,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让他看到古往今来人类走过了一条怎么样的道路,让他打开视野,认识这个世界、这个时代,这才是首要的目标,然后才是知识和方法。
我有一个朋友喜欢说:在谷歌时代,什么样的学问似乎都变得不太重要了。为什么?因为没有必要嘛,你在谷歌上一搜索关键词,一大串东西全出来了——你记那么多干嘛?那就叫现成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你要有一个“判断”。
我觉得他说的“判断”这个词非常好,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你有能力对这些知识作出判断,因为网上的东西不一定都对的,有很多都是错误的,你具备辨别真伪的能力,那才是属于你的真本事。由此,我想到的是,今天我们缺的不是知识,因为知识获得的途径真是太多太多了——过去,我们说一个人要是不经过学校教育,就是“睁眼瞎”,但在现在,获得知识的途径已经非常丰富了,“获取”已经不再是困难的。
困难的是,你怎么去看待这些知识,怎么去判断这些知识,并形成自己独立的看法。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判断我们教育的功能,就能看到它的局限在哪里。当教育把老师和学生的时间、空间挤占得太满之后,留下给他们装备自己、真正提升自己的余地就没有了。
《圣经》中说,耶稣来到世上要干什么?干三件事: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被压制的得自由。我把这三句话用在教育上,怎么解释呢?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对自己本来都是不了解的——所以,古希腊有句名言:认识你自己!
教育所说的把人当成人,首先也是让人认识自己: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往哪里去。认识你自己,就是让“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就是让你看见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被压制的得自由”,指的是你真正认识了这个世界,你就会获得精神上的自由,你就会觉得,自己是活得有自信的、有尊严的。
我觉得在这一问题上,民国时代的学校基本上都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他们有大把的时间让老师和学生自己去想这个问题,自己去读书,自己去玩想玩的项目。学校里有很多不同的社团,有很多让学生去从事文化或其他活动的空间,所以接下来我想说的关键词是:兴趣、健康、能力。
如果一所学校能在教育的过程中让学生发现自己兴趣之所在,真正让他们知道兴趣在哪里,也让老师有机会把自己的兴趣转化成动力,这样的教育才有可能变得丰富、健康,也才能把一个人的潜力挖掘出来——因为每个人的潜能都是不同的,也就是上帝所赋予每个人的恩赐是不同的,每个人恩赐的方向一定都不相同。
在某些领域做出重大成就的人后来回忆自己的中小学时,不约而同地讲到,自己在中学或小学时代,在某个阶段遇到某个老师,这个老师激发出他某个方面的潜能,然后他在那个阶段就奠定了今后发展的方向。
中科院院士施雅风是中国冰川学的开创者,他的启蒙是在初中完成的,他当时就决定要考大学的地理学专业,后来考取了浙江大学。中国最著名的植物学家之一吴征镒,在扬州中学读书时就发现自己的天分在这一方面,后来就不断在这个方面追求。
科学史家、《爱因斯坦文集》编译者许良英,之所以后来会去研究爱因斯坦,也起源于少年时代的一个偶然机会,他读到爱因斯坦的书《我的世界观》,一心想成为爱因斯坦那样的物理学家。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我深感,在学校阶段,如果有充分的机会,让学生发现自己的兴趣、能力在哪一个方向,并且能健康地发扬光大,这就是真教育。
我喜欢讲两个只读过小学的人,一个成了作曲家,一个成了出版家。一个叫周大风,在浙江读的小学,学生时代偏爱音乐,天分得到发掘,初中失学,踏上社会,最后成了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一个叫范用,三联书店的总编辑,他只上过镇江的穆源小学,他非常怀念这所小学,甚至为它写过一本书,我还没有看过第二个人为一所母校——小学——去写一本书的。
他的小学给他留下这么深的印象,以至可以写成一本回忆录,他在书中回忆了整个小学时代的点点滴滴、方方面面。
小学毕业,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他到出版社做学徒。如果要讲知识的话,他根本比不上同时代的其他人,因为别人还可以继续受教育啊,而他没有机会了,但是我觉得他在小学中得到的东西已足够奠定他今后成为一个优秀的出版人。
他特别讲到的是,他在小学做志愿者、做义工——为学校管理图书馆。当时,这件工作是学生们轮流去做的,而他是小组长,并做得很好。他把图书馆的书基本上都看了一遍,其中有一套书,叫《小学生文库》,里面什么门类的书都有,还有大量的杂志,他都浏览过。
这是他小学时代完成的一件事。第二件事是他在学校办了好几个不同的壁报,实际上就是他自己写写画画抄抄的东西,这就奠定了他后来成为出版家的基础。他还参加学校组织的剧团,到街头去演出过,宣传抗日。这些小学时代的经历,成为他今后很多发展的奠基石。
大家都很熟悉的金庸,香港《明报》创始人,当然也是武侠小说的一代大家。但是他人生的根基不是由大学决定的,而是更多地取决于小学和中学。他在小学时遇到一个语文老师(也是班主任),叫陈未冬,那个老师发现他的作文特别好,五年级时,班级创办了班刊《喔喔啼》,老师就让他做主编,还推荐他的一篇作文在当时杭州一家报纸发表。
中学时代,他给报纸投稿,发表了三篇作文。这三篇作文我都在档案馆里找出来了,写得非常好。如果我们将他后来的武侠小说和他中小学时的作文联系到一起,也许我们会蓦然发现,每个人的人生基础在他的少年时代都已经奠定了。少年时代的那条线索是直接抛向你的未来的,这是一条神秘的线索。
我在和年轻人说“读书”这件事的时候,常常会想到这样一番话:你说读这本书有什么用,尤其是这本书考试不考的,读了干什么?你读那本书,也不考的,有什么用?是的,没有用。但是,也许在十年后,二十年后,甚至三四十年后,你少年时代读过的某一本书、某一篇文章,会在你的脑子中跳出来。
或者,在你做某一件事的时候,它会突然跳出来,那是什么?那就是一条神秘的线索。这条神秘的线索就像天罗地网一样埋在你生命的深处,待某一天它就会被拎出来。这条线索就是你的人生,就是你的精神世界。
如果没有你早年的阅读,当你在以后的人生中想要做某一件事的时候,你没有线索可以被拎,因为你的生命中没有布下像天罗地网一样的线索。那些线索在当时布下的时候,是无用的、是无意的。我们今天所讲的教育,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过于追求“有用”,也太过于追求“有意”“刻意”。
我们把这些看得太重了——而对“无用”非常排斥,对“无意”“不经意”看得很轻。等到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拎起来的线索,因为你的生命中本来就没有埋下什么伏笔。
我经常想到,人成年以后,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不是课堂里所学东西的竞争,不是作业、考试里那些东西的竞争,因为这些东西大家都差不多。人与人的真正竞争是在不一样的地方展开的,我看的书你没看过,那我就跟你不一样,最多的竞争是在原先“无用”的地方、“无意”的地方。
如果我们观察每个时代在不同领域有造就的人,你从表面怎么都看不懂他。我喜欢用阅读这个角度去观察,八九不离十就能看懂很多人。比如,我认识一些在各自领域有重要建树的老先生,比如著名律师张思之,他为什么成为律师界的泰山北斗?你可以说他专业好,他有道义勇气,都对,但是你这样说等于什么都没有解释。
法律学得好的人有,辩护辩得好的人也有,有勇气的人也不仅是他。我破译他的精神密码,之所以区别于同时代甚至比他晚一辈的律师,最大的不同在于他身上有一些别人不具备的东西——我用一个词概括:人文性。
专业性、公共性别人同样有,人文性别人可能也有,但绝没有他这么强烈。他是1927年出生的人,六七年前,我在编《过去的中学》时,请他写一篇回忆文章。
他的回忆让我大为惊讶,他印象最深的竟然是一堂课,他回忆在抗战时的重庆读高中,有一位高中老师姓傅,本是东北大学的教授,因为战争的缘故流亡到那里做了中学老师。他记得那是一堂讲李清照词《声声慢》的课,老师仅就其中“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叠词就讲了一节课!
少年的他没有想到汉语竟然有这样打动人心的力量,竟然有这样的穿透力,这堂高一时代的课直到老年他还记得,并将留在他心中一辈子。
他的专业和古典文学没有关系,但是2005年夏天我去北京看他,他在一家酒店的大堂等我,当时带了一本书在看,我一看桌子上的封面,就突然明白了他一生区别于其他同行的奥秘——那本书是《元曲选》。我明白了高中那堂课给了他一辈子,给的不是专业,而是精神的滋养,他一辈子都能在这里面得到滋润。
所以,他一方面可以站在法庭上辩论,另一方面他在辩词中一辈子都在追求汉语的美感。你可以说一个律师与元曲、宋词有什么关系,但是,正是这些才是留在他生命里一辈子的东西。
我特别赞成张文质先生搞的跨年诗歌朗诵会,因为在一个人的成长阶段,这种美育的东西,才更容易成为他生命内在的东西,从中可能转化出一生的资源。其实,教育说穿了就是要把人当人,但是把人当人是需要资源的,这不是一句空话。
你不知道李白,不知道曹雪芹,不知道屈原、杜甫,不知道鲁迅、胡适,你就没有办法让自己在文化上变成一个中国人——你只能是物质上的中国人。就像我们到了美国,我们就不能成为一个美国人,因为我们不是在惠特曼的诗歌、海明威的小说哺育下成长的,我们要进入他的文化,进不去啊。
有些华人在美国生活几十年,交往的圈子基本上还是华人,因为他跟美国人是两个文化系统。我曾经想,一个人在这个时代生活,他在精神上需要两个证件,一个是中国文化的身份证——这是指你身上中国文化的元素,另一个就是全球普世文化的护照,你要知道自古希腊文明以来整个文明的脉络。
你有了这两个证件才可以说基本上是一个现代人,大致上可以跟这个时代构成一种对应的关系。如果这些都没有,那你虽然活在这个时代,但实际上和这个时代是很远的,你只能活在自己的一个很小的世界。
从这些方面来看,我觉得民国的教育是成功的。一个时代不能因为它是乱世,就说它是失败的。诸子百家不是产生在秦始皇大一统的中国,而是产生在春秋战国时代。民国,是中国的乱世,但是在教育上走出了一条真正融合中西的道路,将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本土化,让我们在这块土地上不仅享受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最优秀的文化,同时能享受来自全球的最优质资源,这就是民国时代曾经做到的。
最后一组关键词是:个性、气质、精神。
这些词,我们看上去都是虚词,是这个时代不喜欢的词,但恰恰是这些词才是“把人当人”的根基。人区别于其他人的,不就是这些东西吗?如果在这些方面没有展开,在教育中没有能塑造人的个性,也不能让人的气质得到展现,更不能培养他们健全的精神,这种教育基本上就是失败的。
今天,我们小学阶段的教育是有可能做得更好的,中学可能难度更大。毕竟小学还是能给小学生做一些“无用的”事情——无用的事情,恰恰是最有用的;那些有用的,恰恰是没用的。在这方面我有一些个人的体验。我觉得,当我成人以后,在学生时所学过的东西,基本上都用不着,可以说90%都没有用上。
但是自小学时代以来,我读的那些课外书基本上都有用。这个“有用”不是说直接拿来的那个“用”,而是它总在你写某一本书,或某一篇文章的时候,那条神秘的线索会被激活,几十年前的东西,就被扯出来了,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东西。
这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却又真实存在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也难用一种物质的、可以量化的方式去表达,就好像《圣经》里的一句话:“你必点燃我的灯。”
今年有本书,大陆出的是删节版,没有香港的全版精彩,书名叫《燃灯者》,是讲北京大学周辅成先生的。“你必点燃我的灯”,教育就是要点燃学生那盏灯。你做了几十年的教师,哪怕有一个学生的灯被你点燃,你也是可以骄傲的,何况,你有可能点燃更多人的灯。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者其实就是“燃灯者”,点燃那盏灯的人,你的伟大的工作就是擦亮火柴,因为讲台下面那些眼睛就是那些还没有被点亮的灯。
诚如爱因斯坦所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专业教育可以让人成为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和谐、发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