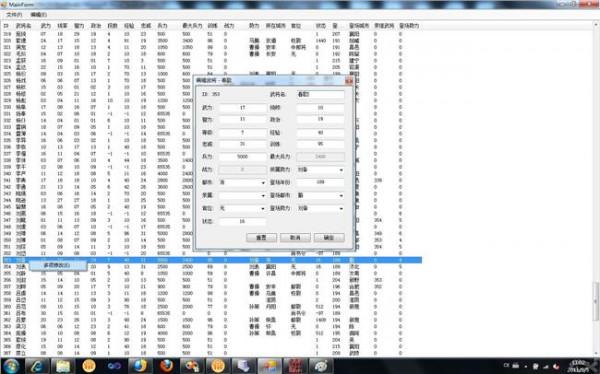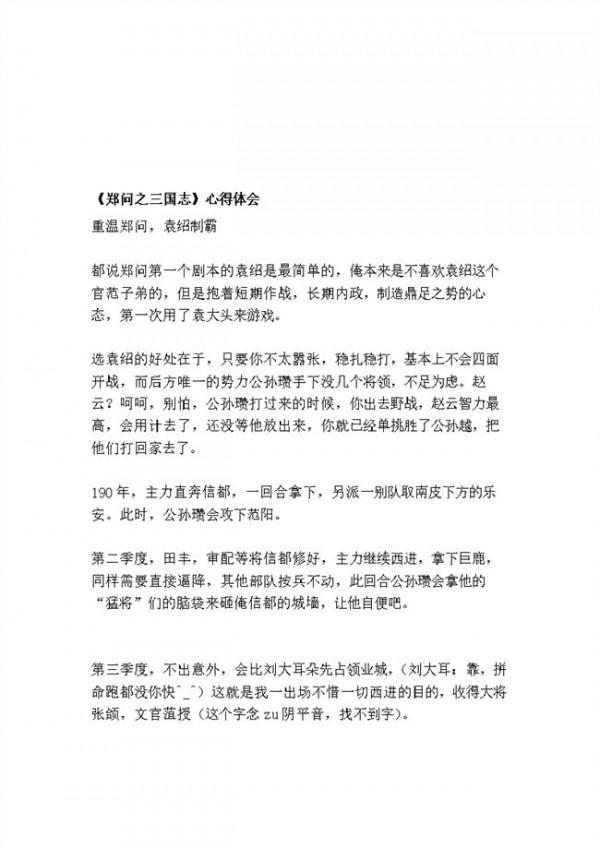道丑郑问 潘道正 李进超:论康德的“丑的问题”(上)
众所周知,在《判断力批判》中,涉及到“丑”,康德惜墨如金,只用了一小段百十来字。康德在“审美判断力批判”的名下,列有“美的分析”和“崇高的分析”,但为什么没有“丑的分析”?康德的美学理论能否给出“纯粹的丑的判断”?诸如此类问题从上世纪末开始,吸引了大批学者的兴趣,在欧美学术界引发了跨世纪的大讨论,保罗·盖耶尔(Paul Guyer)、亨利·艾利森(Henry Allison)等当今最知名的康德研究学者都积极参与其中。
这场大讨论尚未结束,本文试图以这些讨论为基础,通过引入审丑理论,深入分析“美”“崇高”和“丑”之间的关系,就康德的“丑的问题”作出新的解答。
问题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年轻的康德研究学者盖瑞特·汤姆森(Garrett Thomson)在《美学和艺术批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极具挑战性的文章《康德的丑的问题》。汤姆森在文中指出,自然界存在着不可否认的丑,但康德的美学“排斥了这种丑”,“螃蟹的脸、母牛的脸、鲶鱼、猴子屁股:只要想象下这些东西就知道自然界有丑。
”汤姆森开篇就写道,“康德的审美理论排斥了这种丑,原因在于审美理论的角色是联结他的理论哲学和道德哲学。
如果这种联结是成功的,那么就不可能真正作出‘X是丑’这种形式的判断。如果纯粹自然丑存在,那么《判断力批判》联结理论王国和实践王国的努力就失败了”(Thomson107)。汤姆森立论的依据是康德的道德哲学。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即美象征着道德上的善。汤姆森由此推导出“丑象征着道德上的恶”,丑因而“排斥了现象化的德性”,“丑不仅排斥了德性,而且丑存在的可能性也否定了德性先在的、无条件的强制性”(Thomson112)。
汤姆森以“丑的问题”为突破口,试图证明康德美学理论存在致命的结构性矛盾。汤姆森激进的观点引来了保罗·盖耶尔强有力的回应。盖耶尔直接指出汤姆森“没能认识到康德在审美论的和目的论的反省判断之间的区分,并导致了对康德在自然美的现象和审美判断之间以及自然美的现象和德性之间建立起的精妙关系及其复杂性的误解”(Guyer312)。
按照盖耶尔的说法,作为审美判断的美、丑判断跟属于目的论系统的道德判断根本就没有关系,“对任何个体对象物的审美判断,也即是美、丑判断,跟那种是或形成某种可能具有道德意义的目的论系统的判断没有任何关系;因而,任何个体对象物的丑,都不会成为其被感知为一个目的论系统或系统之一部分的障碍——不论有怎样的道德或科学的意义将要附加其上”(Guyer318)。
盖耶尔由此否定了汤姆森的论证。
差不多同一时期,德国哲学家莱因哈特·布兰特(Reinhard Brandt)提出了同汤姆森类似的观点。布兰特同样认为,按照康德的美学理论,鉴赏的真正基础是道德,但在他看来,康德显然认识到了“X不是美的”或“X是丑的”这种判断的现实性,只不过不予承认,因为对丑的判断没有可被普遍传达性——按照康德的理论,只有纯粹鉴赏判断,只有自由和谐的精神状态才具有普遍可传达性。
布兰特进而为康德辩护说,源于趣味和德性之间的关系,康德有很好的理由不承认否定鉴赏判断。
按照布兰特的观点,对于康德来说,自然的美为道德上自然的合目的性提供了标示,“所有的事物(或至少是自然中的每一样事物)都必定是美的,而无法欣赏自然中某些事物的美被归因于鉴赏力的缺乏。
”为支持这种解读,布兰特引证了康德于1754-1755年间发表的一份人类学演讲稿的注释:“自然能生长出某种象人工产品那样丑的东西吗?不。如果我们对自然的目的具备更广的知识,如果我们熟悉其所有成员的应用,那么按照自然的规则生长出来的东西都不能是丑的,而只能是真正美的,因为在自然的进程中无物不美。
丑只是相对于其他事物而言。如果我们注意到规则性,那么甚至丑的事物也是有规则的”(Allison186)。
亨利·艾利森在他研究康德美学的经典著作《康德的趣味理论》(Kant’s Theory of Taste,2001)对布兰特的观点进行了评论。艾利森指出,布兰特仅凭一条注释就说它是康德的核心论点,这不客观。
首先,从康德的其他文本中同样可以找到同样重要的相反观点;其次,在这段引文及其他类似文本中,康德关注的显然是目的论问题或客观合目的性,而不是鉴赏,后者是主观合目的性问题,“因其客观(道德)感知的合目的性乃至合规则性,就宣称无物不美,将会摧毁康德鉴赏理论的全部基础。
因此,如果康德的鉴赏理论得到拯救,那么通过纯粹鉴赏判断进行审美的评价,就必定会显示它不可能得出无物不美的观点”(Allison186)。可以看出,艾利森对布兰特的回应同盖耶尔对汤姆森的回应异曲同工,关键是要区别对待审美论和目的论,拒绝把审美判断和道德判断混为一团。
1998年,华盛顿州立大学哲学教授大卫·史尔避开审美判断和道德判断之间的纠缠,针对《判断力批判》第一部分中论证的前后不一致提出了一个纯美学的问题:“康德《判断力批判》第一部分(‘美的分析’)研究的是关于美的鉴赏判断——或者,如康德通常所说的,就是鉴赏判断。
既然似乎明显存在着肯定和否定两种判断,那么人们自然期待着在第一部分找到对这两种判断的研究。[……]非常奇怪的是,在这些框架性的标示之间,康德关注的只是肯定的判断。
尽管没有哲学家比康德更在意细节,我们发现他在介绍了肯定和否定趣味判断之后,完全忽略了后者。这儿,康德为什么如此反康德式的?”(Shier412)。史尔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既然和谐的自由的游戏总是令人愉悦的,而所有鉴赏判断又都伴随着和谐的自由的游戏,那么结果只能是每一鉴赏判断必定伴随着主体的愉悦的情感。
但是,按照定义,任何鉴赏判断,如果主体情感是愉悦的,那么就都是肯定鉴赏判断。
于是,在康德的美学体系中,与事实明显相悖,关于自由美的否定鉴赏判断根本不可能”(Shier412)。史尔的问题及推论紧扣文本,以康德“想象力和知解力之间自由和谐的游戏”这一核心论点为基础,非常具有代表性,成了后来相关讨论的焦点。
德国伍帕尔塔大学数学教授、哲学博士克里斯提安·文哲(Christian Wenzel)首先在《英国美学杂志》上撰文《康德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是丑的吗?》反驳史尔的观点。文哲首先分析了康德对“否定”概念的看法。
康德早年在《把负量数概念引进哲学的尝试》一文中,提出了包括美/丑在内的很多对立的概念,并认为一方并非只是另一方简单的否定,不快也有其肯定的基础,且同愉快的一样多,可以称之为“否定的愉快”,“厌烦可称之为否定的欲求,憎恨可称之为否定的爱,丑可称之为否定的美,责备可称之为否定的称赞”(Theoretical Philosophy,1755-1770182)。
以此为理论基础,文哲区分了两种和谐:“认知和谐”和“感性和谐”,前者是“认知判断下诸机能的和谐”,后者是“肯定的鉴赏判断下的和谐”,同时文哲把“否定鉴赏判断下诸机能的不和谐”称之为“感性的不和谐”,并认为感性的不和谐同感性的和谐没有差别,因为“感性和谐和感性不和谐总体上都和认知关联,其方式足够相似,基于同等的基础宣称肯定和否定鉴赏判断的普遍有效性”(Wenzel417)。
文哲据此指出,史尔的错误在于“把两者等同起来”。“在自由和谐的游戏中,”文哲总结道,“考虑到认知的可能性(头脑中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我们只是(快乐地)反省对象物的形式,发现它适合于总体上的认知。
同样,我们为什么不能不快地反省并发现客体形式不适合于认知?正是这种感性反省——不论是和谐还是不和谐的自由的游戏——决定了普遍可传达性,因为它是指向总体认知的反省”(Wenzel417)。
艾利森对文哲的观点持充分肯定态度。他认为《把负量数概念引进哲学的尝试》非常重要,并指出这篇论文的中心主题就是把丑定义为一种“否定的美”。
艾利森还引证了康德的一份关于形而上学的演讲稿中“非—美”的提法。艾利森基于文本得出的结论是:“康德为否定鉴赏判断提供了理论基础”(Allison54)。
与此同时,盖耶尔则认为诸机能不和谐的自由游戏是不可能的,按照康德的美学理论的确“不可能作出纯粹丑的判断”,盖耶尔写道:“丑的判断根本就不是纯粹反省的感性判断,而只是感官的或实践的判断——它们涉及的是我们对事物不愉快的情感的表达,是生理的或心理的不适[恶心],或者按照我们谨小慎微的或道德的实践理性为坏的或邪恶的东西”(Guyer151)。
加利福尼亚大学哲学教授汉娜·金斯伯格(Hannah Ginsborg)完全赞同盖耶尔的看法:“我的观点是,对康德来说,根本不存在纯粹丑判断这回事。我们在《判断力批判》中能够发现的所有丑的例子都是康德所谓的‘有害的事物’”(Ginsborg177)。
2008年,正在剑桥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的肖恩·麦坎纳(Sean McConnell)在《英国美学杂志》上发表了长文《康德可能会怎样解释丑?》。麦坎纳认为史尔的问题切中要害,但对文哲的反驳不屑一顾,“诸机能不和谐的自由的游戏这个诱人的概念其实毫无意义”(McConnell214)。
同时,麦坎纳受明尼苏达州立大学艺术哲学教授西奥多·格拉西克(Theodore Gracyk)的启发,试图推演出康德关于丑的判断。
格拉西克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试图为康德辩护,他诉诸《纯粹理性批判》中客体和主体时间—秩序的对照关系,认为在一个既定的场合,于主体时间—秩序中,从观看者的角度来说,如果没能同客体实现充分的统一,客体的美就不能被欣赏或者说只能得到最低程度的欣赏,这时客体就可以说是丑的,“‘丑’的客体就是经此努力后仍只是得到最低限度的统一性的那些对象,因而同其他再现物相比较也只有最低限度的愉悦”(Gracyk55)。
格拉西克没有对自己的观点进行系统的论证,但他关于主、客体统一的观念以及引入时间维度的方法极大地启发了麦康纳。按照麦康纳的观点,象征着纯粹鉴赏判断的主观情感也即愉快或不愉快的情感并非像史尔所说的截然二分,而是一个“愉悦情感的连续统一体”,按照一定的“比率”分化成美、丑两端,“一个完全统一化的客体,一个展现出非规定性、起统一化作用的规则完全实现了的客体,在连续统一体中引向美的一端,而任何减损都引向丑的一端”(McConnell220)。
然而,问题在于康德的纯粹鉴赏判断是一个超越时间的先验规则,这诚如艾利森在评价格拉西克的观点时所指出的,“不幸的是,这种把第一批判在时间-秩序之间的区分强加给第三批判的鉴赏判断并不十分令人信服,特别是,既然鉴赏判断(音乐或许是个例外)似乎跟时间-秩序没什么关系”(Allison185)。
以上是对“康德的‘丑的问题’”大讨论中一些主要观点的梳理,可以看出,在大多数情况,并不存在唯一的正确答案,但这些讨论无疑极大地丰富了之前很少有人关注的康德美学中的丑的理论,但康德的审丑思想仍未被触及,而要想给予康德的“丑的问题”更好的解答,就必须进一步区分丑与审丑,深入诠释康德的审丑理论。
康德的审丑思想
由于“审美判断”总是合目的、令人愉快的,可以说是对美的欣赏(appreciation of beauty)。那么,如何表示“丑的欣赏”(appreciation of ugliness)?首先,丑的客体当然可以被欣赏,大量关于丑的艺术①足以证明;其次,很显然,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同“审美”对应的词语,这个词语就是“审丑”。
审丑就是对丑的欣赏,这儿需要把它同“丑的判断”(judgment of ugliness)区别开来。
对丑的判断是否定判断,产生的是“不愉快”的情感,因而不论就主观还是客观来说,客体对象都不可能是“合目的性的形式”,就此而言盖耶尔无疑是对的,即按照康德的美学理论,不存在“纯粹的丑的判断”。但审丑判断是对丑的欣赏,最终唤起的是愉快的情感,因而完全可以存在“纯粹的审丑判断”。我们将会发现,康德所分析的正是“审丑判断”而非“丑的判断”。
《判断力批判》中,关于丑,就说了一小段话,现照录如下:“美的艺术的优点恰好表现在,它美丽地描写那些在自然界将会是丑的或讨厌的事物。复仇女神,疾病,兵燹等等作为祸害都能够描述得很美,甚至被表现在油画中;只有一种丑不能依自然那样被表现出来而不摧毁一切审美愉悦、因而摧毁艺术美的:这就是那些令人恶心的东西。
因为在这种建立在纯粹想象之上的特殊的感觉中,对象仿佛被表现为好像在强迫人去品尝它,而我们却又在用强力努力抗拒着它,于是这对象的艺术表象与这对象本身的自然在我们的感觉中就不再区别,这样,那个表象就不可能被认为是美的了。
同样,雕刻艺术由于在其作品上艺术和自然几乎被混同了,所以就从自己的形象中排除了对那些丑的对象的直接表现,为此也就容许通过某种看起来令人喜欢的隐喻或征象(Attributes),来表现诸如死亡(以一个美丽的精灵)和战争精神(在玛尔斯身上),这种表现是间接的,需要借助理性的解释,不只是单纯的审美判断”(康德156)。
②这段话无疑是《判断力批判》中最富争议的文字之一,包含了丰富的审丑话语。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康德似乎把丑分成了两类:一类可以直接用艺术加以表现,如复仇女神、疾病、兵燹;另一类只能被间接表现,如死亡、战争精神,因为它们引起“嫌恶”的感觉,会摧毁艺术美。但是这种区分非常勉强,因为前一类同样会引起嫌恶的情感,比如“复仇女神”,我们不妨看看奥维德笔下的“复仇女神”提斯丰(Tisiphone)形象:“紧握鲜血浸泡的火把,穿上滴血的红袍,蠕动的毒蛇腰间环绕。
起身离去,悲伤为伴,惊慌、恐惧、疯狂扭曲了脸面。
[……]伸出双臂,毒蛇缠绕;甩动蛇发,嘶嘶有声。毒蛇有些盘曲肩上,有些爬行在胸脯,发出尖利杂音,吐着鲜血,晃动着舌信”(Ovid213)。此“复仇女神”之丑恶,丝毫不逊古希腊那看一眼就能让人变成石头、堪称丑恶之最的梅杜萨。
如果按照康德的假设方式,“以自然那样被表现出来”,艺术的美肯定同样会荡然无存。事实上,应该说所有的丑都必然是令人嫌恶的,或者说嫌恶本就是丑题中应有之义。按照休谟的定义,如果说美的本质是让人快乐,那么丑的本质就是“产生不快”,“美是一些部分的那样一个秩序和结构,它们由于我们天性的原始组织、或是由于习惯、或是由于爱好、适于使灵魂发生快乐和满意。
这就是美的特征,并构成美与丑的全部差异,丑的自然倾向乃是产生不快。因此,快乐和痛苦不但是美和丑的必然伴随物,而且还构成它们的本质”(休谟334)。
当然,这段话的主旨显然并不在定义丑。康德虽然运用了“讨厌的事物”“祸害”“令人恶心的东西”等诸如此类的话语,但也只是对丑所引起的否定情感的描述,并没有对丑作任何定义,换句话说,康德没有作“丑的判断”。相反,康德所讨论的是艺术如何表现丑,探讨的是“纯粹想象之上的特殊感觉”,是“艺术表象”而非对象物本身,而艺术化地,或用康德的话说,“美丽地”表现丑的过程正是典型的审丑。
康德显然认为,两类丑都可以得到艺术化的表现:一类直接就可以“描述的很美”;另一类虽然令人恶心却可以“通过隐喻或征象”间接地表现出来。
首先,审丑需要“借助理性的解释”。按照康德的观点,审丑的实现需要“通过某种看起来令人喜欢的隐喻或征象”。什么是“隐喻或征象”?《判断力批判》中,“隐喻”一词就用了这么一次,并无特殊的说明,但“征象”一词却很重要,至少有两种含义:一是作为连词用,意思是“把……归于……”;另一是作为名词用,指的是客体的“特性”“特征”。
在康德的用法中,作为连词,并无新意,但作为名词却被赋予了特殊的内涵,是典型的康德式的范畴。
在随后的第49章中,康德就对“征象”进行了深入的诠释。按照康德的解释,“征象”是某种“形式”,“那些形式并不能构成一个既定概念本身的表现,而只是——作为想象力附加的表象——表达同这概念相关联着的意涵以及它同其他概念的关系,我们把这些形式称之为一个客体的(审美的)征象,而这个客体的概念,作为理性理念,是不可能得到恰当的表现的。
所以,朱庇特那利爪握着闪电的神鹰就是强大的天空之王的征象,而孔雀则是仪态万方的天后的征象。
它们并不像那些逻辑的征象那样,再现出在我们有关创造的崇高和壮伟的概念中所包含的东西,而是再现某种别的东西,这些东西促成想象力把自身扩展到大量相关联着的表象,让人们思考更多,远非一个用词语规定的概念所能表达。
它们生成审美理念[感性理念],它取代逻辑的表现而服务于那个理性理念,尽管实际上只是为了鼓动心灵——通过为它展现那些相关联的表象的一个看不到边的领域的盛景”(康德159-60)。
征象可分为两种:审美征象(aesthetic attributes)和逻辑征象(logical attributes)。审美征象是非常特殊的“表象”,一方面,它只是“附加的表象”,并非纯粹的“想象力的表象”,也即是说它不是审美理念;另一方面,它显然也不是理性理念,因为它并不能表现一个“既定概念”,可以说它是介于审美理念和理性理念之间的东西,或者说是两者的“桥梁”。
审美征象的最终目的是生成“审美理念”,并服务于“理性理念”,但在这过程中,它首先需要“表达同这概念相关联着的意涵以及它同其他概念的关系”,也即是说需要借助理性理念来生成审美理念。
由此可见,审美征象的重要功能就是联结“理性理念”(结合着“既定概念”),实现“理性的解释”。这同审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审美判断“不是建立在任何有关对象的现成的概念之上,也不带来任何对象概念”(康德25)。
其次,审丑主要发生在判断者的内心中,具有主观性。按照康德的观点,审丑判断“基于纯粹的想象”,主要发生在“我们的感觉中”,而“那个表象”只是“被认为”不可能是美的,也即是说艺术表象的美、丑与否取决于主观的判断。
康德在描述艺术化表现丑时说:“这对象的艺术表象与这对象本身的自然在我们的感觉中就不再区别,这样,那个表象就不可能被认为是美的了”(康德156)。这儿涉及到主体(“我们的感觉”)、客体(“对象本身的自然”)和表象(“对象的艺术表象”)之间复杂的“三角”关系,内含着非常关键的“心理距离”(psychological distance)问题。
按照瑞士心理学家布洛的理论,“距离体现在我们的自我同它的情感之间,后面这个术语用的是其最宽泛的意义,即能影响我们肉体或精神存在的任何事物,比如感觉、知觉、情绪状态或意念。
通常——虽然并非总是——也就等于说体现在我们的自我同作为情感根源或介质的客观对象物之间”(Bullough94)。
据此,康德所说的对象的“强迫”、我们的“抗拒”,其实都可以用主体同对象物之间“心理距离”的变化来解释——当表象和客体之间“不再区别”,就意味着两者之间距离的消逝,意味着主体得直面客体,这时表象就不可能被认为是美的;而在借助“隐喻或征象”的情况下,实际上拉开了主体同客体之间的距离,表象就可能被认为是美的。
但是不管情感如何变化,判断主要发生在内心中,这同审美判断也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审美判断的根据只能是对象的“合目的性的形式”(康德72)。
第三,审丑判断“不只是单纯的审美判断”。审丑判断可以说是“复合判断”,至少包括“丑的判断”和“审美判断”两个部分。首先,主体直面丑的对象物,会产生厌恶、不快的情感,客体成了反目的性的对象,形成的是否定的判断,也即“丑的判断”,但通过“隐喻或征象”,“借助理性的解释”,想象力被极大地激发,生成了审美理念,从而客观上拉开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心理距离,或者说把主体指向客体的感知转向了艺术表象,主体由此也摆脱了客体的“逼迫”,于是不快感被克服,并实现了反转,代之而起的则是愉快的情感,此时,表象或者作为表象现实化的艺术就表现为合目的性的形式,审美判断由此得以实现。
因此,就最终愉快情感的实现来说,审丑判断也可说是审美判断,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康德可以在“纯粹审美判断的演绎”的名称下讨论审丑问题。相反,“丑的判断”在“审美判断力批判”中则不可能有任何位置。
当我们从康德有限的文字中发掘出丰富的审丑理论后,就会发现康德审丑理论的三个特征都能在他的“崇高的分析”中找到,换句话说,审丑同崇高的判断有着高度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