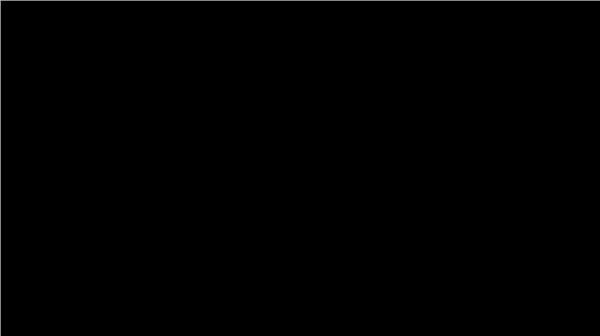乌仁娜演唱会 乌仁娜:我在哪儿开始唱歌 哪儿就是我的家
乌仁娜出生于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的牧民家族,如今她已经是亚洲最杰出的女声之一。她在世界各地都用她的母语蒙语演唱,只要她的歌声响起,观众能立刻感受她的情感,也很容易就理解了她传递的信息。那一刻,只感到任何语言都是累赘。她说,她心中的旋律,全部都是她从小就唱的,是大自然和父母送给她的。点开上面的视频,听听她的天籁之音,她对音乐的爱,以及想分享给“宇宙的人类”的歌声……
唱给宇宙听的歌
撰文
沈沿
乌仁娜汉语不太流利,但她语言天赋极佳。1989年,21岁的乌仁娜从内蒙古坐火车来上海备考上海音乐学院,当时她一句中文都不会,都无法问路,拿了张皱巴巴的电报纸问路;后来听说考试是汉语,她一下子又傻了,只能突击学习。
而现在,坐在眼前的乌仁娜,因为长期旅居欧洲,又和国际音乐人频繁合作,她能说英语、德语,因为在上海读书生活过,她还能冒出两句上海话,唯独汉语不太使用,她经常想不起该如何表达,在脑中拼命搜索恰当的汉语词汇。
不过,对于乌仁娜这样的音乐人、歌者来说,语言本不重要。于是,音乐从某种程度上看,就仿佛是“天籁”——一种与上天沟通的语言。在圣经中,原本人们都说同一种语言,并能够与上帝沟通,而巴别塔建成后,人们开始说不同的语言,彼此也难以沟通。
一个切身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我在采访乌仁娜时问她:“你现在的音乐,和你早期的音乐相比,有什么变化?”乌仁娜告诉我,除了和国外音乐人合作之外,她现在的歌是唱给宇宙听的,她特意用英文了说了“ universe”。我不太明白怎样的音乐是献给宇宙的,库布里克在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在宇宙中播放《蓝色多瑙河》,据说中国卫星会在宇宙中播放《东方红》,但我想这应该不是献给宇宙的歌。
而当我坐在“乌仁娜与SSO室内乐团“音乐会中,我开始明白了乌仁娜的话。特别是乌仁那演唱《Beleg(礼物)》时,临近尾声,乌仁娜一句句吟唱,听上去蒙语歌词很相似,只是在她的歌声中,一句音调比一句更高,情感更强烈,某个瞬间,让我有种置身在祭祀现场的感觉。
此时的乌仁娜,就是在用歌唱和上天沟通,用灵魂对上天祝颂,她的一句句,一开始雄壮、浑厚,声调越变越高,声音也变得越来越薄,最后飘渺,仿佛用尽了最后一分气力,将整个生命都献给了上天。国外媒体称乌仁娜是“蒙古灵魂乐的祭祀”,乌仁娜自己也说过,“我用自己全部的能量和生命来阐释歌曲,每次演出过后,我都如同经历一次重生。”
我瞬间就明白了。乌仁娜最初唱的歌曲,多来自内蒙古她的民族中长年流传的曲子,就如她在采访中说的,她的家乡人人都是歌手,茶余饭后,大家围坐下来,倒上酒、递上乐器,就开始一个接着一个歌唱。她的姥姥对她影响至深,姥姥就是一个当地的好歌手,告诉了她许多流传许久的歌曲和故事。
《Ejin bogdiin hoyor jagal(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Sangjidorji(桑吉多吉)》《Jigder Nana(朱迪娜娜)》等等,都是如此,有的是关于爱情、有的是关于传说中一个美丽的姑娘或英雄,或者是骑马放牧。这些民谣带着古老的智慧、哲理,质朴而有趣。
乌仁娜演唱这些歌曲,基本就是张嘴就来,如果不是和SSO这样的乐团合作才需要排练,她基本是音乐响起就能唱,全凭感觉走,以一种即兴的演唱方式。她也不练声,她拒绝所谓正统的声乐训练,她曾在采访中说过:“我庆幸自己没有选择学习声乐,因为我亲眼看到,那么多来自不同民族的充满天赋的学生,那么多有特色的、宝贵的声音,经过四年的学习之后,他们除了使用的语言不一样,演唱都是同一种(方式)。
”事实上,乌仁娜这些歌唱的方式就来自于她的民族,而她那跨越四个8度的音域、对音乐的感受和丰富表现力等等,就是上天的馈赠。
上天的礼物,还包括她的创作能力。她的创作同样也是即兴的,她对我形容这种感受——音乐在身体里是就像泉水喷涌。她坐下来就能哼唱出新的旋律,她也不知道这些旋律是哪儿来的,但只要她开口,就可以一直唱下去。乌仁娜后来的专辑里,越来越多她自己的创作。
一开始是关于家人的,《姥姥与我》中,“姥姥怜我爱我,总背着我歌唱讲故事,听着听着,我很快就睡入甜甜的梦乡了”。也有《无私》,关于父母对她的教导:“生而为人是一种幸福,智慧、照顾与宽厚,是父母给我最有价值的宝藏,让我克服生命中种种艰难”。
而到《生命》这张专辑中,《摇篮》《九个海洋》《无私》《平和》《记忆》《律动》《生命》,光是这些歌曲的名字就能发现,乌仁娜的创作变得越来越宽广,她开始谈论生命、人类、自然等母题。这或许就是她所谓“献给宇宙”的意思。
这些年,乌仁娜先是定居德国,后来又搬去埃及和开罗,她也曾试图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生活,加上不停地在各国演出,近二十年来,她血液中游牧民族的基因从不曾稀释,她只是将蒙古草原扩大到了世界版图,用歌声在世界各地播下种子。
她很愿意聊她在世界各地生活的见闻,你能发现她一直在细微地、以她的方式来打量这个世界。她说她在埃及时,总是看到游客用手机拍各种风景,而不是用眼睛去看;她住在巴伐利亚时,家边上就是森林,朋友们来做客,一同去森林散步,她发现有些朋友即使在森林中也会忽略大自然的信息,那些鸟的鸣叫、风的声音等等。“我发现我们说话越来越多,唱歌越来越少,观察大自然也很少,听大自然更少。”
“我虽然走了世界上很多地方,大自然对于我来说,还是一个大自然,并不会有蒙古的大自然,德国大自然或是其他大自然之分。当然,我是蒙古人,我出生在蒙古,我的草原是我的根,蒙古是我血液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根。但是,最深的根在哪里?是大自然,大自然在哪里?大自然是大世界,宇宙是大自然。所以宇宙是我的家。”
乌仁娜以上这段话,恰好解释了“蒙古/世界”、“蒙语演唱/各国音乐人”合作,等等一系列问题,还有那个人们最常问她的问题:“你想不想家乡”,也同样可以获得解答,“我无论走到哪里,如果我开始唱歌,就是我的家,我在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