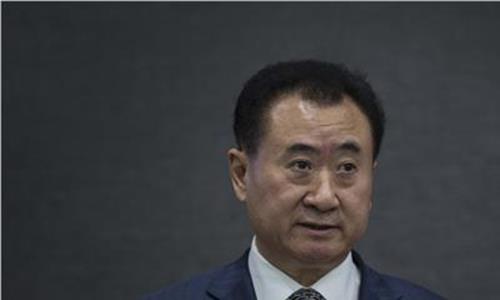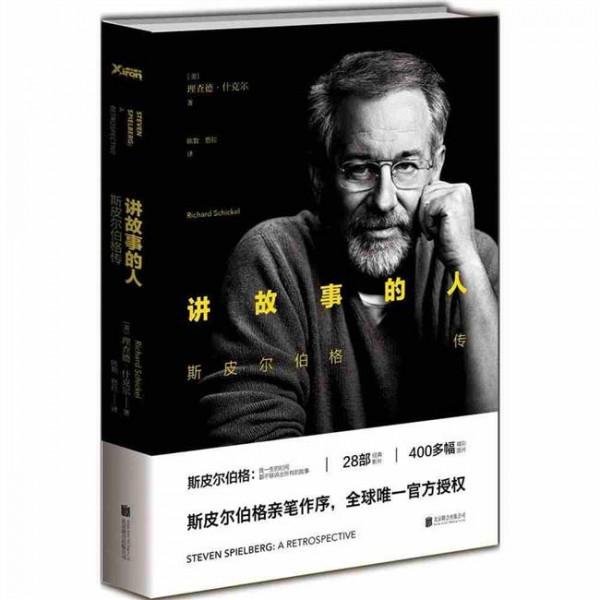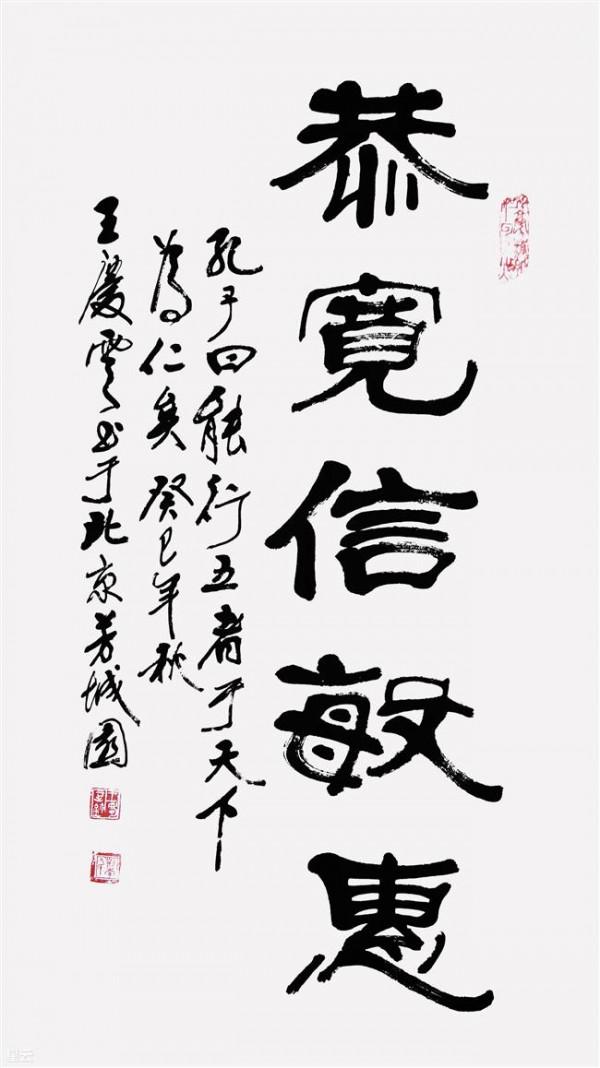瑜伽郭文斌 读郭文斌短篇小说集《瑜伽》之后
重申一种值得珍视的文学感觉——读郭文斌短篇小说集《瑜伽》之后
文/牛学智
《瑜伽》出版于2012年11月,这是2012年郭文斌在继随笔集《寻找安详》修订版(2012年6月)和散文集《守岁》(2012年6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之后的一个新成果,也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在2010年10月重点推出他的长篇小说《农历》之后的又一动作。一年之内,两家南方出版大社分别推出他的最新短篇小说精选集和最新散文精选集,可见作者的读者群在逐渐南扩。
拿起《瑜伽》,照样是先阅览目录,觉得眼熟的暂时放下,依着陌生并且格外吸引人的题目读下去,这是我这些年阅读熟悉作家作品时留下的一个不好的习惯。
这部短篇小说集共收短篇18篇,外加作者与姜广平的一个对话,有20万字左右。时间和习惯的原因,我依次读了《陪木子李到平凉》《今夜我只想你》《瑜伽》《我们心中的雪》《门》等,其他如《水随天去》《开花的牙》等早年读过,印象还在。
下面我要谈的一些想法,也可能与以上所读小说有紧密关系,也可能是由此而产生的联想。
我为什么一定要谨慎地划定一个基本范围呢?第一,自从郭文斌获鲁迅文学奖,包括《农历》入围茅盾文学奖第7名以来,我的眼力和耳力所及,郭文斌的小说创作,在批评界大致形成了这样一个特点:安详文化。承载这个特点的一批作品可能是《吉祥如意》《农历》《大年》《寻找安详》《〈弟子规〉到底说什么》等等。
这期间当然也有作者本人以"安详"、"祝福"为主题的许多演讲活动的助推。但不管怎样吧,无论是《农历》中的两个儿童五月和六月,还是短篇小说题旨"吉祥如意"、随笔题旨"寻找安详",抑或小说主人公的名字"如意",安详文化便形成了。
我不去讨论这个,我只是说,形成这样的一个解释模式或阅读印象,对于郭文斌的其他小说,对于他所面对的世界而言,都并不是准确的判断。
第二,有了以上限定,对于郭文斌的有些小说,显然已经处在了屏蔽或遮蔽状态,包括他本人的疏离。而这些小说,经过我的阅读对比,觉得的确是非常优秀的文学感觉,甚至像《我们心中的雪》这样的篇什,即便放到大学、中学教材中去反复讲,深味都不会有丝毫减少。
那么,郭文斌本人及其作品的阐释者为什么会久久沉湎于以上文化氛围呢?恐怕是一个说来话长的话题了,我不在这里讨论。在这里我想重点讨论的是,郭文斌本人及其阐释者似乎已经疏离了的一种相当可贵的文学感觉,而这感觉在我看来并不仅是文学感觉,它就是人学感觉。
简而言之,这种新颖的感觉就是以《我们心中的雪》为代表的一批作品,这些作品单要拉起来恐怕也有一长串了,譬如《门》《陪木子美到平凉》《水随天去》之类。虽然《门》已经十分接近,《陪木子美到平凉》也已经具备所有素质,但都不如这篇小说给我的印象深。原因是,这篇小说无论形式上、审美取向上,还是社会学信息量、叙事把握力方面,体现的是一种成熟的价值观。
这篇小说给"文化共同体"所面临的精神疑难和心灵处境,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打捞,它使文化共同体有了一次绵长的、艰难的和苦涩的对他人精神世界的全方位观照。今天多数作家无论怎样也不肯离开的所谓"人性",在这篇小说中恰好被严正批判。
人性的真正提升被推到了每个人的面前。读它,不油然使我想起了雷蒙·卡佛的短篇小说《阿拉斯加有什么》和玛·杜拉斯的长篇小说《塔吉尼亚的小马》。后两者的共同点,是都巧妙地化解了婚姻或爱情已经面临的危机,而郭文斌则是成熟地处理了两性关系在走向纵深之前的微妙而复杂的关系。
它的微妙是说一旦处理不当就会立刻发生方向性的变化,复杂是说,即便处理得体,也很有可能属于话语得当叙事却从深处分裂,或者即使叙事圆满话语中可能会埋下崩裂的陷阱。
富有智慧的是,郭文斌以"反高潮"的方式保留下了两性之间弥足珍贵的"爱情"——索性说,是颠覆了"无爱便是恨"的伦理模式,创造并主题化了两性之间日常又绝非"日常"的感情经验,从而深入地撰写了人的现代性困境。
现代人的情感处境,一下子形象地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人非如此不可,但又觉得非如此不可实在不可忍受。
因为叙事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了哲学所常常眷顾的话题,从而在类似这一主题的小说中显得特标独高。生长于西方自由民主文化土壤,《阿拉斯加有什么》中杰克、玛丽与卡尔、海伦两对夫妇之间话语之内充满激烈冲突的暗战,最终化解于他们所笃信的赎罪感,"威胁"于是由此浮上水面,结果呈现;《塔吉尼亚的小马》中雅克与莎拉关于未出场的莎拉的情人的暗处较量,读者的体验也基本终结于双方的"坦荡"和坦荡所产生的原罪感。
郭文斌这篇小说中的"我"和杏花,他们的完整叙事只停留在童年时代,他的发现在于,同时也完成了成年叙事这个本来缺席的故事,也就是说,反过来,他反倒把缺席的成年叙事构筑得还比童年叙事更可信、可靠。
究其原委,我以为这得益于郭文斌对我们优秀文化传统中成熟的道德伦理话语秩序的深刻领会。小说结束于"我"在毫不知情之中对杏花所送围巾的接受,伦理、道德与美和人性光芒达到了完美汇合,儿时两小无猜的"我"和杏花在雪地里用舌头舔雪花的细节,于是开始合理地重现,"抬起头,正迎上杏花甘甜、满足而又潮湿的目光。
心就变成了一个舌头,一个童年伸向天空的舌头,任凭杏花目光的雪花,落下来,落下来"。情窦未出时相知,历经多少年沧桑,而今突然邂逅,优美的伦理叙事是怎么持续的,小说已经无需再强化。
那样的一条围巾,和伸向天空舔雪花的舌头,完成了它们的文学史使命——绝对不亚于卡佛笔下嘴里叼着老鼠突然穿过客厅的猫,也不亚于杜拉斯笔下那个本打算与情人"自由地度假"的莎拉,却突然对丈夫雅克说"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去巴埃斯道姆旅行了"。
虽然都是变平凡为神奇的叙事,但是郭文斌因为打通了"文化共同体"深处的道德难题,我们接受起来自然心服口服。
那么,为什么说,郭文斌这一路小说可能被屏蔽或遮蔽了呢?一个基本事实是,"寻找安详"以来,阐释者和作者似乎都更愿意把关注点植入并非精神文化能解决的问题域,而忽略或者忽视了解决精神文化问题首先必须启动复杂社会学程序的难度。
结果显而易见,关于人本身的叙事,和关于人性本身的叙事,只能让位于抽象的描述和宏大的许诺,《瑜伽》(该集中同名小说)之所以产生叙事的中断,原因大概在这里。我所强化的文学感觉,指的就是类似于《我们心中的雪》这样,源于日常伦理却能从日常伦理中转化出高于日常伦理的审美能量、眼光和结构生活现实的能力。在我看来,这是文学更高一级别的人性观照和哲学观照,因此,它是文学对人的现代性困境的深入体谅。
重申这种文学感觉,无他,不过是感觉包括郭文斌在内,多数作家好像并不在乎消费时代人也同时是消费符号这一时代特点——如果再往前走半步,"我"与杏花之间的故事难道还会保持住那样一种饱满而丰沛的审美张力吗?答案是否定的。
追究下去,原因不见得就是作家或知识分子没有强悍的主体性,而是我们的人性话语没有产生出一种有力的制衡机制。这问题转换到日常生活,实际上就是"文化共同体"(也叫"价值共同体")未能彻底建构起来的问题。
而唤醒类似于《我们心中的雪》的文学感觉,等于说用感知性主体之间的共鸣,通过输出文学秩序的方式,重新界定消费社会个体的基本人性理念。只有这个才是内在于既有人性却又超越于既有人性的,否则,一切的话语努力都将因缺乏具体语境的支持而说服力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