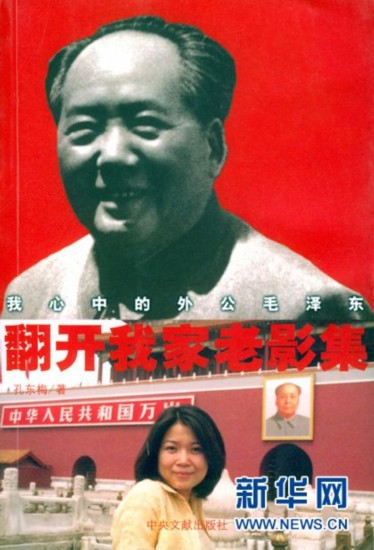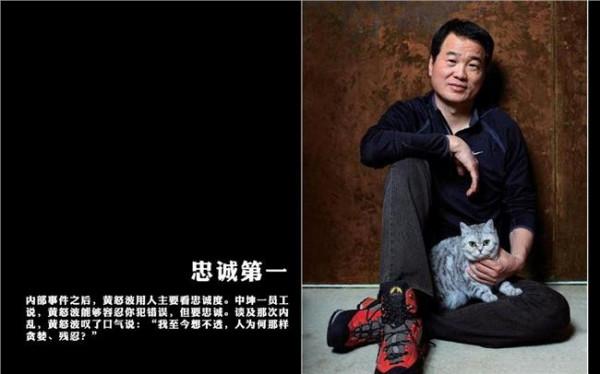曹汝霖之子 曹汝霖21条声名狼藉累及子女 曹汝霖怎么死的
说起曹汝霖,总有些绕不过去的问题,例如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和火烧“赵家楼”事件。然而,这些毕竟只是他漫长一生中的两个片段。和大多数名人一样,曹汝霖也有着鲜为人知的另一面,而后来者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真实、全面地还原这个人。
曹父卖地
供子留日
曹汝霖为家中独子,出生后因五行缺水,所以取名汝霖字润田。曹家算是书香世家,曹汝霖的祖父、父亲均曾在江南制造局任职,但家境并不宽裕。本来,曹家曾为曹汝霖请了一位师傅,在家授课,但后因师傅被大地主家用重金聘去,曹汝霖只好出外就读。
曹汝霖十八岁就考中了秀才,但他不喜欢写八股文,自觉科举无望,竟从未再参加考试。戊戌变法之后,曹汝霖一心想学习如何造铁路,于是投考汉阳铁路学堂。但是学堂只教授法文、几何、测量等,并没有铁路工程学科,失望之余,曹汝霖回到上海,恰逢政府派学生到日本留学,曹汝霖产生了自费留学的想法。
在汉阳铁路学堂学习时,不仅免费,而且学堂还给学生补贴,此次要自费赴日,曹汝霖的父亲虽然赞成,但家里拿不出那么多钱。为了让曹汝霖如愿,曹汝霖的父母商议之后,卖掉两亩地,为曹汝霖筹措学费。
对父母的支持,曹汝霖一直心怀感激,并由衷佩服父母的眼光。曹汝霖一直与父母感情很好,之后的岁月,每逢有变故,总是先考虑到父母,甚至在“九一八事变”后,有人劝曹汝霖南下躲避,为了年老不方便远行的母亲,曹汝霖留在了岌岌可危的天津。
声名狼藉累及子女
曹汝霖向来不否认其“亲日”立场。据他在回忆录中称,他对日本人的好感始于日俄战争期间。那时曹汝霖正在日本读书,亲眼看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百废俱兴的景象和开战时日本人踊跃从军的场景,心中已将其视为中国今后发展的范本。而且他认为日本与中国同为亚洲国家,可相互依傍。
日本人对曹汝霖的拉拢,始于战争结束后召开的东三省会议。会议主要就日俄战争后中日在东北的权益进行谈判,时曹汝霖已经回国,在商务部任职,作为袁世凯的助手参加了此次谈判。曹汝霖觉得自己“人微言轻”,但日本人却注意并开始拉拢这颗外交新星。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委任曹汝霖为外交次长。曹汝霖生平最受诟病的两件事——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均发生在此任期内。
1915年,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条”。据《陆徵祥传》记载,曹汝霖主张“即行承认,不必商议”,曹汝霖在自传中反驳了这种说法,说当时袁世凯举棋不定,要考虑之后再交各部,“各人唯唯听命而散”。之后,袁世凯逐条批示,吩咐外交总长陆徵祥和曹汝霖照办。
曹汝霖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谈判时的情形:“此次会议,我与陆子兴(陆徵祥别号)总长,殚精竭虑,谋定后动,总统又随时指示,余每晨入府报告,七时到府,总统已在公事厅等着同进早餐,报告昨日会议情形,讨论下次应付方针,有时议毕又入府请示……日本所提之二十一条,议结者不满十条;而第五项辱国条件,终于拒绝而撤回。会议结果,虽不能自满,然我与陆总长已尽最大的努力矣”“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同时,他指出在合约上签字的是总长陆子兴。
在《顾维钧回忆录》中,顾维钧曾如此评价曹汝霖:“我认识曹汝霖,并与其在外交部,特别是当签订‘二十一条’时共过事。就我们所共之事而言,我始终感到曹先生是一位能干的外交家,是拥护国家利益的。”
对于把巴黎和会外交的失败归咎于他,曹汝霖更觉冤枉。当时中国代表团代表为陆徵祥、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王正廷,曹汝霖并不在其列。段祺瑞事后曾说过是他连累了曹汝霖等人,把曹宅被冲击看作是项庄舞剑之举。
事发之后,曹汝霖等递交了辞呈,大总统徐世昌非但没有批准,还多加劝勉。但随着“五四运动”影响的扩大,迫于压力,最终罢免了曹汝霖等人的职务。此后曹汝霖避居天津,其实已经声名狼藉,就连他的子女,也受到了牵连。在北京读书的子女受不了同学的言语相继转学,他的儿子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同学们也都不肯跟他同坐,下课后也不理他。
为避嫌,他疏远法官同学
如果不是辛亥革命后仕途不顺,曹汝霖在法律方面的才能,可能终身被埋没。
在日本留学时,曹汝霖曾就读于东京法学院(中央大学前身),此学校的毕业生多从事律师职业,曹汝霖毕业后曾在日本各级裁判所实习,回国前还曾与人合办过一个速成政法班,为即将毕业回国的留学生们讲授刑法、诉讼法大纲、民法大意等。回国后在商部任职的同时,他还兼任进士馆(教授新科进士法律、政治、外国地理历史等)助教,教授刑事诉讼法。
辛亥革命后,政府成立了司法部,新定了律师条例,规定法庭诉讼可以请律师。已经辞去公职的曹汝霖申请律师证书,居然是“第一号”。当时很多法官都是曹汝霖的同学,为了避嫌,曹减少了和他们的交往。
曹汝霖的事务所设在家中,开业之初,因为人们没有请律师的意识,业务稀少。后来曹汝霖接了一个死刑犯上诉案件,在他的辩护下,死刑犯被无罪释放,曹汝霖从此声名远播。回忆起那段往事,字里行间都显示出曹汝霖的自豪:“从此大家知道诉讼不能不请律师,且知道我以侍郎做律师,区区之名,不胫而走,从而门庭若市……后来,法政学生挂牌业律师者渐多”。如果此描述可信,曹汝霖可谓开风气之先。
儿子女儿,一视同仁
曹汝霖十几岁时,家人为他定了一门亲事。21岁时,他娶原配夫人王梅龄进门。他对这门“娃娃亲”本就不满,再加上两人脾气不合,年少时没少争吵。加之后来曹汝霖曾做过些“荒唐事”,使得夫妻间没少赌气。49岁那年,曹汝霖又娶郭静真,此时,两房太太倒能和平相处。
王梅龄有子女六人,郭静真育有两女。曹汝霖喜欢孩子,也从不将夫妻之间不愉快的事情告诉他们,后来忙于工作,很少有时间和孩子们亲近,但却很重视子女的教育。他在闲暇时不仅时常向孩子们讲述人生的道理,还要求妻子要以身作则。在子女的教育方面,曹汝霖向来“不分男女,既愿出洋,无不允许”。其子女四人留学美国,二女儿梧孙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
在子女的婚姻问题上,曹汝霖也很开明。据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对子女婚姻,都由他们自己选择,虽形式上得我同意,然从未干涉,幸都圆满。”他自己的婚姻,也算圆满。虽然与原配夫人年轻时争执很多,晚年却能相敬如宾。郭静真在任何情况下都未曾离开曹汝霖,陪他终老。
爱国牌:梁启超、林长民这样玩死曹汝霖 5年前,因参与《“五四运动”90周年》专题,翻了不少档案,读了10本书,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转折点”“爱国运动”之类标签,虽不以为然,但几个疑点,始终未找到答案:
1、北洋政府对巴黎和会为何毫无准备?
2、美国总统威尔逊干吗百般提携中国?
3、梁启超、林长民(林徽因的父亲,林觉民的哥哥)怎么偏跟曹陆章(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不对付?曹汝霖在《一生之回忆》中,给了个奇葩解释:林长民曾向他借几千元,曹没答应,林因此衔恨。
4、巴黎和会如此失败,两年后的华盛顿会议,为什么中国又能如愿?
读了唐启华先生新作《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顿觉冷汗直冒,回想曾经的文章,在在皆错,好在《三联生活周刊》等一流媒体当年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在没读这本书之前,我们都不太知道“五四运动”,乃至巴黎和会。
北洋政府未必昏庸 本书第一章略显枯燥,作者罗列了“保和会准备会”百余次会议的研讨内容,对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会感到大开眼界。
首先,北洋政府对“巴黎和会”早有预判,准备了近四年,成立了专门的“保和会准备会”,并非过去所说的愚昧颟顸。甚至后来对德宣战,也为了确保参加和会的资格。
第二,“准备会”遍请学界高人,研讨水平极高,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能做出那么精彩演讲,即为重要成果。
第三,注重细节,甚至考虑到中国离巴黎远,怕错过会期,先将驻美大使顾维钧等人派往欧洲等待。
可见,当局苦心孤诣,志在必得。
美国突然送来“秋天的菠菜” 1916年—1918年,中日关系有所缓和,寺内正毅内阁上台后,改变了大隈重信内阁(曾逼迫中国签《二十一条》)的霸道作风,以极优条件借给段祺瑞政府1.45亿日元,并通过密约攫取在中国东北筑铁路、采矿等权利。
在此氛围下,中日同意在巴黎和会上互相支持,步调一致。
恰在此时,美国也对中国频送秋波,美国总统威尔逊正拼命推销“民族自决论”,即“各民族有权按自己意愿处理自己的事物”,但列强反应冷淡,他们明白:美国作为新兴大国,想用唱高调来取代英国的霸主地位,这是欧洲早就玩剩下的把戏。
可对积弱的中国来说,很难抗拒这个诱惑,而中国的积极回应,又让威尔逊大为振奋。每个人都需要走狗,国家亦如此。为了让所有犹豫中的被压迫民族看到榜样,威尔逊决心全力扶持中国。
在赴巴黎前,中国的和会战略是“联美亲日”。
天皇被放了鸽子 但,就在外交总长陆徵祥动身前一周,美国突然提出:在美日之间,中国只能选择一个。
美国在崛起过程中,为了避免触怒英国,重点向太平洋扩张,先后得到夏威夷、关岛和菲律宾,美日形成对峙。美国最担心中日间存在密约,美国不愿帮助一个对日本没牵制作用的中国。
这,迫使中方大幅度调整和会战略,改为“联美制日”。
按计划,陆徵祥先访日7天,再访美,然后去巴黎。驻日公使章宗祥全力斡旋,为陆徵祥争取到和日本天皇见面的机会,可一到日本,陆就“病”了,放了天皇的鸽子,日本首相来探口风,陆徵祥称中国态度不会改变。
日本人认为中国将与他们配合,但陆徵祥认为,双方没有文字确认,无需承担责任。
打了日本人一个措手不及 巴黎和会上,中国突然抛出“山东问题”。
一战爆发后,日本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租界,在巴黎和会上,日方坚持以条约方式,迫使德国先将山东权益转给自己,然后再还给中国,只保留经济权益。
按原计划,中方不准备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山东问题”,因受制于《二十一条》,就算提出也收不回。可在美国的鼓励下,中国代表团决心一搏。顾维钧的演讲极为精彩,他援引《国际法》,提出《二十一条》是在武力胁迫下签订的,并无法律效力,得到列强赞同。
日方大为恼怒,认为是陆徵祥背叛诺言,采取了对立态度,并以退出巴黎和会相要挟。
威尔逊让中国放弃面子要里 子
由于意大利已退出和会,如日本再退出,威尔逊力保的“国际联盟”有流产风险。此外,日本也唱起高调,提出国联应“遵守种族平等原则”,当时列强均有殖民地,无人能遵守这一原则,这让“民族自决论”失去了道义上的立足点。
为保住国联,威尔逊只好出卖中国,在山东问题上做了让步:相关条款虽不列入合约,但要求日本在美国总统、法国总理、英国首相前面口头承诺,把山东还给中国。
美国国务卿对顾维钧说:三个大国给中国做保证,你还怕什么?
这个结果大大好于中方预期,不签约,中国就无法取得战胜国地位,中德便仍在战争状态中,得不到战争赔款,还要继续支付德、奥两国的“庚子赔款”,显然弊大于利。北洋政府决定签约。
梁启超还是没玩过陆徵祥 就在此时,梁启超自法国发回电报,称:“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梁启超没把电报发给总统、总理,而是发给林长民、汪大燮。
梁、林同属“研究系”,与新“交通系”对立,后者把持国内铁路。研究系背后有美国大亨支持,欲引入美国资本,将路权收归国有,统一修造,因此被贴上“亲美”标签。而交通系则由留日生曹汝霖把持,被称为“亲日”。
铁路占压资金太多,谁掌控铁路,谁就掌控了权力,从当年李鸿章建北洋水师起,官员们便悟出此道。民国时,梁士诒因掌握铁路,被称为“二总统”。
巴黎和会时,梁启超以采访名义赴会,带着丁文江、蒋百里、张君劢、刘崇杰等人组成的超豪华顾问团,陆徵祥备感压力,甚至不辞而别,远遁瑞士20余天,在各方劝说下,才重回巴黎,继续参加和会。
这一以退为进的让贤,令梁启超失去了直接干预的空间。
林长民的大招多 梁启超发回电报的第二天,在研究系机关报《晨报》上,便刊出林长民雄文《外交警报敬告国民》,高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林长民的口号体取得了巨大成功,3天后,“五四运动”爆发,学生们打出“威大总统(威尔逊)万岁”的标语,他们不知道,正是威尔逊力劝中国签字。
全国各界电报如雪片般飞向巴黎,中国谈判代表怕担责,反复问政府意见,可政府也怕担责,拐弯抹角鼓励代表们自作主张。人人都不愿顶雷,只能拖下去,可就在学生们激情渐渐消退时,林长民又玩出大招:抬棺上街。于是,新一轮的激情再度燃烧。
人人都不肯踩刹车,必然是少数人绑架多数人。
时代把读书人逼成了小人 跳出本书内容,有太多疑问引人深思:梁启超、林长民时任总长,肯定有探听机密的渠道,可他们为什么不去问问呢?为什么听风就是雨?梁当年46岁,林43岁,他们真会幼稚到如此地步?
原因也许很简单:那一代知识人机会太少,境遇落差太明显,逼得人不得不投机。
民国教授工资较高,但也不过三四百元,曹汝霖在《一生之回忆》中说,袁世凯拉他入阁,许以月薪2000元,他却认为没他当律师时高。况且,教授工资常被拖欠,且一所大学中,教授职位无多,需使出种种手段,才能获得。教授如此,其他可知,连著名报人邵飘萍都在大搞有偿新闻,为了吃饭,读书人只有降低人格。
本书中有个细节很有趣,顾维钧在美国也收买记者,以刊发对中国有利的文章,他对上级解释说,找个人比找报社划算,费用更省。
在一个充满世俗精神的国家中,很难期望天使降临。要么呼风唤雨,要么生计艰难,梁启超、林长民肯定会算这个账。
学生们为何甘当工具 煽动民意来达成个人目的,本是自古就有的手段,而梁、林的幸运是,当时中国确实准备了一批傻人,供他们驱使。
中国传统学问以育人为主,而现代教育以传播知识为主。近代以降,中国知识人最大短板是知识不足,可吊诡的是,后人却总在批评他们道德有问题。
传统与现代各有所长,关键看怎样结合,直到今天,这个结合仍不完美,“五四”时更明显,那时读书人社会地位很高,可在校园里,他们却要忍受考试的压迫,巨大的落差造成人格扭曲,他们需要一个借口来反抗,而爱国主义最合用。
“五四运动”期间,不少学生不再读书上课,而是到处发名片,自封“学生领袖”,这既极大地满足了虚荣心,又不必付太多代价,还能骗取社会资源。而社会的鼓励,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激情,甚至不惜乱施暴力。
爱演戏的一代人 爱国主义能被大家接受,因为在西力东渐的大背景下,原有身份共识被打破,人们迫切需要一个代用品,以合理地发泄怨气,将个人不如意的责任,推给别人承担。
于是,我们匆匆建构起来了一个受伤的民族主义,只有在受欺负时,才会想起自己是中国人,高呼你也是中国人,为什么不来帮我?可在平时,很少会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而对别人更好一些。
缺乏共同的认知,则共同的挫折感便成了代用品。它舔舐着我们的伤口,但也让我们沉浸在受害者的感觉中,敏感、冲动且悲情,由于和现实生活差距太大,只好用戏剧化来填充。比如陈独秀,因错过“五四运动”高潮,未能满足他对悲壮入狱的体验,所以他偏偏要在一个月后到街上发传单,得偿所愿。
当人人都有心病时,集体发作在所难免。
谁也别想赢 曹陆章的政治生涯,从此中断,他们的经验、学识失去了发挥的舞台,如果他们能早点高呼爱国,会不会先把梁、林拿下呢?其实,梁、林下场也不好,由于破坏了政治的潜规则,他们从此仕途艰难,梁启超转向做学问,林长民后来只好去投奔郭松龄,结果死于流弹。
他们都是那个时代中国最优秀的读书人,可悲的是,他们互相消耗了彼此。
其实,那些参与者、旁观者、反对者们,谁又是胜利者呢?一次无操守的运作,带来了底线不断被突破,而一次次集体狂欢后,曾经的荒唐反而成了神迹,成了精神地标,激励着人们开启新一轮的悲剧。
激情从不会因更多的激情而停步,要打破这个循环,只能回归理性。
历史有太多的侧面,太多的不为人知,这就是为什么,在选择立场前,不如先去追求知识、追问真相。而这,也许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