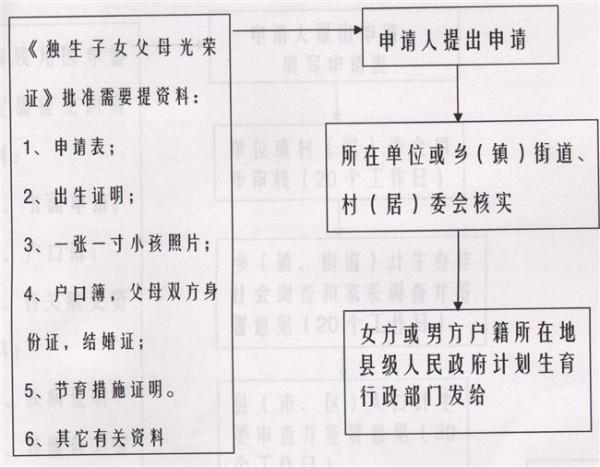徐琛惠济区 徐琛:关于“艺术区”现象
如果说到最近有什么艺术现象?最重要的当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已经在北京形成规模和态势。准确地说,在靠近北京国际机场的费家村,索家村,草场地东村集结着大量当代的青年艺术家。
他们在靠近城市的乡村地带集结,用不大醒目但很另类的方式租农民的地,自建画室或者工作室,这种特别的方式区别于CBD的声色犬马,也区别于中关村的人声鼎沸,他们采用一种独立的扎根农村乡野的方式,在租金极便宜的乡村地带自然聚合。
虽然现在的乡野也许并非纯粹和地道,但是他们依然希望以乌托邦的理想,枫丹白露的情调,也许在有钱人看来未免寒碜,但是艺术理想的执着和都市提供的可能空间让他们一传十,十传百地在一个意味深长的地区“朝阳”和“顺义”之间的地带集结,繁衍和兴旺。
即使在索家村因为土地的使用权问题,土地承包开发商和租用土地创立工作室的艺术家被当地的农民以严重妨碍和损害当地农民经济利益而被驱逐,这个现实本身虽已明显区别于十五年前由于政治原因而被驱逐的圆明园艺术家,然而在这个更多地重视个人价值的实现和公众利益维护的时代,追求独立精神意义的艺术家在商业经济时代的行为,使他们成为与土地承包开发商的合谋人。
索家村代言的乌托邦在经历了数月的繁盛后迅速破灭成一个个虚幻的肥皂泡。但是仅一村之隔的费家村,又名“香格里拉”的艺术实验区则静寂地保佑着自己的艺术理路。在被保护的小范围内,他们实践着如同神话般的艺术想象和艺术标底。
而东村集结的当代艺术展出仍然吸引着对当代艺术极为感兴趣的策展人和他们追踪的目光。也许这一有着较为典型的当代性的地域,有着与保守村落不同的边缘开放性和直白不回避的现代性,它比较费家村的审慎和索家村的声名鹊起,它有着敞开和直白的性格,谁都可以去观摩,谁都可以评说,但谁也代表不了它所暗含着的某种独立的立场。它依然故我地在那里。
而798似乎已成为风光的今日“艺术新贵”代名词。从几个艺术家临时租用空间到迅速地成为艺术家寻求工作室的绝佳风水宝地,加上新闻媒体炒作,和直接的政府表态的首肯,798在一度似乎风雨飘摇的撼动中却牢牢地站立而岿然,七星电子集团的稳固和一时的财力匮乏最终被成长起来的艺术风景区和渐成气候的艺术家独立工作室的坚持而感动,没有被财力雄厚的房地产开发商打跨,而果真将房地产开发商充满金钱气息的肥厚手掌打了回去。
一个独立的艺术新区在悄没声息中渐次登场,而在关心纯艺术的艺术家眼里,也许它是更为商业性的艺术行动,那就是在北湖渠桥的南端原酒厂的位置出现以韩国财团为主的画廊集团。有着强大经济后援的韩国画廊集团将目光锁定在距离望京不远的区域,拓展和宣传以韩国文化为代表的艺术家及其艺术,似乎是顽强的韩国人在民族精神延伸的前提下的一种必然。
比较798艺术区在3818库集结的台湾数家画廊,北湖渠的集结显现出一种态势和后续的力量。也许作为台湾画廊由于地域的原因,以个人的面貌挺进中国大陆似乎散兵游勇,而北湖渠的阵势则更多地带有集团的强势和超出阵势以外的潜在力量。
现代社会分工愈来愈明确化,细分化,跨越商业和艺术的挑战力毕竟太大,而有限的生命如何与无涯的时空世界去比拼?艺术家作为敏感而睿智的群体很快作出战略调整,纷纷重操旧业,回归纯绘画,设立工作室,在赚足商业的利润后重新拾起画笔。
这些年,各地艺术家集结京城发展艺术和他们赖以养息的资讯,人文理念和国际化的环境以及潜在的艺术市场血脉相连。但是,近些年城市的发展和经济的迅猛让参与经济的艺术家愈来愈清醒地意识到作为艺术家的独立和原创的备受尊重。
他们在放弃装修和广告的巨大利润后,纷纷转向纯艺术创作,试图回到艺术的出发点。
也许作过各种尝试的艺术家在“穷途末路”后,再作知识的更新和角色转换时间已晚矣。他们在可能允许的范围内变换身份和位置重新回到艺术,回到纯绘画状态。
因为摆脱乌托邦的虚无,真正投入这个变幻的社会,适应社会角色的变换,调整最初的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开始明确艺术家在社会中的定位和身份,而不是茫然地突围和冲出围城,成为每一个艺术家的共识。
市场经济这架“马车”已义无返顾地前行,原来试图以人文理念和启蒙思想拯救中国的艺术家也成为这架狂奔的战车上试图勒紧缰绳的驭夫,不得不随着战车狂奔而不至被甩出去。
个性化的,独立的,区别于原来公司运营性质的工作室纷纷并列在一起;或者以口口相传的方式组合在一起,以租金的廉价取胜;或者以艺术影响力感召艺术家;或者以商业化的财大气粗,腰身粗壮取胜;或者以另类的方式,特立独行,不羁于世;或者在乡村田野间茁壮成长。
艺术家愈来愈成气候,就象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一样曾经喧嚣,随行就市,也象CBD高档商务区外企公司扎堆,艺术也可以成为一种独特的现象,也可以成为与风行一时的电脑,电子产品和“商务通”一样炙手可热的东西。
艺术越来越成为一种可以交易的买卖,原来虚幻的用以想象的美好,原来用以寄予希望的独立精神,原来被用以奢侈的艺术浪漫全都成为在商品社会等价交换的物质产品。是慨叹这个经济社会?还是悲乎哀哉?
但是,乐观地看待这种显现则是另一种理解。艺术也可以在一个经济繁荣的时代,成为“与时俱进”的时代物产。在经济大繁荣的时代,艺术不但没有萎靡,反而有所振作;在经济压倒一切的时代,政治已经被忽略和“重新洗牌”,成为经济的附庸,艺术则成为在二者空隙间大跳其舞的“众神”。
荒谬时代曾经的不寻常,一但演变为现实的正常,反而一时不容易被理解,就象欣欣向荣的市场泡沫一旦被挤碎,则许多神话和传奇就成为荒诞的故事一样沉睡到昨日的梦中。
而艺术新名词,如“草场地”“东村”“费家村”“索家村”“798艺术区”和“北湖渠”等等就象一个个似乎诗意的栖居地,似乎是与红尘滚滚的尘世隔绝的“桃花源”。
似乎远离尘嚣,似乎遗世独立,也似乎遥远不可及,但事实是它们存在着,只不过经历着与众不同的沧桑和不同想象的坎坷。
草场地,费家村,索家村,798艺术区的艺术家,他们是不是仍在坚守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他们是不是“小王子”眼泪滴下来后遥望的星空,还是他们是杉上春树小说营构的理想世界“挪威的森林”?他们是我们这个良知没有泯灭时代的感恩者,还是这个急促时代让你停息的驿站,他们在这个步伐越来越快捷的时代成为少数可以嘹望的灯塔和航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