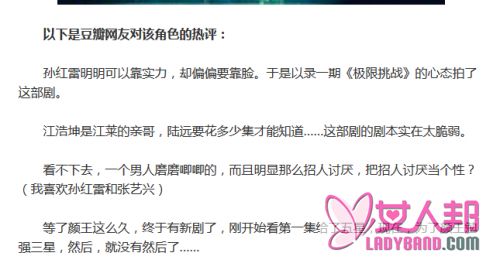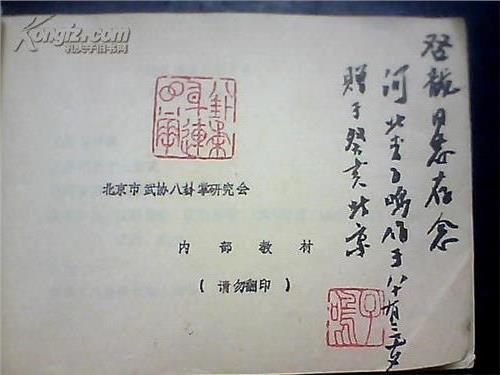画家王庆松 【在线影展】王庆松:不去吃饭的艺术家才是最牛的
王庆松作为中国当代艺术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一直以极其刺激的图像作品和特立独行的形象、言行出现在大众面前。他的摄影作品紧跟时代步伐,把摄影和舞台艺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兴师动众”,用众多的群众模特和庞大的场景来突出主题。他的作品还将传统文化符号和现代化的社会现实嫁接在一起,调侃当下文化价值混乱的社会现状。
2015年是王庆松首次督军,在重庆长江美术馆策划了轰动一时的首届长江国际影像双年展。在他有意制造的这场“是· 非”纷杂混乱的展览中,看似毫无逻辑和撞车般的雷同作品屡屡变为了对中国当代摄影现状的隐喻。
本采访特意以一种特别口语化的方式进行,王庆松在尽情的叙事中,回忆了90年代初他来到北京时很多同时代艺术家的艰辛、无可琢磨的展览机缘、他对自己作品纪实性和新闻性的理解以及他对不同时代的基金会赞助模式的亲身体会。
(本文由谷雨计划支持。谷雨计划致力于耕耘中国故事,支持中国非虚构作品创作与传播,由腾讯网联合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陈一丹基金会发起。谷雨计划微信公众号:GuyuStory。)
那时候可以很便宜的生活,现在反而更难。现在看似机会更多,其实当时更容易出头。
谷雨:你是在大庆出生的吗?什么时候到的湖北?
王庆松:嗯,到湖北应该是69年。那时三岁左右,湖北出现了油田。当时属于潜江,荆州地区,大概离沙市六七十公里。
谷雨:你小时候一直是在油田长大的吗?
王庆松:对,一直待到上初三,然后就调到沙市了。跟随父母,父母到哪就跟着去哪。后来父母被调到江汉石油学院,也就是现在的长江大学。我在那里开始读初三。因为发现了油田,需要培养更多的人才,就成立了那所大学。之前只有小学到初中二年级。我去的时候是第一批初三,初中毕业之后才成立了高中。高中只有两年,也是第一批毕业,17岁就直接参加工作的油田子弟。
谷雨:那后来是什么时候来的北京呢?
王庆松:来北京是93年。那时27岁,刚完成四川美术学院的学业。毕业就来了北京。先是在圆明园附近。住圆明园的时候还不知道有画家村,是我一个朋友的姐姐住在那里。我们就在国际关系学院后门那里租的一个房子,但和圆明园就相隔一个小树林。我们住的地方和画家村大概是一个片警管理的,为了方便管理,他们不希望到处都是外来租户,就建议我们去画家村。某种程度上算是把我们赶过去了,可圆明园的房租太贵。
谷雨:我以为画家村会便宜一些。
王庆松:原来我们住的地方就是农民房两间,两间中间打通,我和一个很好的朋友一起合租,房子也很好,房租大概就是150块,但去了画家村就要大概250到300了。我那个朋友觉得价钱还能接受,但我觉得很贵了,因为在沙市租一个很好的房子带厨房的也就大概25块钱,画家村那个房子很破,地上坑坑洼洼的,而且是一个偏房。
谷雨:再后来就去了宋庄?
王庆松:我开始是没有打算去宋庄的,因为确实是太远了,所以开始是从圆明园往香山那边搬,在香山住了一个多月,然后又被警察赶走了。那个时候的警察很厉害,没有像现在这么多摄像头,居委会就群众举报,最后没办法就只能去宋庄了。
谷雨:那个年代住了这么些地方,你很完整的经历了中国当代艺术那些年的一个个重要的地点和人物。
王庆松:对,2000年过后还差点去798。798当时很便宜,我们那时候是两毛三一平米,那边基本上没什么工作室。之前到处被赶,住过宋庄后来搬出去住了一段时候又被赶回来,有时候晚上睡觉警察能把门踹开。那个时候社会也在很快的发展,房价涨的也很快,过两三个月来问房子的人多了,只要价钱比我们出的高就把我们赶走,找各种理由把我们赶走,然后再租给出高价的人。宋庄我是好几次进去出来进去出来。
谷雨:你那时候也没什么收入吧?
王庆松:那时候没有,但是那时候可以很便宜的生活,现在的年轻人不能很便宜的生活了,可能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房租。现在到北京来发展,起步得十万,对于一般人而言做父母的得把工资全花进去,还觉得很费劲,买房子什么的就根本不可能。
这样的话就压力很大,所以现在反而是更难一点,而且看似机会更多,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机会,不像以前,比如说展览,那个时候北京的展览很少,一个星期就两三个,大家就花很长时间去看,花一整天时间去看展览,然后大家一起吃饭。
能知道展览信息是很厉害的,而能在一起吃饭的是关系非常好的,相互认可的艺术家。我们那个时候成功者是可以拍桌子的,饭吃到一半,把桌子一拍“我今天成了!”那就是确实成了。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传播,就是口口相传,说张三或者李四成了,大家就都知道他成了,见到他就是点头,那个时候机会很少,但是相对起来成功率很高。
谷雨:现在通过展览能够一展成名的就很少见了。
王庆松:对,现在的大双年展都不能达到那个效果。因为展览的人太多了。
那个时候摄影是当代艺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像现在,现在虽然表面上很多人去摄影,但是人的那种理想状态没有了。
谷雨:你的作品是哪一张或者哪一个时期开始能够有比较好的销售,能够保证比较正常的创作和开销。
王庆松:有孩子以后吧,2000年到2001年,生活可以解决了,正式卖作品是从2000年年底。卖的最好的其实是《找乐》,拍《老栗夜宴图》完了以后的一个合影。《夜宴图》还有很多人不喜欢,一个原因是细长的不好装裱。拍完了《夜宴图》我说大家来合个影,就借着那张床,一个女孩在那里吹箫。但这个作品被很多人、尤其是国外的很多人误解为是在吸大麻,卖得很好。那个作品就差不多解决了两三年的生活。
谷雨:98年你做过一个台北双年展,做了一个作品印在金丝绒上面,那件作品的资料还有吗?
王庆松:没有了,之前很多作品都弄丢了,因为在2000年我做自己的个展之前,我是没有把自己定位在摄影方面的。摄影最火的时候也就是97和98年的时候,99年其实已经到了摄影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摄影是当代艺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像现在,现在虽然表面上很多人去摄影,但是人的那种理想状态没有了。
那个时候我还是在“艳俗艺术”里面,我还不愿意把自己的时间花在摄影方面。到了99年,我已经觉得摄影是当代艺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就一直在想写一本关于摄影的书,写的时候能够把自己也加入进去,但是事实上没有写成功。
到了98年台北双年展的时候,当时一个策划人对我说“明天有一个日本的策划人过来。”我当时拿的照片是用A4纸打印出来的,没法编辑,就将原作挑了两张送过去。
谷雨:你是怎么打到金丝绒上面的?
王庆松:就是喷绘,那个时候很麻烦,因为别人不给喷,金丝绒能把喷绘头给磨坏了,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后来我就和日本的策划人名叫三木讲我的作品,我的作品是表现都市之中人的欲望,用金丝绒是因为它是一个闪光的东西,闪光、华丽,具有我们中华民族的闪光、华丽,而且金丝绒的作品从不同的方向上可以看到不一样的画面,看着影像会有一种变化,有时候会消失、有时候会闪光,但跟她聊她好像没有什么感觉,给她看了照片也感觉平平,于是我说我带了原作,要不你看看,她一看也没有说什么,就只是说好。
当时那个展览的主题就是艳俗,我的主题和这个主题一模一样,本来说好每个艺术家大概二十分钟,但最后我和她聊了两个多小时。
当时我和一些其他的艺术家本来是打算去参加台北双年展的,结果过去不包机票,而且在上世纪90年代从大陆去台湾很麻烦,我后来觉得去一次台北要花两千块钱,最后我就没有去,但其实这个展览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让国际上很多人看见我的作品。后来98年99年的时候就去参加了很多双年展,包括台湾和意大利的,只要是35岁以下的都去参加,那时候感觉只要参加一个展览,展览上就会有人邀请我参加另外一个展览。
谷雨:一个展览接一个展览。
王庆松:后来在2000年上海双年展,阿尔勒的弗朗索瓦第一次到中国,来上海看中国的东西。他们也没介绍,弗朗索瓦就拿了一个小册子,说是法国南部一个小镇上的一个展览。他很激动,将他们过去两届的展览的册子给我。
后来我回到酒店,翻这个册子后发现这个小镇做的展览还挺好,那时哪知道他们是那么好的摄影节。但这个事情就过去了,3年后他们做了一个关于中国的展览,中国的艺术家去了十几个,他就想让我进去,但这个展览并没有邀请我,因为是请的一个中国人过去策展的,他不能干涉策展人的工作。
到了2006年的时候因为获得了一个国际奖,他才跟我说他的心终于放下了,从2000年见到你就想一定要邀请你来做展览,但是每次都很困难,06年他让我做评委,后来又泡汤了。弗朗索瓦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看起来很柔弱,但是骨子里有反叛,法国的整个体制还是很严密的,所以没有办法。
02年平遥国际摄影节,当时所有人都说我一定会获奖,最后却没有获奖,但是所有前来观展的其他摄影节的主持人都以个人方式找到我,邀请我去他们的摄影节。从03年开始我就陆陆续续的参加国外大大小小的摄影节,慢慢的开始拿我的作品作为摄影节的宣传,再到后来我就不愿意参加这种摄影节了,国外的很多摄影节也特别像中国的庙会。
摄影的优势得益于它传播快,后来写社会评论的人开始拿我的作品做插图。现在的摄影比当代艺术更有趣,我现在在开始往电影方面偏,电影肯定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之前的电影有点被扭曲了。
谷雨:对电影的管制比对其它艺术门类的管制严太多了。
王庆松:如果希望在电影院播出的话,限制特别多,但是可以不仅仅局限于这方面,现在的电影有的可以是极小的投资。如果我来做的话,我不会做很具有艺术性的东西,我会仅仅就是做电影,有故事,通过故事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有剧情,但是剧情又不是重要的。
我一直在准备,但是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作品。可能明年年底开拍,因为我希望以雪景为开始,等到真正的下雪的时候,这样可以节约成本。现在摄影已经大面积推广了,我想换一种语言可能更有意思一些。
谷雨:我之前看到一句你说过的话:“西方所谓的现代艺术进入中国以后把中国传统的艺术文化脉络打断了。”我觉得你的作品已经早就进入西方了,你现在还会有这样的想法吗?我觉得这个因素只是一个部分,中国的文化断裂主要是自身的历史和社会原因造成的。
王庆松:对,但是那是一个导火索,西方文化的传入对中国是有很大的冲击的,像市场上商品,大众认为外来的一定是贵的,是好的,和日本不一样。日本的商品会标示“国货”,在日本国货是很好的。中国原来的文化受到两面夹击,面临整个传统文化的流失。
谷雨:你就很快的把学院给你的框架和束缚抛弃了,在你这几乎已经看不到学院派那种感觉了,这和当时来北京的环境有关吗?观念上怎样发生这样重大的改变的?
王庆松:学院对我来说只是一个给别人看的东西。我考了七八年,进学校的时候已经比老师年龄要大了,而且我也不可能上湖北美院,我很多同学在那当老师,去了我会不好意思。所以想去外省,去四川。在学校里边我们还是受了一个框,就是我们在学的时候,其实就学了两年时间,有一年时间我还是按照非常传统的方式去追求造型能力,这个是必须要的,也下了功夫的。
再就是我不追求大,别人一般进学校之前就是画的那个大的人体,我还是几个星期就画这个小的,要把这个东西深入下去,很多头像画成小的。
我发现画大的就还想两笔涂完,画不深入。而且我不让老师改画的,老师改画经常改到一个星期后你发现这星期画室里的东西都画得差不多一样了,老师过来基本上我都躲着他画,他站在我后面我也躲着,画的再烂你也要自己去找感觉。
93年毕业出来我就直接到北京来了,在家呆了很短时间。那会儿想筹点钱,在我哥的餐厅打工,让我哥给点生活费,我根本就没想过在湖北呆着,92年我是先到北京来看了一趟展览,接着93年就一定要来的,就没有想,而且也不想回去了。
最早你要能知道哪儿有展览就很牛逼,再后来能被叫上一起吃饭很牛逼,最后你能不去吃饭才是最牛的。
谷雨:北京是什么东西对你感触比较大?
王庆松:中国美术馆看了一个日本富士美术馆收藏展,富士电台可能有一个美术馆吧,反正叫富士美术馆,他们就做一个西方从古典主义蛋彩画开始,一直到印象派之后,所谓后印象,就这批东西。不是画对我影响很大,而是那时北京的人,社会的精神,我看到很多人做笔记,这个画是什么感觉,那个画是什么感觉,是一种什么状态,心得呀,画个速写呀,那个图是什么样构图,色彩,很多人认真的看,我就被这种文化氛围感动了。
80年代末我们对文化就没什么兴趣了,那时候开始商业化,92年南巡之后就真的全民开始做生意了。
我上大学前在单位就摆台球厅,最后摆地摊,做生意。92年来北京,我就突然感到哎呀!北京怎么那么好呢!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来北京。那时我用本子写了三篇日记,日记的名字我都记得,“北上之路”,就像万里长征似的。
本子是硬壳的,一定要用硬壳的,写了不容易坏。北上写了三天,第一天写了,第二天写了,最后隔了两天写,就一星期写了三篇,之后就没有了。
谷雨:你在很多场合会说自己的作品有纪实性和新闻性,您怎么看待纪实摄影的?
王庆松:纪实是肯定的,摄影的优势就在于他的纪实性。现在很多人都在把摄影当成当代艺术在做,做的花哨,贴点东西,当代艺术上使用媒介和材料,粘点破布,锅碗瓢盆什么的,60年代到80年代西方很多就弄这玩意儿,把摄影开始往那方面弄。
我觉得和那些大艺术品就差很远,一看就小设计小技巧。所以我觉着摄影的纪实性是非常重要的,最早我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往现实主义方向,当然也包括纪实的手法,我一直没有放弃使用这个方法去拍摄,尽量直接拍摄,少用电脑动,尽量不动,就是调了色。
谷雨:所以其实你是经历过这一阶段,然后再找到你自己要做的。
王庆松:对,那个时候电脑去拼的很多,就觉得那东西很无聊。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只是可以提供一个行为艺术的形式、图式吗?当然不是这样,艺术的形式翻过这一篇后这个形式就是一个复制了。
摄影其实是需要你创造你自己的一个形式,艺术肯定要以一种形式去呈现出来。但它不是表面形式,你折腾那两下啊。因为我自己也做了很多,在塑料上也做过,包括镜面上的,都不是我想要的感觉。那我最后为什么用一个朴实的方式,其实在2000年我开始做个展的时候印在相纸上。
我觉得我不想再印在各种所谓材料上了,展览也是这样子。当时做的一个展览叫王庆松作品展,请柬都还是印的作品展,开展前在门口我把那个标题和海报加了摄影,就叫摄影作品展,后来我的简历上都这么写。
但也得益于加了摄影,因为加了摄影,2000年以后所有写摄影的都写了我。第一次就开始写了,让老栗(栗宪庭)写的前言嘛,几百字,不到一千字。老栗一分钱没要,他就很朴实的写了一段。我自己把自己写在摄影里面了。
谷雨:这个还蛮重要的。
王庆松:那个展览其实是卖了几张,但花了几千块钱,差不多持平。场地是免费的,装裱花了不少。我当时就知道接下去有宣传,要求画廊印个折页,他说行。那家画廊原来是做很传统的水墨画的,他希望我来做个当代的展。虽然是一个普通的画廊,但做的时候很使力,这种情况大家就可以不在乎是大画廊还是小画廊。
美术馆有时候也是这样,有一次在德国的一个小城市,有家美术馆是旧邮局改造的,三层楼全部都给我。那是一个老的所谓印刷之都,他们给我11个月展期,全年所有经费的百分之七十全花在我一个人身上。那个展览是做的很扎实的,看似小的一个美术馆其实是一个艺术中心。
谷雨:是国外的还是?
王庆松:德国的。西方有些地方还是陌生的,土耳其,包括英国原来有很小的一个画廊,整个画廊加办公室还没有我工作室的这间房大,但观众很多,塞得满满的。一进来一个人也不认识,我觉得那个展览是最成功的,没有熟人,那样传播的是另外一群人,而且人家也能卖,其实那些所谓好的画廊反而不一定卖得动,因为它的客户好多都太熟了。
这种小画廊很有意思,今年肯定是要去巴西展览。哪怕不知道当代艺术也没关系,要找一个不一样的宣传方式。这些小画廊使劲,是真使劲,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它没有那么大的party,就开幕结束的时候买作品的那几个人在这儿吃饭,没有买的人就走了,就很简单。
我们这儿一搞就几十桌,北京的小馆都包满了,这个也是我们原来的心态,也是一个过程。最早,你要能知道哪儿有展览就很牛逼,再后来能被叫上一起吃饭很牛逼,最后你能不去吃饭才是最牛的。
真正去了解异国文化还是有用的,我做的艺术和西方有关系,就希望去美国看看,了解东西方到底谁影响谁。
谷雨:你有一段时间得到过纽约亚洲文化理事会的支持是吗?我们来谈一下基金的帮助。
王庆松:2003年,ACC,很多中国最早的当代艺术都和它产生了关系,包括老栗、蔡国强,摄影方面应该是邢丹文。还有一些人上学读书就是拿那个基金。我当时也是在一个饭局上认识他们那个头,纽约总部的,他们是每隔几年就来中国考察一遍。
饭局上我知道申请已经快晚了,还有一个月时间,他说你提交,我们往后推一个月。我就很简单写了申请,因为我做的作品和西方有点关系,就希望去美国看看,了解东西方到底谁影响谁。我想去看看美国华尔街、拉斯维加斯,芝加哥、丹佛、旧金山、洛杉矶,反正就知道这么几个大城市,没想到他们就同意了。
三个月时间,他们给经费就来回转,什么也没有要求,后来走的时候我就不好意思,签字送了一个小的作品。实在是不好意思,因为我跟我夫人待了三个月,每到一个地方只要你说要见谁,说得出名字,他们就去联系,一定让你见着这个人。
那个基金会是很厉害的,洛克菲勒支持,甚至你要在那,弄个汇报展览它也去做,那时候资金给的足,但我们见不着钱。就到哪都给你发个支票,给你一点点现金支票,大概是几千美金,所有的都是支票去划账,挺有意思的。
谷雨:感觉挺好,住的用的都挺好。
王庆松:所有的行程都有安排,唯一的要求是不能打工,绝对不能挣钱。不过去哪都有人请你做讲座,讲座不能收费用,但翻译费可以,我老婆可以收,翻译300块钱一场。我觉得这样也可以,挺好的。但待不住呀。你想,第一个月还很新鲜,第二个月天天吃西餐,幸亏每个城市跑,要不一直待在纽约,肯定掰了,估计不到第三个月就直接离了,实在是……(开玩笑)
她待的习惯,她在美国留过学。北京多好,一群难兄难弟。最后很快我就回去了,但是美国转一圈还是收获很大,感觉受到了他们所谓的异乡文化。
谷雨:现在国内的基金一般是资助艺术家去驻留和创作的,你对这方面整体的评价一下。
王庆松:现在肯定是不一样,它更像一个项目。之前基金会管的少,基本不管。现在希望你要来做点什么,能不能在那做件作品,还有非盈利空间做完在这展展怎么样等等。我还去过一次丹麦,需要一个月时间,我待一个星期就受不了了,太难了,我就提前回来了。
现在更多就是创作机会,那个时候更多的是让你去了解文化,站在资本家的角度让第三世界来了解他们,给你吃给你喝,你来了解就行了,不用什么东西回报。因为你也不值钱,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更像救助难民一样。真正去了解还是有用的,我还是更喜欢原来那种感觉,没有压力,想干什么干什么,也可以创作。
谷雨:现在有没有什么其它工作计划?除了拍电影以外,还会再做策展吗?
王庆松:我现在大量时间,是往电影上靠,每天就看碟,耽误了很多时间。策展也很难,但我想还会去做一些,做一些有兴趣的。现在还在谈新的地方,其实我更有兴趣的是湖北,毕竟是自己的家乡。不过要等到我闲下来,我想做的更有意思点,长江当代美术馆是开馆展,要做得热闹,再做肯定是另外的方式去做的。
作者简介
唐晶,1981年生于武汉。2004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雕塑系,2006年就读于德国卡塞尔艺术学院摄影专业,2015年大师生毕业。现为自由摄影师与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