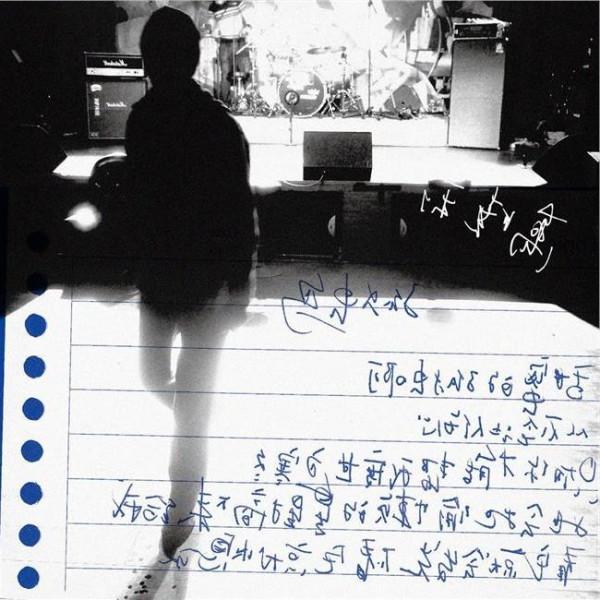摇滚歌手郑钧频现公众视线 为电影宣传开启路演模式
摇滚老将郑钧最近频频出现在公众视线中,不是因为他又出了新专辑,而是因为他用6年做的一部动画电影《摇滚藏獒》。上映在即,郑钧开启了路演模式,“我这一段时间做的这些宣传的事儿,我觉得我这一辈子,为了音乐我从来没做过,有些是打死我我也不会做的。”而说这话的郑钧,已经9年没有再发过新专辑。所幸的是,郑钧还保持着愤怒不吝的摇滚遗风,言谈之中振聋发聩。谈起中国的唱片业,他说,“中国从来就没有过唱片工业,我有过一阵‘唱片农业’”;谈起摇滚的商业化,他说,“现在摇滚歌手一个个儿都穷得跟孙子似的,然后你嫌摇滚圈没有好作品,能有好作品吗?能写出牛逼的歌的人,他为什么要在这儿受穷呢?”;他甚至还把自己给解构了,“摇滚明星是当你成为明星之后,你再去过那个生活,之前那都是给你表演的,没意义,都是编的故事,唱片公司编的故事,别听这个”;谈起参加真人秀,“我跟我儿子吃饭,别人为了看这个付钱给我,我觉得,好神奇啊这个世界!”一、90年代摇滚圈集体在挣扎,但我是一个人在正式成为摇滚歌手之前,郑钧只是一个痴迷摇滚的工科生,在这所典型的工科院校,他有一个同样大名鼎鼎的校友:马云。但90年代的学生郑钧,选择了颇为摇滚的方式终结了自己的学业,“我没有毕业,我退学了,我毕不了业,我一辈子都没毕业”,“因为我想当一个歌手,我想写歌,变成一个音乐人。但是我的环境和条件不具备,我也没机会,然后我继续写,我周围所有的人认为这样不可能。我大学玩乐队的同伴们,最后大家离开大学告别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告诉我,他们都要去工作了,说现实一点,这事儿没戏。大家都笑一笑,啊,老郑一根筋,你非要干这个事儿,我不认识任何一个音乐圈的人,我是一帮工科大学的学生,不认识任何音乐圈的人,你怎么可能混到这个圈呢?”完全置身摇滚圈外的郑钧,凭着对音乐的热爱,开始了“一个人的流浪”,“他们挣扎是他们都在北京挣扎,都在面上挣扎,他们有个圈子,这个圈子在集体挣扎,我是一个人。”肄业后,郑钧回到西安的家,“我去跟那些草台班子演出,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呆着,我在我的宅子挣扎,没有工作、没钱、没有希望,没有任何东西,我也挣扎了好几年。”长年的蛰伏挣扎,其间郑钧产生过自我怀疑,“我也出去找过工作,人家说你谁呀,一看也没文凭,大学自己肄业,退学,也没文凭。你有工作经验吗?也没工作经验。你想应聘什么职位?我问你们销售经理怎么样?人家说出去笑。所以我在别的方向也不适合我,我干不了,我只能干这个和热爱这个。”思虑再三,“另类”的郑钧决定只身奔赴当时的摇滚圣地——北京,出发前,“我哥哥当时跟我说,你去北京要当歌手这个事当成一个协议,两年时间,如果你成了你就成了,如果你没当成歌手,那就把这个事儿忘了吧,到深圳来,找个工作。”郑钧回忆,“那时候深圳最赚钱的是出租汽车司机这种普通工作,给你找个车,你开车当司机吧,这我是真这样准备的。如果两年后我再没机会,我就去深圳当司机了,然后业余时间在酒吧里唱个歌,也挺好。”?二、因为热爱,最可怜的时候也从未自卑来到北京后,“北漂”郑钧经历了人生“最穷的时候”,“我每天弹吉他、写歌,住在人大后门的一个农民房。房东大妈有时候问你干嘛呢?我说写歌呢,她说写歌干嘛呀?喜欢呀!然后自己烧点开水,打点开水回来泡点方便面,继续写歌。”困窘的生活,也没有打消他对音乐孜孜以求的摸索,“我跟草台班子去演出,晚上我乐队的人在台上聊天、看设备,在台上聊天,乐手问我,你干嘛呢?我说写歌呢,他说你写歌干嘛?他说哦,你不用写歌,别人都写好了那么多歌,那么多牛的歌,不用你写了,唱别人的歌就行了。我说我想给我自己写几首歌。他说你自己写的歌谁会听呀,哪有机会被人听到,谁也不会唱。我说我就是想写给自己听,我喜欢这件事我就去写。”不久后,郑钧被当时黑豹乐队的经理人郭传林发掘,随后就签约红星生产社,发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赤裸裸》,“写到有一天,我把这个真的变成唱片了,真的有人听,有人喜欢的时候,那时候我回头看,我一想想,真的就,当年经历的那些事,你回头去看它。我在我当年最可怜的时候,其实我从来没有感到过痛苦,真的,从来没有自卑过,就是那个,我很穷,我穿的鞋是窟窿,裤子都是天然的洞,蓬头垢面的,还跟朋友谈笑风生,还去跟女孩儿混,然后呢,就是,你会觉得你的内心世界有一个自己,有一个非常骄傲的东西在,我在为我自己在干一件我热爱的事儿。”但时至今日,再追怀起来,郑钧仍然觉得“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我很独特。我是觉得,我在干一件我喜欢,我热爱的事儿,我很幸福。但你说那时候,我能不能未来当个歌手,能不能火,能不能挣钱,我真不知道。”他将自己大学时突然逆道而行的举动形容为“冒险和赌博”,“我没有走你们的道路,你去上班,你去干嘛,你走的是别人走了一万遍的路,没意思,我在走一条没人走过的路。我自己想成为一个摇滚歌手,我的路跟崔健成为一个摇滚歌手的路绝对是不一样的,无法复制,这种生活无法复制。”
三、我过不了复杂生活,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挺好玩了近三十年的摇滚,如今49岁的郑钧再谈起摇滚,已经褪去了曾经摇滚青年怀才不遇和落拓不羁的色彩,对他而言,“摇滚乐现在意味着一种生活态度,甚至于我回想起来,从一开始就意味着一种生活态度,就是真实、自由的东西,简单、真实、自由地活着。”郑钧说他“现在过不了复杂的生活,我觉得复杂的生活太可怕了”。在他看来,“做歌手最幸福的一点就是他的生活很简单,写歌,去录音棚里面录音,宣传、演出,他非常单纯,人际关系非常单纯,不需要勾心斗角。我不需要去因为害别人而得到某种利益,这东西也没有这些勾心斗角的东西,没有这种复杂的东西,所以特别简单。歌手是一帮很幸福的人,生活非常单纯。”郑钧也经历过“复杂”的生活,“我以前老是想让事情按照我的想法发生,我要干嘛,我计划明年、后年的事儿全计划好。我去年干多少事,我要挣多少钱,我要做什么事儿,全计划好好的,都是好事,想起来你就会乐,这个计划。计划是你想起来就会高兴,但是它发生了以后你都会哭的事儿,就叫计划。”为了摆脱这种计划与现实的落差,保持“简单和单纯”,现在的他已经不再为规划所累,“别人觉得我不靠谱,因为我没什么特别细的计划,也不怎么担心明天,就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态度,觉得特别好。因为明天你的计划一堆,到时候这个计划实现不了你又失望。所以大概差不多就行了。”然而有时候还是他还是会被现实情况拽着走,比如“最近宣传的生活就是复杂了,我就已经害怕了。”郑钧说的这种“宣传的生活”,就是因经他一手打造的《摇滚藏獒》而起,这部历时6年的动画电影,在上映前迅速将郑钧卷入频繁路演和大规模曝光的生活之中。在《摇滚藏獒》的首映发布会上,郑钧谈及此事苦不堪言,甚至觉得“路演完全违背我自己的天性,因为需要不停地说话,我是不喜欢说话的”,但是又“不想为了自己的个性而影响被受众接受的可能性。”采访中,郑钧也强调,“我这一段时间做的这些宣传的事儿,我觉得我这一辈子,为了音乐我从来没做过,作为歌手的职业生涯里边,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多的宣传,有些是打死我我也不会做的。”四、摇滚歌手都穷得跟孙子似的,能有好作品?2016年,距离崔健在1986年喊出的那声“一无所有”,已经整整过去了30年,摇滚乐也在中国发展了30年,郑钧也从嘶吼着“灰姑娘”的青春代言人变成了众人口中的“摇滚老炮儿”。对于中国摇滚在音乐市场上一直以来的尴尬地位,以及讨论不息的商业化问题,郑钧认为,首先要区分“职业音乐家”和“业余音乐家”两个不同的概念,“你可以以此为生的叫职业音乐家,你可以因为你的音乐赚钱,可以维持你的生活和过得很好的,这是你的工作和职业。音乐爱好者是什么?你就是喜欢这件事,你并不能以此为生,这事没问题,你可以爱好它。你不能说我所有的音乐爱好者,就是摇滚音乐家,然后能以此生活的人他们不是的,他们已经商业了,这是非常愚蠢的一种说法。”郑钧希望“中国的所有摇滚音乐家都变成亿万富翁,那时候的摇滚乐圈子一定会特别牛逼。”“因为当这些人都变成富翁的时候,就会有无数的年轻人觉得,这是一种可能性的,是这样的生活太牛逼了。在美国,你问年轻人,十个里面有八个男孩儿说我的梦想就想当个摇滚歌星Rock star,我就想当,谁都想当Rock star的时候,你会听到无数无比美妙的音乐出来。”因此,当下公众对于摇滚音乐人商业化的苛责,在郑钧看来是毫无道理的,“你现在摇滚歌手一个个儿都穷得跟孙子似的,然后你嫌中国音乐,摇滚音乐圈没有好作品,能有好作品吗?能写出牛逼的歌的人,他为什么要在这儿受穷呢?这个时代跟六十年代是不一样的,他有这个才华,他分分钟可以去写一个小说,写一个电影剧本,他的生活没有任何问题。他为什么要干这个?职业,我所说的是以摇滚音乐,以这个音乐为职业的职业音乐人,他为什么要以此为职业?连活都活不下去!”他觉得中国的摇滚圈存在一个“巨大的误会”,“认为摇滚音乐人可以不吃不喝,我就当神仙,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真的热爱这件事的话,你可以找个职业,赚着钱养活自己和老婆孩子,业余时间你可以玩乐队,继续写歌,你去创作,然后去卖你的歌。如果火到一定程度,你可以拿这个钱养活老婆孩子,你可以把那个工作辞掉,这是我认为现实一点的。美国人是这么干的,中国人给我的印象完全是一个误会。我玩摇滚了,从此啥也不干,每天有大把的时间在那儿抽着烟聊天,也不创作,也不干别的,然后就抱怨,就是说为什么我的歌不火,为什么他们都,这个社会完全这个,音乐摇滚圈是太可怜了,我不被重视。我觉得首先的问题是这个问题。”郑钧甚至觉得,“我的故事都有点误导别人,我的故事、别人的故事,都有点误导后来的音乐人,觉得我既然这么热爱摇滚乐,啥也不干了,就干这个事儿。你如果能从早到晚写歌,排练的话,我觉得你干这个,有才华,我觉得你也很牛。但是你不能就写俩小时歌之后,剩下的时间就开始一帮哥们儿开始聊了,你就开始玩摇滚明星的生活,那是错的。摇滚明星是当你成为明星之后,你再去过那个生活,之前那都是给你表演的,没意义,都是编的故事,唱片公司编的故事,别听这个。”说起这些,郑钧显得有些激动。
五、中国从未有唱片工业,只有过唱片农业在中国公众的认知里,摇滚乐更多地意味着主流之外的一种的音乐类型,天然地为小众所追捧,而对西方音乐了然于胸的郑钧,有着不同的见地,“在西方,美国和欧洲,摇滚是一个极其主流的文化。你在美国,为什么我说这个,我公司里面那些员工,那些画画儿的漫画师,个个都有乐队,个个都出唱片,你会觉得这个群众基础太大了。”摇滚之所以在中国有如此境遇,“说实在的,我是觉得大家都有责任,你不能光怪听众,大家都有责任。如果你成批的优秀作品不停地冒出来,一个唱片工业的标准是每年至少要有十张以上极其优秀的唱片产生,才会产生,算作一个小唱片工业,我哪有?”郑钧郑重其事地分析道。而延伸开来谈及中国的唱片业,郑钧更是义正辞严,“中国从来就没有过唱片工业,我有过一阵‘唱片农业’”,他解释称,“唱片农业文明我有过,我有过唱片‘封建社会’,我曾经经历过,现在也过去了,现在就没了。但是音乐从来没有衰亡过,我觉得唱片工业的行业,是因为原来的唱片工业体系崩溃了,但是音乐,对音乐的需求和热爱从来没有崩溃过,这是两个事。”虽然一直被当做摇滚老将,但郑钧很不喜欢将个体类型化,“说这一帮他们玩儿摇滚的,这一帮玩儿流行的,这是玩嘻哈的。或者这是西安人、北京人、河南人,这种划分没有特别,或者这一帮是天蝎座的,这一帮是巨蟹座的,这种划分是你可以作为娱乐的那种,但是它没有实际的意义”“摇滚圈子这么多人,他们会一样吗?他们会不一样。所以这才是他们的魅力,老崔、黑豹我觉得都很喜欢他们,但是都不一样,他们之间也不一样,我跟他们也不一样。个人有个人的原则和做事风格,我自己的喜好。所以你自己高兴就好,我觉得重要的是,每个人,像老崔是我大学的偶像,我真的希望他,他是按他的思路走就行了,他想写什么音乐写什么音乐,我听得懂觉得好,听不懂,他高兴就好,就是这样。”[星态度]郑钧:摇滚歌手穷得像孙子 能出好歌?六、我不理解真人秀但觉得带孩子有人付钱给我很神奇从2007年的专辑《长安长安》后,9年来,除了零星发过几首单曲,郑钧再未推出新的音乐专辑。但在音乐领域之外,他创作漫画、担任歌唱比赛评委、综艺节目导师,去年甚至也投身真人秀洪流,带着儿子一起参加亲子类节目,到如今,他又拿出了耗时6年制作的动画电影,看起来,歌手郑钧似乎离摇滚、离音乐越来越远,转而变成一个全能型艺人。采访中,聊及此事,郑钧都已经记不清自己多久没出过新专辑了,他询问助理,“《长安长安》之后是什么?2007年之后我没出专辑?”“我的心太大了,确实,我以为我出了。出单曲了,对对,出单曲了。”对于自己的“不务正业”,郑钧并不讳言,“说实在的,我从小有一个特点,就是我特别不爱活在别人的期待里面,我不愿意活在别人的期待里面。别人觉得你,老郑是一个我很喜欢的摇滚歌手,你应该过成我想象的一样,那样过的生活,你要不食人间烟火,很牛逼的这种姿态得有。但是我觉得,我为了他们活在那个姿态里面,太没意思。人生很短暂,我想看看还有别的活法没有。”其中让粉丝最不能接受的“别的活法”,就是这位华语摇滚的扛鼎人物,竟然在真人秀的镜头里带孩子,他需要面对无数育子难题和琐碎日常,与往常人们印象里洒脱不吝的摇滚歌星形象大相径庭。可郑钧不在乎这些,“我去上真人秀,我觉得这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你不能让我停留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生活状态之中,这个时代有无数的新东西,互联网是太神奇的一个东西。”让郑钧觉得神奇的还在于,“我跟我儿子吃饭,别人为了看这个付钱给我,我觉得,好神奇啊这个世界。你要问我对真人秀什么感觉,我觉得真人秀真是个理解不了的一件事。我在那就吃饭、玩儿,我陪他,看孩子,给孩子洗澡,有人给我付钱,很多钱。我觉得,好神奇的事儿。”所以,其实郑钧也不理解真人秀的消费模式和存在形态,他只知道,如果你不想看,“可以不看,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可以不看。就跟鲍勃迪伦似的,鲍勃迪伦那时候写一个反战歌曲,然后大家觉得他是牛逼的反战大师,各种抗议之声,鲍勃迪伦你得站在前面,你得是我的代言人。鲍勃迪伦说我从来不是任何人的代言,我是我的代言人。我就是一个,我是个职业歌手,我写歌的,别让我干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我还有老婆孩子,我要过我的生活。列侬也是这样的人。”“所以记住一点就是,没有人是神,再牛逼的人,也要拉屎。你说你的偶像拉屎你受不了,他也得拉,要不然他受不了”,说完,郑钧自己也开怀大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