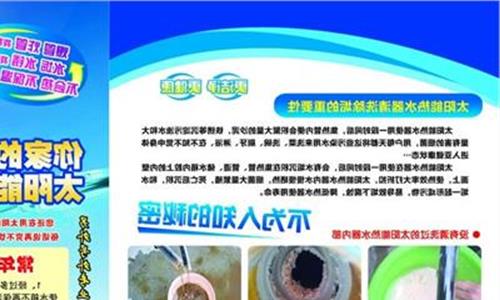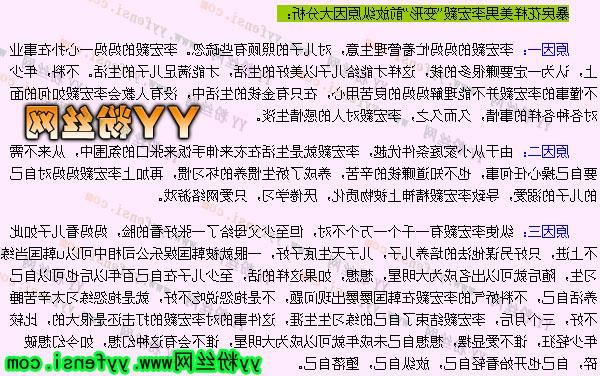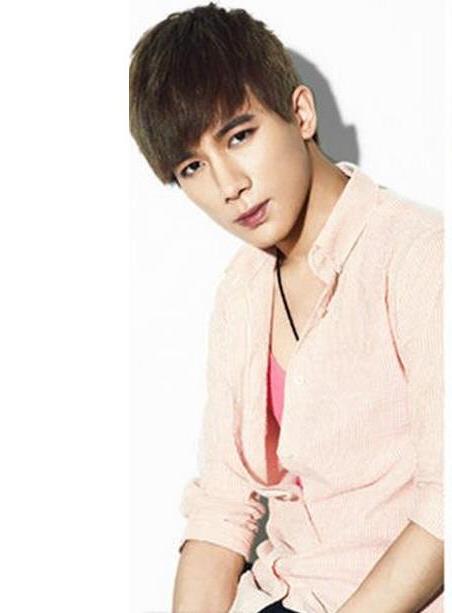李铁锤李明霖 李铁锤:消失的村庄文明
城市那些把白发烫成波浪的雄性教授那些于大妈一样的雌性教授,他们说:乡下的村庄,它的传统文明在渐行渐远。这一点,留在村庄的人还是候鸟一样回来又走的人,都感受到了,他们自己说不上乡下传统的文明是什么样子,可他们承认,自己的村庄与过去越来越不一样了。
我也不知道乡下的传统文明是什么,但我能感受到他们认为文明的东西在村庄里一件一件在减少,这样说一点也不怪诞,“文明”这东西在中国就像“文化”,它被滥用后好像什么都是文化,又好像什么都称不上文化,可这不影响人们开口闭口说文化,虽然很多人根本掰扯不清什么是文化,虽然连内地的大学也几乎找不到文化。
一、消失的森林、土路、村落
村庄文明的消失,从它的毛发、衣着开始,它的毛发、衣着渐渐变了。有些村庄,村庄的森林像有些人的头发,快速地稀疏,最后光秃。直到村子里头残留的最后几棵古树也消失了,它们在村民与“树贩子”之间像清朝与洋人一样的交易中,被挖掉或砍掉运出村庄,有些村庄,一户一户无声的撤离,灌木野草无声的入侵,村庄成了灌木荒草的营寨,撤离中,人们砍掉了那些古老的大树,残败的村庄像胡子拉碴的醉酒汉子,不成样子地卧在那里,没人理会。
九十年代前的田野,只有两样东西,田地里长着庄稼,田埂上长着野草、灌木,那时候的土路,路边有自然而生的古树,拐弯宽敞处有前人栽下的大树,路边的古井旁,没有树的话,也是青翠的草,那个时候走在春天的田野,只能看到青的草、绿的树,黄的土,人的眼睛很舒服,田野与路很宁静。
九十年代前的村庄房屋,都远远地退让在山下,对农田怀着千年来的尊重,各自秩序井然。那个时候,走在土路上的人,看看路边的古树,看看田野那边古树下的村庄,在小桥流水的声音中,会有文明古国的感觉。
现在,乡下古老的土路很多不见了,充满乡村乌托邦美丽理想的村村通工程,在它的款项被层层克扣消减以后,乡下的水泥路就像山东煎饼,薄如蝉翼,那些修路的人,怎么就不知道珍惜,这可是在修他们自己那片土地上的路。
他们砍掉路边的树,他们随意把土路截断,再马虎地粘连在一起,上面铺着劣质的水泥,一些暴发的农民,不把重型卡车停在村外,几步远的路,非要炫耀式的把卡车开进开出,这路就像恶狼的嘴,到处呲牙咧嘴,丑陋不堪。
路不再是原来的土路,也不是玲珑精致的水泥路,四不像的路边的树不见了,房屋也不再与田地保持着矜持恭敬的距离,生活在它上面的人,抛荒了大片的土地,还炫耀着对土地的鄙夷与嫌弃,把刺眼的小楼房杂乱无章地盖在村庄最显眼的田地上。
村庄的文明开始从它的外形上渐渐消失了。
二、石磨、石杵、榨油坊
在我少年的时候,村东头那两棵古树下还有一个石磨, 2个巨大的石碾,一个石杵,它们歪斜的一半躺在地面,一半插在土里,半阴半阳地显示着它们存在的古老。
石磨的直径我那时估计过,有2米多长。后来到城市,我看到城市宾馆那个2米的粉红色圆形床,我会想到村东头这个外形一样大的石磨。这时,联想成性的我还会流氓地幻影出城市人把床弄成情趣的圆形与暧昧的色彩,然后在上面那个的情形,接着,我的脑袋里会幻影出乡下的村妇围着那个古老的石磨牲口一样打转的情形,破棉袄,旧棉裤,棉裤口上用旧布条紧扎着,这种装束让八国联军打到中国时,得出中国女人是世上最丑陋女人的结论。
小时候看到这个石磨,我想得最多的就是古代人就是食量大,用这么大的磨盘磨粮食,我还会联想,古代我们村庄一定是粮食丰盈,才需要这么大的石磨来碾碎一个村庄的粮食。
少年后,路过这个石磨,我会想到这个石磨不仅仅是磨粮食的,它还是个文物,用现在城市学者的看法,它们就是乡村的传统文明了。我甚至还想把它弄到我家的院子里,我活着的时候躺上面纳凉,我死了后,它就是我留给后代的值钱文物了。
可偶尔一次听到大人说,它们是大食堂的时候村里请石匠凿的,说是全村一起吃饭了,共产主义了,村里需要一个大石磨,至于多大为好,队长说尽能力凿吧。这是不是真的,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敢问,那时候的乡下,社会不流行疑问,小孩子随便向大人乱问,也就是忌讳了。于是,我总在问与不敢问之间摇摆,这几个石东西也就在到底是文物还是石头之间摇摆了很多年。
直到后来,也不知道哪一天,它们不见了,再以后的某一天,我无意间发现它们砌在李家二杆子的院墙下,我说这是文物呢,二杆子说:球,五八年凿的东西是鸡巴的文物。
村西头的稻场边,有个后来一直在使用的石杵,我在少年时,还经常随母亲去那里捣东西。这东西由三部分组成:一个中间被凿成光滑半圆型空心的花岗岩大石头,把开口向上埋在地上,一个几十斤的花岗岩石棒,在上面凿一个方形的大洞,把一个结实的方形木一头穿进去,再铆紧,方形木七分之三的地方再凿一个方形洞,中间穿一个棒子,棒子两端支在两边的木墩上,在另一方的地面上再掏一个槽子,之后,人就可以用脚去踩方形木的一头,方形木有石棒的另一头会高高翘起,脚一松,那石棒一头就狠狠砸在半圆型石碾子里面的东西上。
“嗵哧、嗵哧”的声音逐渐沉闷下去的时候,那杵里的东西就被捣成粉末了。
小时候,冬天里,男人、年轻一点的女人每年候鸟一样去很远的地方做徭役去了,现在的水库、盘山的沟渠、国道的前身基本都是他们无偿徭役的结果。他们走后的村庄冷清,表面安详,里面忧伤。现在城里研究留守儿童的教授肯定不知道,那个时候其实就有了留守儿童。
留在村庄的妇女会在空闲的午后,有月光的夜晚把糯米背到这里,放在里面捣成面粉,把收获的豆子拿来捣碎,再背回家烙成饼子晒干,在冬天不长蔬菜的季节,村妇女们会把炒熟的黄豆拿来,与辣椒一起捣碎,回家拌上盐和水,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唯一的下饭菜。
这个石杵给我留下了印象,还在于石杵前面的一家人,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发现石杵前面的几间土墙屋里面黑洞洞的没人住,后来知道里面的一家五口人,孩子都在半成年的时候,一个个得怪病夭折,最后只剩下大妈一个人了,忧伤过度的大妈眼睛一日一日的模糊,我小时候见过她几次,坐在她侄子的门洞前,眼睛已经看不见东西了。
村里人说,都怪队里不该把他家门前的院子当成打谷场,在我们那里,迷信的说法是打谷场上的房子住不得,门前与堂屋齐平的院子更不能做成打谷场,否则会家门不幸,人丁夭亡。大妈的丈夫是地主,当时,把他家门前开辟成队里的打谷场,这种明显欺负人的做法,有让人有理说不出的阴毒,为了孩子,地主成分的大妈丈夫还是愤怒的抗议,这个抗议的男人立即被扣上在社会主义还相信封建迷信的帽子,整斗。
抗议无用后,不久,大妈的丈夫就去世了,最后,真应验了,最后大妈一家人都不在了,比我一样大的孩子他们基本都不知道我们村庄西头的打谷场上曾有过一家人,他们曾经共有五口。因为他们没有我敏感,我也只是知道得支离破碎,因为我不敢追问。
那个榨油坊,在西山对面的半山坡上,三间黄土墙的屋,屋的两头有高大的松树,屋后有清冽的沟渠,在每年的四月里,大山深处水库里的水开始放闸,沟渠里就有冰凉清澈的水流过。这个时候,榨油坊也开始榨油了。
我们要到达那里,中间隔着一片很宽阔的起伏田野,在这个田野里,一条泛黄的土路延伸在两个天际深处,把梯田分成上下两半,我在西山放牛时,往山下俯视,总能看到这条路,看到这条路,我会想起父亲讲到的那个在这条路上栽倒饿死的少年。
山下的田野属于另一个公社,不是一个公社就有老死不相往来的忌讳,像是两个国家了,我们也就从来没有过去,虽然只是十几分钟的脚程,虽然我们很想去看看那个榨油坊,顺便偷偷舀一勺子香油喝,偷偷掰一块榨油后的饼子或者芝麻藏在衣服里偷出来。
在一个晚春里,我终于尾随着大人进入了这个榨油坊,秋天金色的阳光从透明瓦照进来,投射到那个黑乎乎的巨大榨槽木上,还有古色古香的油锤,映衬着金黄色的光柱,人就有进入古老岁月的感觉。
这个榨油坊哪一天消失的,榨油的师傅知道,我却不知道,我现在知道的,是找遍整个西山,也找不出一棵可以做榨槽木的古树了,榨槽木必须是一根独体的圆木,笔直的躯干必须5米以上,直径必须有一米,这样才能在它的中间,挖出一个2米长,40公分宽的油槽。顺便说一下,这种树必须是木质坚硬的沉木,要长三百年以上。
在快节奏的喧嚣城市生活中,我偶尔会想起榨油坊,想起那种七分榨油,二分打发岁月,一分红尘之外岁月宁静的从容。
我也悟到那种原始的榨油方式,它是人类对大自然无意识而达到的有意识尊重,它还是一种最科学的人类生存方式,古老有啥?原始有啥?现代技术放出了沉睡在地底的恶魔,这个恶魔异化了人与自然不紧不慢的和谐相处,人类变得浮躁不安,技术崇拜下的欲望无穷让这个地球七孔冒烟,生态再也走不回原来的样子。
三、舞狮、乡戏、乡下的魔术
很多事,人真应该在它们来的时候,在它们消失的时候,拿个本子记下来,做这点事其实不费力,但人就是不做,等到回忆的时候,人们才发现,很多往事想起来,有那么回事,但就是不知道它们发生在哪一年,又在哪一年消失的,还有它们原来的具体样子是怎样的。
乡下的舞狮、社戏,还有乡下的魔术、货郎担子……,它们都在乡下存在过,它们也都渐渐稀疏,消失,只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在偶然唏嘘的回忆感叹中,后来的人,才模模糊糊知道他们的村庄,真的像书中谈到的那样悠然古老。
小时候,乡下的舞狮在每年的春节准时来到我的村庄,它不会遗漏每一户人家,除非这一户人家故意把门锁上,乡下的农户,穷到确实连最便宜的“大公鸡”、“黄金叶”香烟都拿不出两包时,他们就会把门锁上,大人不知道躲到哪里叹息去了,他们不懂事的孩子会跟着玩狮子的,从一家走向另一家,感受乡下少有的喜庆热闹。
城市的舞狮,不是我说它,它永远舞不出我家乡那个狮子的神,也舞不出对行当的敬,我在城市背着几岁的小女儿看了几次后,我叹息我女儿一样的孩子,我想:等他们长大后,他们会说他们小时候看过很多这样的东西,其实他们哪里真正看过呢。
举狮头的大哥是山那边村庄的,狮子来到村庄的锣鼓声一响,人们就拿出鞭炮、香烟,那时候不给钱,给点香烟、点心,图个热闹。
想逗狮子的人,会把廉价的烟,系在大门前丈把高的房梁上,或者搭梯子塞进梁洞里,总之是越高越好,越难拿越好,等那狮子来拿,舞狮子的大哥总能拿到,如果哪个愣头青故意把香烟吊在两个人搭人梯都够不着的高度,就会遭来年长者一声呵斥,愣头青就会顺从地把香烟吊在适合的高度。
这个时候,那个狮子就会蹲下来,然后“倏地”一下子站起来,举狮头的大哥就稳稳地站在舞狮尾巴那个人的肩上,大哥再舞动狮子的大嘴,故意笨拙地用狮子嘴巴去咬那吊在梁上的香烟,逗出一院子快乐的笑声,等大家都高兴了,狮子就会敏捷地一口咬掉香烟,大哥这时候轻捷的一跳,再一个翻滚,舞尾巴的人完美配合,一个矫健活泼幽默的狮子就出来了。
每一个村庄都舍不得狮子很快地离去,它们挽留的方式很奇特,在村子前的空地上,村里人会在空地上叠罗汉搭一样叠上依次大小的四张桌子,有时会是五张桌子,在每一层桌子上,放上东西,让那狮子吃,狮子最后要登上最上面的那个桌子上,再做一点威猛、滑稽、矫健的表情,还有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