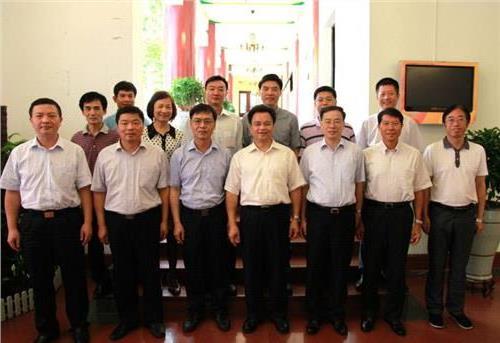童庆炳王一川 王一川忆童庆炳先生:我一生的“人师”走了
童先生对待周围同行、同事和弟子,总是有着温润如玉的品格,给人以持久而温馨的感动。人们都知道,他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作为总导师与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何镇邦先生等联合带出了莫言、刘震云、余华、毕淑敏、迟子建、刘恪等硕士作家,他们早已成为我国文坛的中流砥柱了,这一点已无需由我来说。
我这里要说的只是,这批早已功成名就的作家,多年以后仍然会念念不忘当年的恩师。诺贝尔奖获得者莫言说:“我记得童老师在讲授‘形式情感与内容情感的互相冲突和征服’时,曾经举俄国作家蒲宁的小说《轻轻的呼吸》为例,来说明文学的内容和文学的形式之间的对抗所产生的审美愉悦。
当时我就很兴奋,似乎感受到了一种伟大的东西,但朦朦胧胧,很难表述清楚。
十几年来我经常地回忆起这堂课,经常地想起蒲宁这篇小说,每次想起来就产生一种跃跃欲试的创作冲动。”余华写道,童老师的课吸引人的有两点:一是“平等待人”的“教学风度”,二是“清晰的思辨和独特的感受相结合”的“学术风格”。
那时正在卫生所所长职位与专业作家两条路之间徘徊的毕淑敏,则从这“流光溢彩,闪烁着湿润高贵的人性光芒”的讲课中获得宝贵的启迪:“童老师的课程,在我这一学生的人生道路选择和转变的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我看到了一位杰出的文艺理论家的风度和修行,我被他对文学的执著和献身所激励。他使我感到了文学的美丽和魅力,使我在学习的过程中,渐渐地充实和自信。”迟子建则如此记录童老师给她的印象:“认真、洁净、儒雅、温和。
”如今已是知名小说家与文艺理论家的刘恪,曾这样写道:“他学识渊博而深入浅出,讲述流畅而不急切,精细而不繁琐,理性而不艰涩,论点阐释必结合实例分析,追根溯源之后又有抽象的提升。
那虽然是理论课他却有许多亲切的比喻,他的声音发散于四壁回旋于静空,在我们的心里形成共振。”(以上引文均引自童庆炳《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学》,序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9-15页)作家们的生花妙笔,是先生温润人格的最好素描了。
我多年前曾带过一名博士生,其性格天真、单纯、活泼,始终有颗童心在,因感觉童先生和蔼可亲,没有架子,似乎什么难题都能帮助解决,所以一有问题就总是去找童先生聊天,可谓“童言无忌”。我的其他博士生都懂得童先生有太多事务要办,不该花时间去麻烦他,有的还劝告别去。
但这名博士生却不然,一有事,无论早晚,就天真地直接电话过去或者径自闯到他家里。不管有多忙,童先生都总是放下手中活,耐心地接待和开导,细心化解其心结,直到后者喜滋滋地出门而去。毕业以后多年,这种情形还延续着,直到前不久又到先生家里如沐春风。连我都有一段时间不敢轻易打搅先生了,但这位学生却有此令人们好生羡慕的福分!
我知道(但我那学生未必知道),这主要是因为,正像童先生自己的姓氏所蕴含的意义那样,他在其文艺美学思想中一直推崇李卓吾等的“童心”说,教导我们,研究文艺理论和美学的人应当懂得尊重童心,始终葆有一颗童真之心,因为这正是维护人性和研修美学的必修法门之一。
同时,他也深谙“有教无类”之道,对各种学生都一律来者不拒地循循善诱,助他们成人成才。他把这些不仅用于文艺思想建树中,而且更用于自己的日常待人接物中,可谓内心为学与为人的内在统一性人格的闪光。
挺拔如松
当然,如果仅有温润如玉的一面,那未必就是多样而又完整的童先生人格。由于身为中国高校第一批文艺学博士点的第二代掌门人,他难免会身不由己地处在激烈的学术争鸣漩涡中。每当遭遇来自内部或外部的误解或打击时,先生则显示了另一种秉性——挺拔如松的人格操守。
我曾经多次目睹,他如何在一些人的无端批评和指责中,坚守自己的信念,坚持自己的清白品质,决不向那些诬陷和攻击低头。也就是在那些年,他由于调动极大的身心力量去加以抵御,不料逐渐患上了糖尿病和失眠等多种病症。
更加严峻的是,他因自己的这种坚守和顽强抵御,在一段时间里逐一失去了不少原来已有的显赫的机构位置。但他绝不因此而后悔、后退一步,相反,他坚持默然治学、教书。在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里,他带领我们这些年轻人埋头学术,默然耕耘,直到终究赢得了学界的美誉,也为他后来一生的学术盛誉奠定了厚实的学脉与人缘。
通达如桥
童先生在学术上通达开明,善于包容不同的见解,是学界素来称道的。用他自己在《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一书中的主张来说,就是要修建一所学术“立交桥”,让来自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外国的种种不同的文艺理论主张,都在这里共存、汇通、化合,而中国学人就应当以自己的主见去加以批判地吸纳。
他时常嘱咐我们,对外来的新思想、新观念,没有什么可怕的,千万不要视若洪水猛兽而“御敌于国门之外”,而关键就是开放而有自己的主见,容纳新知而又有消化之功。我觉得,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点之所以多年来长盛不衰,就是由于坚定地遵循了童先生的这条学术秘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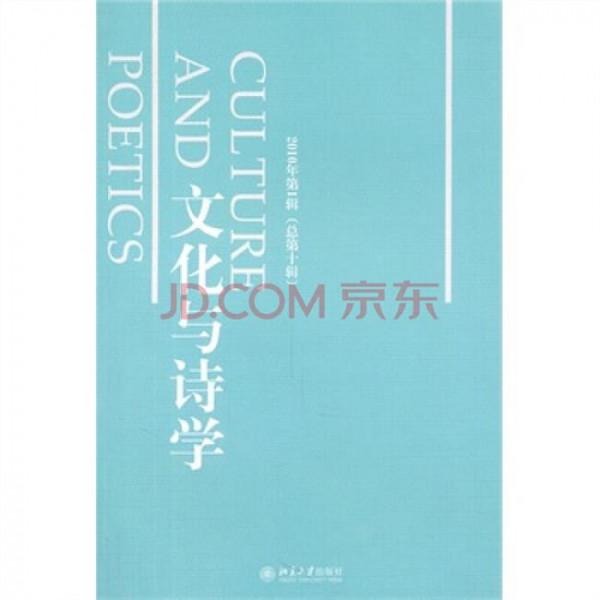


















![>[王夫之与王阳明]王安娜与王炳南之子王黎明于70年代赴德与母亲团聚](https://pic.bilezu.com/upload/5/e2/5e2593ff0a41ed956b7d76004b17d6e2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