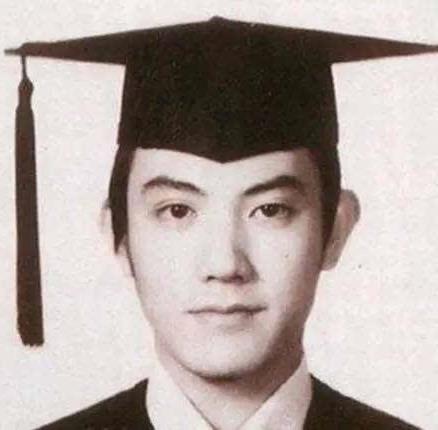马戎回族 马戎 用中华民族观念研究民族问题
文︱本刊记者 李肖含 茉莉园小区位于京城西北郊的百望山附近,距离北京市中心约30公里。较之喧闹的市区,这里的环境幽静,空气也格外新鲜。 马戎先生一身休闲服,在房间里踱着步。或许是因为起得太早,他看起来仍有些疲惫。
由于长期高强度的工作,他的脸上一副沧桑模样,头发也开始显出灰白的颜色。他出生于1950年,已过花甲之龄。 但这位长年致力于民族社会学研究的社会学家,仍然对新闻时事保持了习惯性的关注。“呼格吉勒图案轰动全国,但你有没有注意到,呼格吉勒图的父母都是汉族人的姓名?”他说,“到了呼格吉勒图出生的年代,一些蒙古族民众才开始又给孩子起蒙古名字,这其实正反映出上世纪50年代边疆地区各民族一度融合的态势以及文革后出现的微妙变化。
” 去年以来,新疆地区陆续发生了数起暴力恐怖事件,马戎对此不无忧虑:“必须承认,我们的民族工作遇到了新的现实问题和严峻挑战,如何有效地应对,考验的是我们的智慧与能力。” 曾在内蒙古锡盟草原上插队5年,1985年开始从事民族社会学田野调查与专题研究,马戎很早就开始对中国的民族问题进行反思。
从2000年开始,马戎写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了民族关系“文化化”及“去政治化”的建议。国内学术界关于民族理论问题的讨论逐渐开始活跃。
他的这些观点得到不少人的赞同,也受到一些人的批评。马戎说,民族社会学研究是最讲究客观事实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有不唯书、不唯上,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在国内外形势的快速变化中与时俱进,推进理论创新,切实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
不久前,马戎写了一篇长文对新近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座谈会的精神进行解读。“这次会议非常重要,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既有宏观的理论框架,又涉及当前民族工作中必须关注的许多具体问题。
”马戎说,“很显然,中央领导已经注意到我国的民族关系在21世纪出现了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 从北京到草原 马戎是回族,1950年出生于辽宁沈阳,父母都是七七事变之前参加革命的国家干部。
6岁之前,他一直随父母在东北地区生活。1956年,父母工作调动,他也一起到了北京。7岁开始上小学,他对当时的“红色教育”印象深刻。在那个时代,孩子们读毛选,学雷锋,参加各种社会劳动,一心要做毛主席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小学四年级时,他转到了北京景山学校就读。当时的景山学校是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下的一所实验学校,在教学及管理方面都与其他普通学校有不少差别。
夏收和秋收农忙时节,初一以上的学生都要到郊区参加劳动锻炼。马戎记得,他连续几年到京郊的金盏公社劳动,割麦子、掰棒子,学生们吃住都在农民家里,平时还帮助房东挑水、推磨、扫院子。 1966年,“文革”爆发,马戎刚刚16岁。
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说法,马戎认为这是“出身论”,因为每个人的家庭是无法选择的,但个人的人生道路却是可以选择的。 1968年8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马戎和一批同学自愿报名去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沙麦公社插队。
当时他刚满18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他怀着“向贫下中牧学习,扎根建设边疆”的伟大理想,决心在内蒙古草原上扎根一辈子。
草原上的牧民们对这些“毛主席派来的知识青年”非常欢迎,马戎和同伴们也陆续分到了自己的蒙古包和畜群。慢慢地,他们开始对方圆几百里内的草场、水源和道路熟悉起来,并学会了接羔、剪毛、抓膘等技能。
与牧民们的朝夕相处,让他们学会了带有锡盟口音的蒙古语,有的甚至还锻炼出了相当可观的酒量。 这时候的马戎和他的同伴们,在日常的生活习惯上已经和当地的牧民没有任何区别了。刚到草原时“建设草原,改造边疆”的口号言犹在耳,只是没想到,他自己却被草原改造并逐步融入了草原。
到草原上插队的第五个年头,全国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马戎来到内蒙古农牧学院农业机械系学习农机设计。毕业后,根据当时农业院校“公社来公社去”的原则,他到内蒙古镶黄旗牧业机械厂做了一名技术员。
接下来,“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开始陆续返城。马戎也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北京,进入交通部公路规划设计院从事全国公路规划调查。
“心情正与顾老当年相似”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正式结束了十余年混乱与徘徊的局面,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此时正在公路规划设计院做技术员的马戎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人生中的一个新时代也即将到来。
1979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马列研究所开始招收硕士生,马戎报考了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开始学习马列经典著作和英语。后来开始“清理精神污染”,许多他感兴趣的研究专题成为“禁区”。
这让他很想了解一下西方国家的学者们是如何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1982年,他获得了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奖学金,到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系继续深造,学习的专业也换成了社会学。 那时候国门初开,中国大陆地区到美国留学的学生还很少,马戎是其中为数不多的文科博士之一。
1987年3月,马戎学成归国,进入由费孝通先生主持的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工作,并随即参加了该研究所在内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区的一系列社会调查活动。
早在1985年,还在美国布朗大学深造的马戎为了撰写博士论文,曾到内蒙古赤峰地区开展了问卷调查。他对那时各民族群众之间融洽的民族关系记忆犹新:每到一户牧民家中,对方都会热情招待,大家一起闲话家常,亲如一家。
他感觉,那时内蒙古农牧区基本上不存在什么“民族”矛盾。人们之间相处,看的主要是对方这个“人”,而不是他的“民族成分”。 而在美国学习的几年间,马戎感到同时期的美国尽管在种族问题上还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但与六七十年代出现激烈种族冲突的“民权运动”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各族裔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经济、文化方面,同时黑人和各少数族群对美利坚民族和国家的政治认同有所加强,现在出现的一些少数族裔的抗议活动,针对的不是政治制度和政府,而是警察和一些部门的具体做法,要求的是切实落实美国宪法,实现平等和公正。
”马戎说,这促使他开始对中国现行的民族政策进行反思。 1950年代初期,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在新中国享有极高的威望,我国的民族理论与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苏联的经验。
当时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建立区域自治制度和对少数民族实施的各种优惠政策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后,为什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的民族关系却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国内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别主要是政治认同还是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上的?当下的民族理论和政策是否需要根据社会发展中的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创新与调整? 1939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艰难时刻,帝国主义国家在建立“伪满洲国”后,又策动内蒙、新疆、西藏等地的少数民族地方势力发起独立运动,妄图以此分裂中国,削弱中国的力量。
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怀着满腔激愤写下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著名文章,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中国境内的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虽存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同属一个中华民族。
“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国内民族地区的某些情况与1939年有些相似,”马戎说,“而我的心情则正与当年的顾颉刚先生相似。” “从文化角度来看民族关系”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国际环境的急剧变化,我国的民族关系也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主要的工作,各民族间原有的意识形态认同基础(共产主义理想、无产阶级革命等)大大减弱,而汉族与少数民族在历史、语言、宗教、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多种差异开始凸显,经济发展的差距也不断拉大。
“涉及少数民族的许多社会问题也开始被从‘民族’的角度来解读,”马戎说,“民族身份变成了最重要的身份认同。” 而与此同时,国内学术界关于民族和民族政策的讨论也开始逐渐活跃。
2011年,中国的两位知名学者——胡鞍钢与胡联合共同在《新疆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了《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的文章,在海外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胡鞍钢与胡联合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应当“实现从识别国内56个民族、保持56个民族团结发展的第一代民族政策,到推动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促进中华民族繁荣一体发展和伟大复兴的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转变,建构起凝聚力越来越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你我、永不分离的中华民族的繁荣共同体”。
这些主张与马戎此前提出的民族关系“去政治化”的观点有颇多相似之处。早在2000年,马戎就提出应当“主要从文化的角度和层面来看待族群(民族)问题,而不要把我国的民族问题‘政治化’”,并建议进行话语调整,即“保持‘中华民族’的称呼不变,以便与英文的‘nation’相对应,而把56个民族改称‘族群’,以与英文的‘ethnic groups’相对应”。
但马戎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也绝对不能只强调“一体”而不重视“多元”,必须坚持民族平等和相互尊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仍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同时,民族与区域之间的关系应当逐步淡化。
对于各部分公民(当然包括少数民族成员)权利的保障机制将逐步从地方性行政机构的运作向全国性法制体制的运作过渡。 马戎的说法引来了不少争议。他的一位批评者认为,民族问题也罢,族群问题也罢,是多民族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
其表现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难以对其作出抽象的‘政治化’或‘文化化’认定。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提法,从理论上讲站不住,在实践中既做不到,也不能这样做。
因为绝大多数民族问题都不可能不借助于国家力量和民族政策等政治平台去加以解决。 “我提出民族政策去‘政治化’的建议当然并不是否认民族政策的政治性,”马戎说,“事实上,我是想把我国民族问题的改善和解决导入一个具有现代发展方向的轨道,让民族政策真正成为保障各族公民的文化、经济和社会权益的工具。
” “比如,长期以来实行的少数民族考生高考加分政策,就不如改为在现代社会更加公平的按区域加分的方式。”马戎说。
“前不久结束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指出新中国成立65年来,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正确性的同时,也提出要‘开拓创新,从实际出发’,借鉴国外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马戎说,“我相信接下来,中央政府在民族工作的努力方向和具体做法上将会有一些调整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