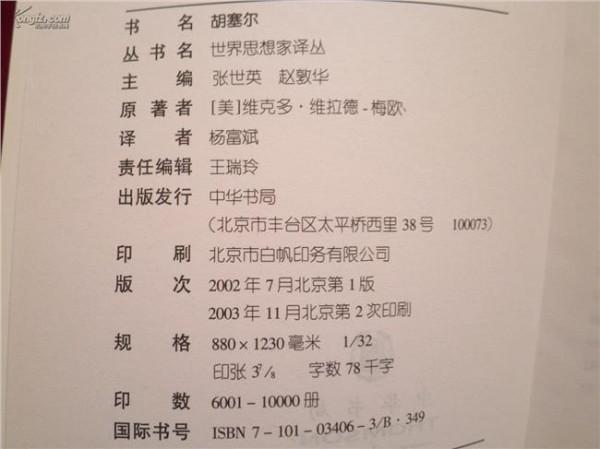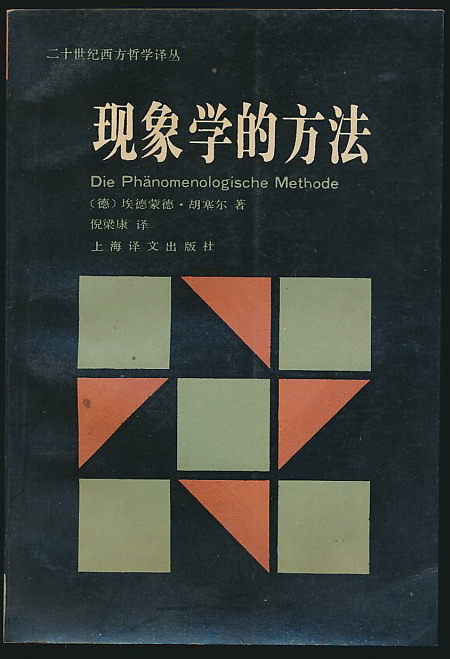胡塞尔触发 叶秀山:胡塞尔先验现象学对欧洲哲学发展的贡献(二)
原标题:叶秀山:胡塞尔先验现象学对欧洲哲学发展的贡献(二)
四、“人文科学”作为“自由”的“科学知识”
在康德第三批判里的“自由”已经不是第二批判里那个空无“内容”的“绝对命令”,也并无“道德律令”的“强制性”,而或是一种“有(感性)内容”的“(理智)游戏”(审美),或是为“自然一感性”“世界”在“理智上”“彻底”的“可以理解”的“无目的的目的性”“推定”。
这两种理性的态度都是“彻底自足”的“自由判断”,不以“预设”一个“外在世界”作为“矫正”的“基准”,“美”不“设定”“外在客观”“有”一个“美”的“属性”,“目的”也不“设定”“外在自然世界”“有”一个“目的”,而是将这种“世界”“内化”为“主体”的“内在”的“独立”“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体现出一种“主体”的“独立自由”,“审美”的“无功利性”与“目的论”的“无目的性”,都意味着是就“悬搁”一个“外在”的“基准”而言的,是把那个在“理论理性”“设定-推定”的“不言而喻”“存在”的“条件”“悬搁”而又“吸收”进来加以“自由”“创造”的成果。
“审美”与“目的”都不是“给予”“自然一客观”“世界”以“规定”,对这个“世界”,《判断力批判》经过“审定”的结果是“在客观上”“不置断定”,而只是对于“人”的“主观能力”(即“人”的“自由”“能力”亦即“判断”“能力”)“给出”、“规定”和“评定”这个“局域”里的“判断”,康德叫作“反思判断”,以区别于“理论一实践”两个领域内的“立法性-规定性”“判断”。
“反思判断”是对“人”作为“主体”的“能力”的“判断”,有“反躬自问”的意思。
我们看到,在这个“局域”里的“自由”,不是“概念”的“抽象形式”的“自由”,而是“具体的”、具有“直观性”的“自由”;但胡塞尔认为,这种“主体性”的“具体自由”,不是“情感”的,不是“审美”和“目的论”的,恰恰正是“知识”的,是一种不同于“自然一客观”的“必然性”“真理”的“纯粹自由”的“真理”。
于是,“自由”也不是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里所谓“无条件命令”的“道德性”“自由”,而恰恰是被康德“逐出”去的“理论知识”性的“自由”。
在胡塞尔这里,“主体性”没有被“分割”成“知一情一意”,而好似一个直接从“理性”“获得”的“同一一统一”的“领域”,是“哲学”的“领域”,这个“领域”是“纯粹理性”的、是“先验的”。
“哲学”“对于一关于”这个“领域”的“知识”不是“必然”的,而是“自由”的;而“关于”“主体一心理”的“自由”“知识”并不是“随意一偶然”的,不是“游戏”,恰恰是“必真的”(王炳文以此译apodictic,以示与necessary的区别,我认为很好),这个“自由”的“真理”不是“被逼”出来的,不需要由一个“异己-非己”来“矫正”,而是“自己”“建构一矫正”“自己”,就“必定”是“真”的。
“必然性”的“知识”和“必真性”的“知识”,表面看来似乎都是“真理”,但却有层次上的不同:按照我们这里的说法,前者是“第一次”“悬搁”的结果,而后者则是“第二次”“悬搁”的成果。
“第一次”“悬搁”的“结果”为“经验科学知识”,这个“知识”之所以“可以确信”“无疑”,乃是它们有“原因一结果”“范畴”的“保障”,“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是“先天-apriori"的,不是“习惯成自然”,而是“不依赖习惯”的“逻辑推理成自然”。
有一个“原因”就“必定一注定”有一个“结果”,以此“求得”“事物”的“原因”,就是“求得”了关于“事物”的“真知识”,这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一个坚定的信念。
人们把这个富有成果的从“朴素自然”的“生活世界”里“超拔”出来,再“运用-回到”这个“生活世界”来,“得到”了非常积极的“结果”:人们不仅“适应”了这个“世界”,而且“按照自己”的“目的”“改造”了这个“世界”,“暂时”“脱离”这个“实用”的“世界”,被“科学”“武装”起来的“人”“让”“世界”变得“柔软”起来,“顺从”“人”的“目的”;然而“人”的这个“主观”“目的”要“有可能”在原本作为人类科学知识“客观对象-客观条件-客观限制”的“世界”中加以“实现”,则具有许多“偶然性”。
“人”为了“自己”的“目的”有可能“实现”,“人”必须作出“无限”的“劳动”,而“人”作为“现实”的“存在者”,并无“无限性”。
这就是说,“人”在“经验科学知识”里的“自由”只能“限制在”“被认识到的必然性”之中,而这种“认识”又是一个“无限”的“长河”,在这个意义上,“人”必须“超出-超越”“自己”的“被限制性”,“意识到”“自己”原本就是“无限者一自由者”。
“人”并不“停留-局限”“在”“第一次”“悬搁”的“结果”之中,“人”未曾“满足-止于”以“经验科学”为“武器”来“征服”这个“异己”的“自然客观世界”,作“永久性”的“斗争”;为“保障”这个“斗争精神”“永不衰落”,“人”的“理性”还要“唤起”“人”对“自身”“自由”的“确信”,“建立”“自由”“必真”的“信心”,而无需在一个“异己”的“自然-客观世界”“获得”“实证-批准”。
正是“人”这种“理性”之“自由”“本质-本性”“推动”“人性”的“第二次”“悬搁”,即由“自然科学”的“悬搁”“进入”“哲学”的“悬搁”。
这里所谓“第二次悬搁”,乃是从“自然一客观”的“经验科学”的“视域”中“超拔”出来,以一种“更高”的“视域”将由康德“理论理性”“建构”的“概念世界”“提升”到“具体”的“自由”的“世界”中来,这样,这种“超越”和“提升”又是一种“回归”-“回归”到一个比起“概念世界”来更是“真实”的一个“生活世界”来。
但是,我们看到,胡塞尔这种“回归”不是”简单地”“退回到”“朴素自然的生活世界”,而是“建构(在康德意义上)”一个“超出”这个“自然客体”的“理性主体”的“生活世界”来。这个“知识建构”同时也是“视阂转换”,从“概念”的“间接(抽象性)”“回归”到“直接(直观性)”,从由“概念”“建构”的“科学世界”,“转换”为由“直观”“建构”的“现实世界”,所以胡塞尔也把这种与“概念”的“悬搁”不同的“悬搁”,叫作“直观的悬搁”。
欧洲哲学的传统观念,特别是经过中世纪哲学中“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使得人们有一种习以为常的“确信”:唯有“概念”才是“普遍”的,而任何实际事物的“直观”只是“特殊”的;然而,如果“普遍性”与“直观性”“脱离”,则“概念-普遍性”就不“可能”“存在”,从而就不具有“真理性”。
于是,康德就“必须”从“概念”之外“引进”“感性”的“直观”材料,以“保证”“科学”的“真理性”,这个思路直至黑格尔仍有残余的痕迹:尽管“直观”已是“概念(绝对概念)”“外化”的一种形式,但“直观”仍“在”“概念”之“外”,“概念”“异化”“自己”而“成为”“存在”。
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异化”的“概念”“本身”则无“存在性”,“概念”“本身”“不存在”,因而不是“真理”。
对这个问题,胡塞尔采取了与黑格尔相反的思路,他不强调“概念”的“异化”,而强调“直观”本就具有“普遍性”,“直观”“蕴含”着“概念”的“普遍性”,“现实-存在-直观”的“世界”“本身”就是“普遍的”。也就是说,“实际的世界”-“生活的世界”“本身”就是“直观-概念”、“特殊-普遍”、“同一-统一”的“世界”,“普遍性”原本是“直观”的“特性”。
这个“生活世界”不是“物理的世界”,而正是“心理的世界”、“意识的世界”,亦即“有意识-有理性的”“人的世界”;不是“必然性”“统治”的“概念世界”或“概念”“外化”出来的“世界”,而是“具有普遍性”的“直接的一直观的”“生活世界”;不是“必然性”的“世界”,而是“自由性”的“世界”。
这个“世界”,在康德那里是那个“艺术-目的论”的“局域世界”,在柏拉图那里是那个“理念”的“世界”;胡塞尔经过“二次悬搁”的“生活世界”,乃是一个“直观-直接”的“生活一理念一心理一意识”“必真的”“自由世界”。
于是,我们也许可以概括胡塞尔的思路为:由“概念”的“悬搁”“超越”一个“朴素-自然-外在”的“生活世界”,这一“悬搁”把一个“感觉-经验技术(包括实用技术和实用巫术在内)”的“混沌”的“世界”,“提升”为由“理性-知性”“立法”的“自然-必然”的“物理世界”;而经由再一次的“直观”的“悬搁”,“人”“超越”了这个“自然”的“物理世界”,“提升”并“进入”“自由”的“心理世界”。
“人”作为“自由者”“直接地”“生活”在一个“普遍”的“自由者”的“社会”中,而这个“自由者”的“集合体”并不是一个“自然科学”的“实验室”,而是一个“生活的世界”。
在这个“直接”的“生活世界”中,举凡“物理世界”的一切成果,无不被吸收进来,成为“心理-意识世界”的“事实”,被笛卡尔意义上的“我思”所“认识”,这种“知识”无需任何“前提”,具有笛卡尔意义上的“拒绝”任何“可疑性”。
在这里,胡塞尔所推进的思路在于:不仅“我”之“存在”“无可怀疑”,而且“思(之内容)”之“存在”同样“无可怀疑”。也就是说,“自由”之“存在”“无可怀疑”。
“超越的纯粹心理学”“保障”了“自由”的“存在性”,也就是“必真性”,“自由”是“真理”,而不是“形式”;是“普遍”的“存在”,也是“存在着”的“普遍性”。“自由”是“我”的“本质”,是“人”的“本质”;“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自由科学”,乃是“人的科学”,是”人文科学”,亦即“哲学-第-哲学”。
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就不仅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而是“超越”一切“有条件-有外在对象(客体)(无论自然还是社会)”的“(经验)科学”的“超越性科学”,也就是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
五、胡塞尔“先验现象学”之“显现”
我们看到,胡塞尔在“纯粹心理学”意义上的“纯粹-先验现象学”,由于“建构”“在”“直观性悬搁”的“基础”上,他的“显现”不是“寻求”一个“外在”的“对象-客体”“让-令”一个“非对象-纯概念”的“绝对精神”“开显”出来,“让-令”那个“自身”“不开显”的“绝对-自由”“冒着”“受限制”的“危险”“寄托-寄生”“在”“感觉经验”中,而是如实地揭示:不是“自然”“开显”了“自由”,而是“自由”“开显”了“自然”;不是“限制自由”的“必然”“开显”了“不受限制”的“自由”,而是“不受限制”的“真实”的“自由”“开显”了“被限制”的“必然”;不是“存在”“开显”了“意识”,而是“意识”“开显”了“存在”的“意义”;或者用不确切的比喻来说,不是“石头”里“含有”“思想-意识”,而是“思想-意识”“含有-确立”了“石头”“存在”的“意义”。
我们看到,胡塞尔这个“现象学”思路,他的两位杰出的学生海德格尔(“存在”即“存在”的“意义”)和舍勒(质料-直观之先天性)的确是“在”他的“现象学”的“路上”。
“原始-朴素”的“生活世界”是我们“人族-人类”“生活-生存”的“根基”,在这个“世界”中,“人”和“动物”亦与一切“物”一样,“适者生存”是一条铁律,而对于这条规律,“人”基本上处于“盲目”的层面,其“智慧”只“限于”“制造-利用”最粗糙的“工具”,“谋求”自己“不稳定-无保证”的“生活”,或许随着经验的“积累”其“工具-技术”达到相当的水平,仍然为“身体”“存活”所“局限”。
为“存活”而“建构”的任何“高超”甚至“神奇”的“技术”,都难以进入“科学”的层面,而这样的“生活世界”因缺乏“理性一意识”的“确证”,也就难以“提出”“存在论”的问题。
只有“人类-人族”“智慧-意识-理性”达到了“科学-概念”的层次,这个“存在论”的问题才有可能明确地提了出来,也就是后来海德格尔所说的,对于“人”来说,“出了”“一件大事情”“一个大问题”,就胡塞尔的现象学来说,这个“存在论”的“问题”乃是在“知识论-意识论”“基础”之上“提出来”的。
在我们的“论域”里,是已经经过了“第一次”“悬搁”以后的事情。这个“悬搁”确立的“原则”是:唯有“概念”才可以“思想”“存在”,因为“概念”为“事物”的“本质”,而“感觉”为“变化”之“流”,唯“概念-本质”“长存”。
然而,“自然科学”“概念论”的“悬搁一超越”,仍缺乏“彻底性”,即“概念”仍与一个“非概念”的“感觉世界”“对峙”并受其“制约”,因为这个“感觉之流”的“世界”以自己的“直观性”使“概念”“抽象化”而成为一个缺乏“直观-存在”的“空洞”的“世界”;唯有再一次“超越”这个“感觉-客体”的“世界”,再一次经过“直观性”的“悬搁”,“超越”那个由“概念”“建构”起来的“客体世界”,才有可能在那个“原始-朴素-自然”的“生活世界”,“回到直观”,“建构”起一个“真正”的“存在世界”,使单纯“概念世界”转化为“意义的世界”,这个“意义”即是“概念”“回到”“直观”、“回到”“存在”,从而这个“世界”才有可能“彻底”“拒绝”一切可能的“怀疑”,成为“必真”的“存在”。
这样,笛卡尔的“我思”不仅使“我”的“存在”“不受质疑”,而“思”也同样“不受质疑”,不仅是“因”“我”而“有”“思”,而且是“因”“思”而“有”“我”。“认识论”和“存在论”“相互参证”,取得“同一性”。“人”“在”这个“第二次”“悬搁”中不仅“得到了”“自身”的“存在”的“概念”的“证明”,而且得到了“直观”的“证实”。
“概念”固然可以“自身”“证明”“自身”,“神”的“概念”因其“大全”而“必然”“包含”在“存在”的“概念”之中,但“无权”“超出”“概念”“自身”“证实”“自身”的“存在”,因为“存在”的“概念”仍是“概念”;“概念”要“超出”“自身”,必“求助”“非概念”之“感觉材料”,就其“自身”来说,“概念”的“真实存在”仍是可以“质疑”的;只有当“概念”与“直观”“同一”,“概念”与“直观”“无分内外”,“概念”之“存在”才是“无可怀疑”的“必真”的。
这种“同一性”意味着欧洲近代传统“理性主义”把“直观”“放逐”到“外在感觉世界-客体”的“逐客令”必须“收回”,“收回”这条“命令”,也就是把“直观”“收回”到“理性-主体-意识”中来,而这种“收回”,就“生活世界”原本的“同一性”来说,乃是一种“回归”,使“直观”“回归”到“概念-理性-主体”,而不再“寄生”于“外在”的“感觉世界”,而为了求得两者的“同一性”,“概念”也必须“放逐-外化”出去,“谋求”与“直观”“在”一个“异己”的“(物理)世界”“相濡以沫-相依为命”。
于是,胡塞尔与黑格尔都把自己的哲学叫作“现象学”,但在实质上,方向却恰恰相反:后者是一道“逐出令”,前者则是一道“召回令”。我们看到,哲学立场-方法上的一进一出,使各种“关系”都有一种“颠倒”的“效果”。
六 、“理念”与“现实”、“自由”与“必然”、“人文”与“自然”等
这个小标题所列之种种“对立”,乃是欧洲哲学传统的观念。对这种“对立”的“理解”,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特别是经过从康德二元对立到黑格尔一元同一,德国哲学家们的思考,似乎已经有了一个“化解”的“思路”:“现实”中“显现”了“理念”,“必然”中“显现”了“自由”,“自然”中“显现”了“人文”-“非我”中“显现”了“自我”,等等;这意味着,那个原本“不开显-不显现”的“绝对”,“在”“非绝对一相对”中得到了“开显-显现”,“理性”的“东西”“在”“非理性-感性”的“东西”中得到了“显现-开显”。
何谓“开显-显现”?“开显-显现”就是有了一个“(感性一具体)存在”的形式,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普遍性”。这种思路发展到黑格尔,已经具有很深刻的“一分为二”的辩证发展的内容,“绝对”“自身”“异化”成为“非-绝对”,成为一个“理性”“逻辑-合理”的“过程”。
只是这里的问题在于:这种“异化”的过程,意味着“绝对-理性”的“存在”是一个“被存在”过程,是一个“被限制-被规定”的过程,“理性”“必须”“受到(非理性)的限制一规定”才是“存在”,“理性”“自身”仍“不存在”。
在胡塞尔看来,这个思路仍然具有严重的“不彻底性”,“理性”依然“需要-等待”一个“外在”的“形式”来“限制”,才得以“存在”,尽管为“弥补”这个“不足”,“绝对哲学”要“追认”这个“非理性”的“限制者”原本就是“理性”自己的“异化”,但这个“被异化”出来的“非理性者”须得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才又“被”“征服”,直至“绝对哲学”的提出,“理性”才“意识到-认识到”这一切的“非理性”的“妖魔鬼怪”,原本是“理性”自己“创造-放”出来的。
“理性”“创世”,乃是“理性”的“神学”。“理性神学”与一切“神学”一样,都要“解决”“理性-神”自己“制造”出来的种种“麻烦”。“麻烦一矛盾”意味着“不彻底性”。
经过“二次悬搁”的胡塞尔的“主体一先验现象学”克服了黑格尔对待“理性”的这种“不彻底性”,认为“理性”无需“兜圈子-迂回”地“认识自己”,“理性”的“意识-知识”原本就有一种“先验”的“直接性”,也就是“先验”地具有“直观性”,“直观”与“概念-理智”原本“同一”,这种“同一性”“保障”了“理性”本就是“开显”的,“直观”“在”“理性”中“开显”,而不是“理性”“在”“直观”中“开显”。
在这个意义上,“理智直观-直观理智”就是“存在”,“理性”与“存在”“直接”“同一”,或者,“存在-直观”“在”“理性”中“开显”,“存在”在“概念”中“开显”,“具体性一特殊性一个别性”“在”“普遍性”中“开显”。
这就是说,“客体”“在”“主体”中“开显”,“外在”“在”“内在”中“开显”。
我们也可以说,胡塞尔这个哲学思路,是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继续和发展:不是“谁围着谁转”的问题,也不是黑格尔“绝对哲学”的“颠倒”;而是“谁开显谁”的问题。也许,在胡塞尔看来,就哲学来说,既不是“主体围着客体转”,也不是“客体围着主体转”,更不是为“克服”这种“二元对立”“令”“主体”“进入”“客体”,从而“令”“客体”“开显-显现”“主体”,而是“客体”原本就“在”“主体”中,“必然”就“在”“自由”中,“直观”就“在”“理智”中、“存在”就“在”“认识-意识”中,而不是“两个”“东西”“分个高下”。
“理智-认识-概念”无需“要求-征服”“直观-感性形式”“实现”自己的“存在”,“直观”也无需“依靠”“理智-概念”来“建构”自己,这种“直观”与“概念”的“同一性”正是柏拉图当年寻求的“理念”的“意思-意义”。
“理念”不仅具有“普遍性”,而且“同时”也具有“特殊性-个别性”,“理念”已经“蕴含”了“直观”、“蕴含”了“存在”。 “理念”无需“经过”“时间”的“因果”“连续”以求“存在”,“理念”“同时”就是“存在”,“理念”“瞬间(后来克尔凯郭尔阐述出来)”就是“存在”。
“理念”“直接”就是“存在”,“理念”“超越”“时间”、“超越”“时间-空间”、“超越”“因果”,“直接”就是“存在”;“理念”“断裂”“时间”之“连续性”,“打断”“因果”之“(概念)必然性”,“理念”“无待-无需等待”“原因-结果”之“必然-推理”“过程”之“(逻辑论证推理过程)结果”而“存在”,“理念”“直接”“必然”“存在”。
而“直接”的“必然性”就是“自由”。“理念”“必然”“存在”,也就是“理念”“瞬间-同时-无时间性”“必然”“自由”地“存在”。
这也许就是胡塞尔“现象学之剩余者”“第二次悬搁”“所剩下”的“局域”,这个“局域”“被”“封闭”“在”“自由者”的“主体”“心理”之“内”,是一个“再也括不出去”的“我”和“思”,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成为“我思即我在”,以此为“课题”的这门独特的“学问一学科”,就是“哲学”。
“哲学”“悬搁”一切“朴素自然的概念世界”和“朴素自然的生活世界”,但并不“闭目塞听”地“无视”这个“自然朴素”的“世界”,而是“邀请”它们“进入”“我思”的“世界”,“使-令”它们“存在”,而不“随波逐流”,随“时i司”而“流逝”;“我”把“它们”“邀请”“进到”“我”的“心理”中来,“保存-使其存在”起来,“自由”地“建构”起来,成为一门“自由的”“科学”,为“维护”“自身”的“独立性”而与“朴素自然的技术科学”“区别”开来,是为“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或关于“人-自由”的“科学”。
在这个“科学”的视角下,“人”就是“自由”,因这种“自由”的“普遍性”,“人”不“孤独”,“人”有多数而成为“人们”,但“人们”又因其“特殊性-个别性”而是一个“独立实体(斯宾诺莎)”。在这个视角下,“人们”之间的“关系”同样不是“时间”中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同时性”的“瞬间”“关系”,是“思想-精神”间的“自由”的“关系”。
这种“关系”在胡塞尔看来,德国莱布尼兹的“单子论”得其大概,即“单子”“之间”有一种“(相互)反映”的“关系”,亦即“自由”的“思想-精神”的“关系”。
这种“自由者”之间的“非时间-无时间-超时间”的“思想-精神关系”,并不“损害”对于“客观社会”之“因果关系”的“科学研究”,“哲学”并不“夺走”它们的任何“权利”,相反,胡塞尔认为他的现象学为这些“客观自然科学”“寻求”出更为深层的“生活现实基础”。
在这个“内在自由”的“基础”上,“保障”了它们“永久”的“进步”的“必然性”意识,增强了它们“努力工作”的“信心”,即它们的种种努力,有一个“必然”的“自由”“基础”“存在”。
有了这个“基础”,它们就有“权利”“超越”“前人”的“既成事实”,“改变-改造”这个“本来”就在“改变”的“世界”,越来越有一个“自觉”的“方向”使“自然”的“世界”,“转化”“成为”“人”的“世界”。
“一切既成”的“自然事实”,都将被“人”的“学问”-“人文科学-精神科学”-“悬搁”而“获得”“内在”的“自由”,这种“自由的学问一自由的科学”,“悬搁-搁置”对于“单纯”的“自然”“客体”的一切“判断”,“让一交给一鼓励”“经验科学”“持续”作出努力,而“哲学一现象学”将这一切“成果”“奠定”“在”“内在自由”的“基础”之上,使“必然”“回归”“自由”,“使”“概念”在“内在自由”中“找到”自己的“存在-直观”。
这种“回归”的“成果”,使“人”“自觉”到“自身”的“自由”、“自身”的“存在”:“人”不是“生活”在一个“自然的朴素的一或概念必然的”“环境”之中,而是“生活”“在”“自由者”的“自由组合”之中。
这个“自由者”“在”“组合-局域”中的相互关系,不同于“朴素自然-客体”的“因果关系”, 不是“时间”中的“存在-不存在”的“出没”交替的关系,而是“非时间-无时间”的“同时”“存在”。“同时”即是“同在”,“过去”和“未来”、“昨天”和“明天”,都在“现时”中“开显-存在”,而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就不只是“过去-过时”的“曾在”,“历史”有可能成为“必真”的-“直接”的-“现时”的“存在”。
就胡塞尔现象学来说,“过去”和“未来”都“在”“现时”中“开显”,“历史”也是“活”的“现时”;被“经验科学”“判定”的一切“古人”,仍然“有权”在“人-自由者”的“世界”中作为“自由者”“现身-开显”,“古人”有“可能”“在”这个“自由者”“组成”的“局域一世界”里“复活”,“古人”与“时人”“同在”。
没有这一层“关系”,“历史”只限于对“过去”的“客观”的“科学知识”,而难以发挥对于“现时”的“活的一能动”的“作用一意义”,难以成为后来伽达默尔所谓的“有效应的历史”。
因为这种“效应”,只有通过“让-令”“历史”“存在”,“让-令”“古人”在“自由”层面上“复活”,才得以“发挥”出来。这样,我们才“可以-被允许”说,正是植根于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自由”,这种“有效应”的“因果”作用才“发挥”出来,“历史”才不会在“本质”上“被遗忘”,而这个“本质”又不仅仅是“概念”,而且也是“直观”,“本质-概念”就是“存在”。
从这个角度来说,“主体”的“内在世界”“大于”“客体”的“外在世界”,“自由”“大于”“必然”,“意识”“大于”它的“对象”;“大于”亦即“超越”。“意识一意义”的“世界”是一个“非-无对象性”的“独立一自由”的“世界”(雅斯贝尔斯),“一切”“对象-客体”都已经过“第二次悬搁”“进入”了“主体-意识”,被“经验科学”“设定”的“随时间而流逝”的“经验对象-客观事物”,都已“成为”“人”作为“自由者”的“世界”“组成环境”而得以“保存-存留-存在”,“人”“实际上”“生活”“在”这个“自由”的“意义世界”,而“意义世界”亦即“理念世界”,“人”“从未”“生活”“在”一个“单纯的-朴素的”“自然世界”里。
“人”的“生活世界”里的一切“事物”、一切“现时”的“事物”都是或大都是“昨天”的“事物”,也都是或大都是“明天”的“事物”;在这个意义上,不是“人的本质”“对象化”为“物”,而是“物-对象”“人化-主体化-自由化-意义化”为“哲学”“意识-认识”。
经过“第二次悬搁”之后的“生活世界”,不是“单纯概念”的“世界”,也不是“退回到”“原始朴素”的“感官世界”,而是“坚持住”“理念的世界”、“意义的世界”即“理智性”的“直观世界”,同时也是“直观性”的“理智世界”。
“人”的这样一个“生活环境-生活世界”,将人的一切“感官”“理智化”,也将“人”的一切“概念-判断-推理”“感性化”,而这个“世界”并非“艺术的世界”(康德),而是“真实”的“生活的世界”,“艺术”只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存在”的一种“方式”(海德格尔)。
正因为这个“生活世界”“超越”了那个“朴素-自然的生活世界”,我们也常说,“艺术”“高于”“生活”(黑格尔及其后来之影响)。这样,于一切“现象学”“显现-开显”的“关系”“被”“颠倒-颠覆”一样,不是“艺术(感性)”“开显”了“生活-理念-意义”,而是“生活-理念-意义”“开显”了“艺术”;一如不是“感性-必然”“开显”了“理性-自由”,而是“理性-自由”“开显”了“感性-必然”;不是“客体”“开显”了“主体”,而是“主体”“开显”了“客体”。
用中国哲学话语来说,这层意思就是:不是“物”“开显”了“人-我”,而是“人-我”“开显”了“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