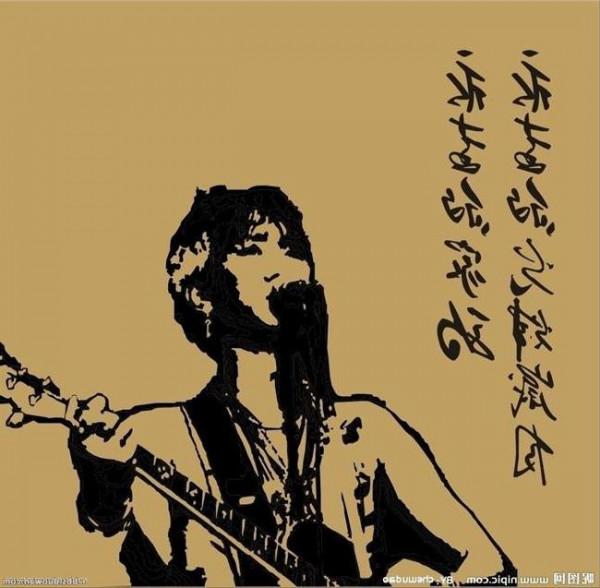朱哲琴丹顶鹤的故事 朱哲琴:音乐之外的漫游
为什么我采访的女艺术家都有这样一双 “伤口般”的眼睛,充满神秘,让人无法碰触。写诗的翟永明,做雕塑的向京、还有眼前这位朱哲琴,从视觉到听觉,再到语言。
朱哲琴身材娇小,但气场足够。歌手身材小,台上视觉效果不占优势,2000年她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开《天唱人间》演唱会,记者买最便宜的票,坐在最后排,她穿着重叠繁复的服装,出现在舞台上,并没有渺小的感觉,靠的就是气场。那场演出,是用演奏带伴唱。事后有人怀疑她假唱,因为她现场的音色与唱片没有区别,好得不真实。事实上,她在录音棚里都是一次就过,用不着混音修修补补。

翟永明和向京是典型的女性主义艺术家,而朱哲琴展现的,却是一个与性别无关的音乐世界。从最初的《黄孩子》,到一举成名的《阿姐鼓》,直到最近的《七日谈》和《波罗密多》,她是自由而任性的女声,自云“超现实主义与月亮的融合”。

“达达娃”,是朱哲琴的另一个名字,“达达”主义是超现实,“达娃”是藏语里的月亮。做世界音乐的朱哲琴用藏语为自己命名非常好理解,可达达主义……她强调自己其实一直喜欢超现实主义,并在自己身上总结出很多超现实主义现象:身材那么娇小,但声音却那么大;还有就是对生命的看法,人们通常接受的观念就是死亡乃万物俱灭,但她将死亡和诞生看作相同的东西。

这已经是哲学上的意义,朱哲琴的确是中国少有的用人声探索哲学意义的艺术家。
朱哲琴是湖南人,生于广州,从很小就开始唱,进入儿童艺术团体,天赋很好,从来就讨厌练声,音域却非常宽广明亮,但父母并不支持她以唱歌为职业。1990年大学毕业时,广州流行乐坛因为毗邻香港的关系,领内地风气之先,出了很多像解承强、李海鹰这样的制作高手,是她出道的领路人,她还得过青年歌手大赛第二名。

记者记得当时有一本叫做《流行歌曲》的简谱本,诸如《酒干倘卖无》等歌的结尾处都标着“那英演唱”、“朱哲琴演唱”等,其实那不过是内地歌手们的口水翻唱,力求学得像而已。后来的这批歌手,出息了的大多成了流行歌曲天王天后。而朱哲琴,唱着唱着,完全变了调,做起了最早的“概念唱片”。
因为她遇到了何训田。
何训田当时在四川音乐学院当老师。朱哲琴不想进入体制内的歌舞团,她喜欢自由的生活,想当导游,可以到处玩。何训田在音乐上有强烈的自觉意识,他明白朱哲琴这种自由的天性和宽广的音域对他们俩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当时,唱片包括专辑都没有主题和完整的概念表达,而是歌曲的拼凑,如果有,那也是《长征组歌》或者《东方红》。何训田和朱哲琴当然不属于《东方红》时代,他们很清楚自己想围绕一个主题做一张概念唱片。
在做带有巴蜀文化特点的 《黄孩子》时,他们就在思考自己是谁,究竟迷失在哪里。之后,他们去了西藏,开始寻找自己。
当时的西藏远不像今天这样成为人人狂喝的心灵鸡汤,人人都可以在西藏找自己内心某一刻的映照,或者溜进八廓街的玛吉阿米找点可口的藏餐。而在当时,听说他们要去,周围的人担心的是:当地人不欢迎你,向你们吐口水,你们会没吃没住的,你们没法和当地人融合。
但何训田和朱哲琴不相信一面之辞,他们要的是“看见”和“经历”。她戴着朋友妈妈的一顶土毛线帽,穿着旧式土棉袄,有点像打官司的秋菊,就这样到了拉萨。一去,她就觉得跟那里很有缘分。
并没有人向他们吐口水,人们都在专注祷告。她在大昭寺跟着一个老太太采集声音,老人一直在朝拜,在念颂祈祷,很专注。她打开采样机,老人发现了朱哲琴,就把她的头按在祭坛上,意思是说,你也祈福,你也会得到加持,得到福报。那一瞬间,朱哲琴觉得一切都释然。这就是慈悲。
1995年,《阿姐鼓》出世。朱哲琴用既甜美又妩媚,既静谧又狂放,既超凡又入世的女声,将藏族文化中的“人皮鼓”由凄厉之美变成崇高之美。崇高一直是何训田与朱哲琴所追求的,在之后的《七日谈》、《波罗密多》等专辑中,“西藏”的特色已经隐去,但崇高感一直清晰地持续。
《阿姐鼓》是中国第一张概念唱片,也是第一张获得国际声誉的中国唱片,在这之前,印度、拉美、非洲的音乐都在世界音乐史上留下了足迹,《阿姐鼓》使得中国的世界音乐也有了这种可能。
可以说何训田与朱哲琴开创了中国的世界音乐,并一步到位将中国的世界音乐提升到最高水平。如果有人为在金色大厅举办独唱音乐会而沾沾自喜的话,那朱哲琴的演唱会经历远远傲立其上,她所获得的实质性国际音乐奖项更是数不胜数。
之后的朱哲琴一直在世界各地旅行、采风、创作,她已经多了一个听上去十分西藏的艺名“达达娃”,但她不愿把“西藏”看成她的代名词,她说:一直唱《阿姐鼓》,她会死的。她的眼界放到更宽广的亚洲地区。《七日谈》呈现泛亚洲的东西,对应的是有、情、真、生、善、美、无这七种觉悟,或者称人生的七个阶段,其中第七“无”,是无歌词的即兴吟唱。
《波罗密多》有印度的民间乐器,汉传佛教的偈子,有一段《心经》由朱哲琴演唱,这次演唱不同于《阿姐鼓》“力”的表现,而是自在、平和的歌声。
对于《七日谈》和《波罗密多》里大量的宗教和哲学内容,朱哲琴表示,她不是世俗意义上的信徒,但她相信佛陀的真理:没有神,或者说人人都可以成为神,人是自救的,而不是等待他救。藏历马年,她去转神山,快到顶时,看见藏族司机拿出一个干净的小包裹,包了很多层,打开一看,是一本经书。
她问:“师傅,你念的什么啊?”司机说:“祝愿世间万物众生祥和。”她大大地感动了,因为多少人拜佛就是求升官发财,一个西藏的普通司机却有如此大的胸怀。
她在拉萨看到,那些贫穷的藏民,白发苍苍,每个人怀中都揣着散钱,见人就施给。在那样人迹稀少的恶劣地区,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天地之间的关系,不发自内心带着慈悲去维系,早就分崩离析。同时,宗教使她以善良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
她在印度旅行,混乱不堪的火车站上,到处游荡着小流氓,他们冲她不怀好意地笑,她并不恼,报以善意的笑,这笑居然感染了那些小流氓,不仅没有骚扰她,反而还帮她提行李。她相信人性本善,一定要耐心去激发这善。这也是慈悲心。
2007年,已经远嫁加拿大的朱哲琴回到中国,云南迪庆州的书记齐扎拉想让她帮助整理一下香格里拉古城经堂的颂经,她与喇嘛们一起工作时,正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驻华代表马和励与夫人到访。马和励发现朱哲琴是理想的UNDP中国亲善大使人选,因为在多年的艺术探索生涯中,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音乐多次成为朱哲琴的灵感来源,朱哲琴对这些地区文化遗产传承所面临的保护与发展的困境也有相当的了解,便用1美元的年薪聘任朱哲琴做了2009年至2010年的亲善大使。
今年初上任后,朱哲琴与工作组一起发起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行动,这个行动由音乐和手工艺两部分组成。4月到7月,朱哲琴先后在五个省区做音乐旅行和田野调查,谈及这段经历,她说:“我天天觉得很幸运,看到这么多壮丽的山水,听到那么多很原味的音乐,我的营养太好了。
但是回到城市里,一方面经济好像很发达,一方面又好像没有希望。经常性地,当我进入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空间,觉得生命无限美好。但是当我一面对现实,我发现落差很大,我会觉得很糟糕、很痛心,怀疑周围的意义。
能选择的东西越来越少,只是几个主张,天天在轮番出场。”但朱哲琴不是个被动的人,哪怕每天只有那几个主张在轮番出场,她也要在自己能掌控的范围内玩出花样。
她会以音乐旅行为素材,以保护和再生的双向理念制作一套CD,对这些少数民族的音乐进行艺术推广,还会邀请知名设计师对少数民族的手工进行设计,进行新的营销,中国不能只做A货,有那么多美丽的元素可以进行原创设计,她要借此来“增进整个区域与外界的相关了解和交流,以文化的复兴来带动当地的经济复兴”。如此愿望,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也许过于宏大,但对UNDP亲善大使,确实是一份尽责的职守。
朱哲琴的艺术生涯达到过巅峰,她看到人生最美的风景,唱出天籁般的歌声,而且受到过那么多的加持与祝福,甚至在个人生活上也堪称美满:何训田使朱哲琴成为达达娃,达达娃让何训田的音乐有了完美的载体,虽然他们最终并不在一起,有各自的爱人,但他们继续相互成就,并达成精神上的映照。这样的人生,朱哲琴不会再有遗憾和畏惧,惟剩梦想,有一个梦想就是在布达拉宫广场上开演唱会。
感谢上苍。
访谈
经济观察报:现在大家都提倡做慈善,一般是从经济上、教育来做,你做UNDP大使是从文化上来做的。
朱哲琴:我觉得我不是在做善事,因为同时也是在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自己的文化生态,是我们自己应该做的。就像做环保既是为环境,也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存。
经济观察报:你一直做少数民族音乐的整理和再生,这是UNDP找你做亲善大使的原因吗?
朱哲琴:可能是这个,因为原来我的创作都跟这些区域有关系。其实我在被任命的时候也是,UNDP也没有说让我去做什么太多具体的项目,只是起到呼吁公众意识这个宣传层面的作用。但我觉得不够。说实话,少数民族的文化现在不是热门,但这是跟人们非常密切的事情。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多民族生活在一起,但是在文化领域的认知和沟通,我觉得还是比较少。我们谈国学的时候,主要是在谈汉学,这显然不够。我的朋友钱文忠引用了季羡林先生的话:国学不应该单一提倡汉学,而应该将西藏、新疆以及更多的文化都囊括在一个版图里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多元的大中国。
看到这段话我很感动,中国现在有那么好的经济腾飞的基础,下一步应该是中国精神和文化并存,同时崛起。
从音乐开始,我要去那些地方,把原汁原味的民间音乐先忠实地记录下来。第二步我们一方面是去保护这些东西,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发展它,让它介入当代,并且延续下去。所以我就开始了策划一个活动。其实这个事情跟UNDP也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是我自己在做这个计划,一个音乐的五省自治区的寻访之旅。
第二是联络一些音乐家、设计师、出版人,让这些东西与外界有机会见面。这中间以保护和发展双向概念为基础。在对待传承的时候,要并行地去做:一方面要保护,更多应该落实到政府、学院、机构、基金会的保护,把它放在很特定的一个区域,尽量让它的基因和品种保护起来,就算是标本也是一个活标本。
另外一部分我自己认为,要让这些传承生长,对当代有影响并延续下去。我们今天触摸到的传承也不是一个定格的东西,也是发展而得,绝对的真空保护,是不现实的,是一厢情愿的乌托邦。
经济观察报: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会把中国和印度做比较,你在印度做过深度旅行,从文化的角度,你是怎么看待这两个国家的对比?两国之间的竞争存不存在?
朱哲琴:我去印度的时候,这个问题想了好几次。印度人传统观念非常强大,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让我惊讶。他们也穿牛仔裤,也看篮球,也用电脑,但到了重要节日一定穿上传统服装,每天该祷告的时候一定要祷告。这些你每时每刻都能感觉到,传统在他们身上起很大的作用。
在中国情况就不是这样了,中国的当代面貌多以颠覆过去创造未来的形式呈现。这是很大的一个不同。我觉得印度强调科技的现代化,但是在意识形态和观念上,他们还非常坚守,而且很有成就。印度有宝莱坞,好莱坞无法与之抗衡。印度所有的文物景点是拿着枪保卫的。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不同。
我无法预言将来谁更好,我不是经济学家。我只看到印度有根深蒂固的等级关系、伦理道德,印度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的。中国是以革命来发展的。如果最后中国更强大,而且完整,优于印度,那我们可能要重新估量一下(革命的作用)。如果印度系统的优势展现的话,那可能印证了人类的传统文化比革命更优越。我去印度就完成了这样一个思考。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自己唱歌是特别有天赋的吗?
朱哲琴:这是显而易见的!从小就觉得我天生会唱歌。
经济观察报:你的歌音域特别宽广,很自由,声音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朱哲琴:这是我的一个理想。大部分的时候我能做到,很少的部分我也出轨一下,就是回到现实。我是一个东方人,相信精神意念对人产生本质影响。所以小时候我很烦练声,在不练声的情况下,我要求我随时唱都特别好听。这是我的要求和标准,我做到了。我的乐器在我的身体里,我锻炼身体。
经济观察报:这是对歌手最基本的要求吗?还是说只有少数人天赋很好的人才能做到?
朱哲琴: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的。艺术是很奇妙的,你问我有没有天赋,我会说有,我的确认为它是很奇妙的,我并不是说我没有努力,或者我是一个不认真的人,但我觉得艺术是不能够像量尺一样去计算的,它是无形的,你不能用有形的逻辑去解释。
艺术很本能,像歌唱实际上是人的天赋,人应该有的,那些原住民没有上过音乐学院,那些苗族人也没有上过音乐学院,但是人家唱得比你高。
经济观察报:少数民族的艺术基因天生比汉族要多,还是说汉族人受的束缚太多了?
朱哲琴:我觉得是后者。你去度量人的声带、脊椎、口腔,不同的人种是有差别,但差别不大。我们汉族在过去的文明发展中,很多东西被抑制住了,而这些少数民族没有被驯化,身体里面有很多天然的东西。
经济观察报:在你的纪录片《声音的漫游》里,看见你随时能融入各国各民族,随着他们的节奏唱、跳,你是个很放得开的人吗?
朱哲琴:如果我们坐在这里,你让我站起来唱支歌,哪怕是我自己的歌,我也会觉得很难。但在那种情境里,我很自然就融进去了。
经济观察报:你好像尤其重视你自己的感觉。
朱哲琴:我的所有经历不是人家告诉我什么,而是我自己体会的。像2005年的时候我在尼泊尔做 《声音的漫游》,好多朋友都说你不要去那边,很乱。我达到加德满都的时候,完全是另外的一个状况,你可以从我的纪录片里面看到,那是一个多祥和快乐的世界。等我要去喜马拉雅山,离开加德满都的时候,的确在乡下看到荷枪实弹的军队。人要自己去体会印证。释迦牟尼说得很对,你要去印证,自己去印证。
经济观察报:你对民族文化和音乐这么感兴趣,是因为跟何训田在一起工作,还是说你天生就跟这种文化比较有亲近感?
朱哲琴:说我天生就有亲近感,有点牵强。20岁左右,我有机会去旅行,去四川康巴地区,我一下子就被那些东西吸引住了,很多人对我说我会不习惯那里的落后,我从来没有想过那些东西,倒是他们的美一下子吸引住我。
经济观察报:别的少数民族有这样强烈吸引你的东西吗?
朱哲琴:也有。我们这次去苗族,他们的强悍很感染我。我曾经在山坡上录苗族飞歌,苗族人在山上砍柴的时候,因为离得远,就要把歌唱得很高很远。那个声音啊,一开始我觉得被一股声浪冲击,就像好莱坞电影镜头一样,我整个人都被弹出去了。我经常去不同的地方,会被不同的东西感染,尤其在西藏感受很深,因为除了艺术以外,那里还有一种慈悲。
经济观察报:怎么解释这种慈悲,它来源于人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面还能生存还是别的原因?
朱哲琴:我觉得是对生命的珍惜,在海拔那么高的地方,物质非常贫乏,人特别珍惜生命,珍惜生灵,不只是人的生命。
经济观察报:能问一下大家都比较关心的问题吗?现在好多活佛都在给人开示,人们也闹不清是真的假的。
朱哲琴:我看事情从来都看本质,我不会太在意那些世俗的名号,也不管他穿着怎么样、说什么语言,而是更关注看他让我们干什么、这个人做什么、结果是什么,这是最重要的。他如果跟你说爱别人、慈悲、度化别人、容忍别人、关爱别人、成全别人,并且身体力行,那他就是佛,我觉得他就是对的。
你明白吗?这是一个什么都可能发生和什么都可能存在的时代,但是最终我们要什么,关心什么,我们自己心里面应该有一杆秤,当你明白这个的时候,不用我告诉你,你自己就知道谁是谁。我关注人的内心那个觉者的存在和向往!











![>朱哲琴新乐府[WAV/百度网盘]](https://pic.bilezu.com/upload/9/68/9684d9522a1e431fd15310975ecbc6b0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