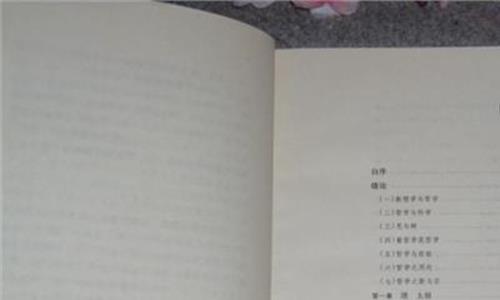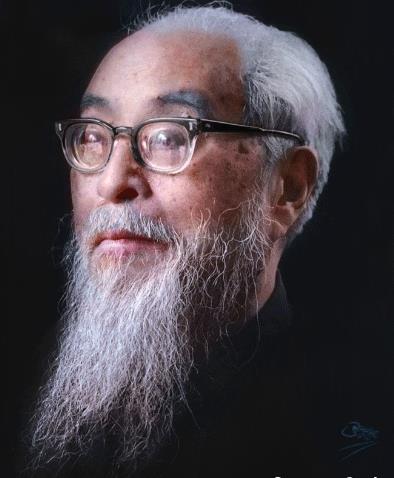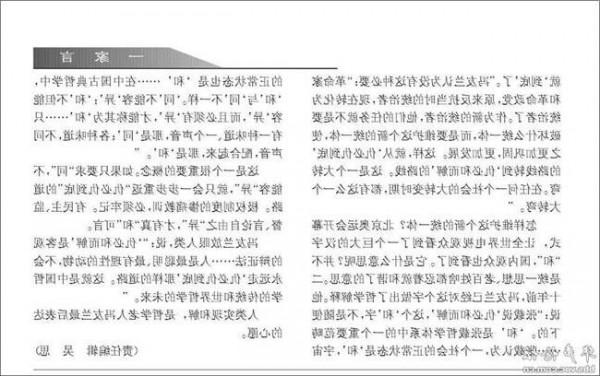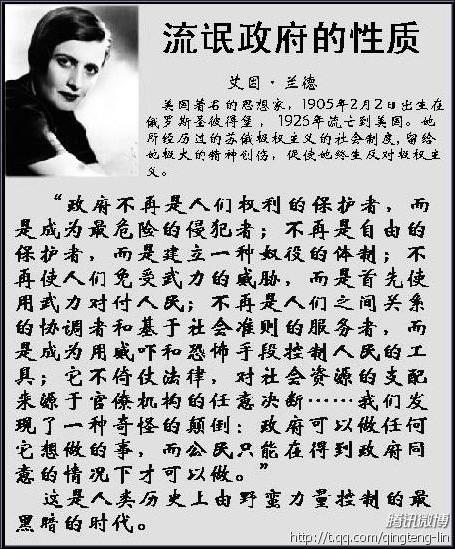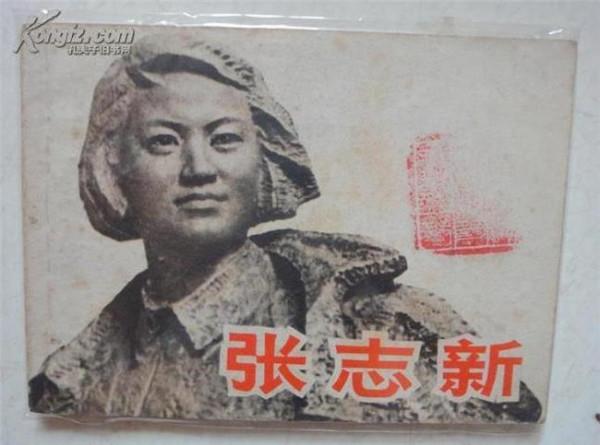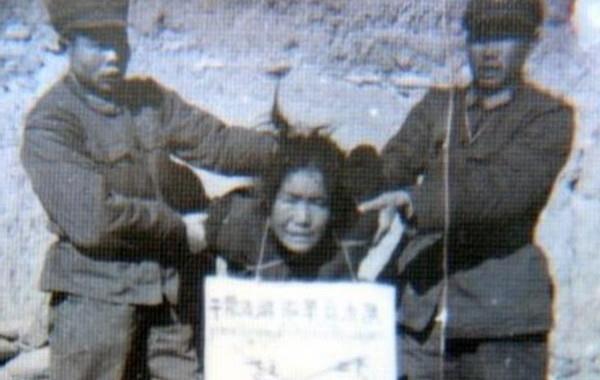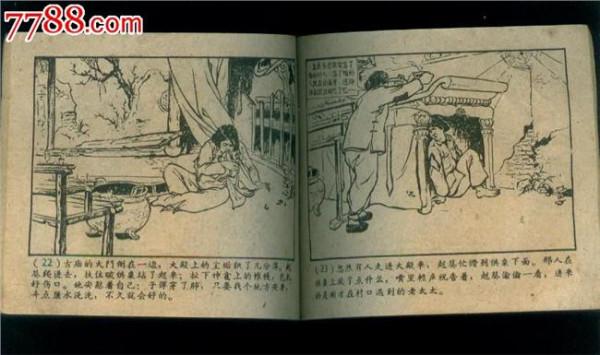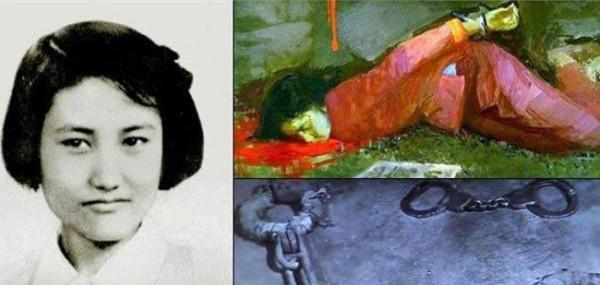冯友兰新理学 朱光潜: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
近一二十年来,关于中国哲学方面,我还没有读到一部书比冯友兰先生 的《新理学》更好。它的好,并不仅在作者企图创立一种新的哲学系统,而在它有忠实的努力和缜密的思考。
他成立了一种系统。这对于中国哲学的功劳是值得称赞的。我们一般浅 尝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人们,常感觉到这两种哲学在精神和方法两方面都有显著的差异。就精神说,中国民族性特重实用,哲学偏重伦理政治思想, 不着实际的玄理很少有人过问;西方哲学则偏重宇宙本体和知识本身的性质 与方法之讨论,为真理而求真理,不斤斤计较其实用。

就方法说,西方哲学 思想特长于逻辑的分析,诸家哲学系统皆条理井然,譬如建筑,因基立柱, 因柱架顶,观者可一目了然于其构造;中国哲学思想则特长于直觉的综合。
从周秦诸子以至宋明理学家都喜欢用语录体裁随笔记载他们的灵心妙语,譬 如烹调,珍味杂陈,观者能赏其美,而不必能明白它的经过手续,它没有一 目了然的系统。

这见解大概是普遍的。读过冯先生的《新理学》之后,我们 对于这粗浅的印象至少要加几分修正。他很明白地指点出来:西方哲学家所 纠缠不清的宇宙本体和知识性质诸问题,在中国也是向来就讨 论得很热闹 的。

我们从前读旧书,固然也常遇到“理”、“性”、“气”、“道”、“太 极”、“无极”、“阴阳”等等字样,但是这些字样对于我们门外汉颇有几 分神秘气息,“玄之又玄”,也可能地是“糟之又糟”。经过冯先生解释之 后,我们才恍然大悟这些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还是可思议可言说,而且我们 的哲学家所求之理与西方哲学家所求之理根本并无大别,所得的结论也差不 多。

其次,中国哲学旧藉里那一盘散沙,在冯先生手里,居然成为一座门窗 户牖俱全的高楼大厦,一种条理井然的系统。
这是奇绩,它显示我们:中国 哲学家也各有各的特殊系统,这系统也许是潜在的,“不足为外人道”的, 但是如果要使它显现出来,为外人道,也并非不可能。
看到冯先生的书以后,我和一位国学大师偶然谈到它,就趁便询取意见,他回答说,“好倒还好,只是不是先儒的意思,是另一套东西”。他言下有 些歉然。这一点我倒以为不能为原书减色。冯先生开章明义就说;“我们现 在所讲之系统,大体上是承接宋明道学中之理学一派。
我们说‘承接’,因为我们是‘接着’而不是‘照着’宋明以来理学讲的。因此,我们自号我们的系统为新理学。”他在书中引用旧书语句时,常着重地声明他的解释不必 是作者的原意,他的说法与前人的怎样不同。
这些地方最足见冯先生治学忠 实的态度,他没有牵强附会的恶习。他“接着”先儒讲,不“照着”先儒讲, 犹如亚理斯多德“接着”柏拉图讲而不“照着”他讲,康德“接着”休谟讲 而不“照着”他讲,哲学家继往以开来,他有这种权利。
要明白冯先生的系统,必须读原书。粗略地说,他的系统基于“真际”(即“本然”)和“实际”(即“自然”)的分别。“真际’包含超时空的 一切“理”,“实际”之最后的不可分析的成因为“气”。比如说,“这是 方的”,“方”的理存于真际,“这”是实际中一个方的物。
实际的方的物 “依照”真际的方的理而得其方的性。只有性不能成物,方的物必有其所“依 据”以成为实际的方者,这叫做“料”,料近于“物质”,不过物质尚有其 物质性,将一切性抽去而单剩一极端混沌的原素,则得“绝对的料”,此即 “真元之气”(简称为“气”),亦即“无极”。
真际所有理之全体为“太极”。“极”有二义:一是标准,每理对于依照之事物为标准;二是极限, 事物达到标准亦即达到极限。
“太极”理之全,“无极”物之础,由“无极 而太极”,即由气至理,中间之过程即我们的事实的实际的世界。理为“未 然”,为“徽”,为“体”,为“形而上的”;物为“已发”,为“显”, 为“用”,为“形而下的”。形上的理是思之对象,是不可经验的;形下的 物是感之对象,可经验的。哲学所研究的为形而上学的理。
这是冯先生的基本原则,从这些基本原则出发,他解释天道,人道,历 史,宗教,艺术以至于将哲学本身当作一个实际事物看。篇幅只容许我讨论 他的基本原则,虽然原书引人入胜的地方并不仅在基本原则。我接受冯先生 的立场,来审查他的系统是否完整无漏或“言之成理”。为清晰起见,我把 我的意见分作三个问题来说。
一、真际和实际是否有范围大小的分别? 冯先生以肯定的回答此问题,他说:“属于实际中者亦属于真际中。但属于真际中者不必属于实际中。我们可以说,有实者必有真,但有真者不必
有实;是实者必是无妄,但是真者未必不虚。其只属于真际中而不属于实际 中,即只是无妄而不是不虚者,我们说它是属于纯真际中,或是纯真际的。 如以图表示此诸分别,其图如下:
就此图所示者说,则对于真际有所肯定者,亦对于实际有所肯定。但其 对于实际有所肯定者仅其‘是真际的’之方面,??我们说哲学对于真际有 所肯定而不特别对于实际有所肯定,特别二字所表示者即此。” (10 至 11 页①)
就图及解看,冯先生以为实际与真际的关系,犹如实际的事物与实际的关系一样,同是范围大小的关系。真际大于实际,犹如实际大于每个实际的物,犹如动物类大于人类。但是大者与小者都同在一平面上。依形式逻辑, 对于全体有所肯定者对于其所含之部分亦有所肯定;所以冯先生说,“对于 真际有所肯定者亦对于实际有所肯定”。
于此我们向冯先生说,你这个人是 实际的人,决无疑问;要是说你这一个实际的事物亦属于真际中,和你所谓 形而上学的理在一块儿站班,那就大有问题,因为属于实际中者即不属于真 际中,固然,你是人,有人性,而人性所“依照”之理仍在你所说的“太极” 圈里。
其次,你假定真际有纯真际和不纯真际的分别。其实,是理就是纯理, 真际都是纯真际。
唯其“纯”,才是“极”。实际事物“依照”纯理为准而 至其“极”者,依冯先生的看法,亦属罕见。真际有“极”圆而实际不必有; 真际有“凡人皆有死,若泰山为人,则泰山有死”之假言判断所含之理(如 罗素和怀特海在《数学原理》中所说者),而实际不必有此事实。
所以对于真际有所肯定者,对于实际不必有所肯定。所以然者,真际和实际并不在一 平面上而有一部分范围相叠合。它们并不是一平面上范围大小的分别,而是 阶层(order)上下的分别。
真际是形而上的,实际是形而下的。实际事物的 每一性与真际中一理遥遥对称,如同迷信中每人有一个星宿一样。真际所有 之理则不尽在实际中有与之对称或“依照”之者,犹如我们假想天上有些星 不照护凡人一样。
冯先生自己本来也着重形上形下的分别,而有时却把真际 和实际摆在一个平面上说,拿动物和人的范围大小来比拟真际和实际的范围 大小。此真所谓“比拟不伦”。就这一层说,冯先生似不免自相矛盾,而这 矛盾在冯先生的系统中是不必有的。
二 真际和实际如何发生关系?
真际是形而上的理,实际是形而下的事物,这个分别是从柏拉图以来二千多年一般哲学家所公认的。如果冯先生的贡献亦在说明这个分别,那就可不用谈。哲学家所纠缠不清的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际”如何合拢起来,成 为我们所知道的形上又形下的宇宙。一种哲学系统能否成立,这问题是一个 试金石;每个大哲学家的企图都在打通这个难关。冯先生打通这个难关没有 呢?他提出“依照”和“依据”两个观念来讲,物“依照”其类之理而得性
(如圆),“依据”本身无性的气而成为实际的物(如圆物)。气是“无极”而理是“太极”,由“无极而太极”,即由气而理,“中间之过程即我们的 事实的实际的世界”(74 页)。此“而”即是道。宇宙大全是静的,这是动 的;“宇宙是静的道,道是静的宇宙”(98 页)。
动依“一阴一阳”之公式。 “依照某理以成某物之气之动者,对于所成之某一物说,名曰阳。与此气之 动者之气之静者,对于此物说,名曰阴”(87 页)。阳是动的,生长的,阴 是静的,消毁的。
比如房子,砖瓦工匠之助其存在者是房子之阳,风雨炮火 之阻碍其存在者是房子之阴。物物都有阴阳,而阴之中与阳之中又各有阴阳, 如此循环不止。阴阳消长乃有成(=)盛(=)衰(=)毁(=)之四象。易卦 即为事物变化公式之象。这是对于易学及道家哲学的一种很有趣的新解释, 但是冯先生似尚有未能自圆其说处,现在分六点来说。
一、气本身无性。但冯先生承认它为“物存在之基础”,“至少有存在性”。此“存在性”为在真际有理为其所“依照”呢?为在真际无理为其所 “依照”呢?为其有,则气仍非“绝对的料”,仍非“无极”;如其无,则 宇宙中可有无理之性,此在冯先生的系统中说不通。
二、理超时空。据冯先生说,“真元之气亦是不在时空者”(82 页)。 他没有告诉我们,不在时空者如何有“存在性”?它是否仍是“太极”中一 因素?他更没有告诉我们,两种都无时空的“理”与“气”如何生出有时空 的事物?
三、由“无极而太极”,此“而”字冯先生甚看重,认为即是“道”, 亦即是“实际的世界”。这不啻说,道即是实际的世界,但这又似不是冯先 生的系统所能允许的。此“而”字我们也甚看重,但如何“而”法,我们读 过冯先生的书之后,仍不甚了了。就他所举的例来说,房子由砖瓦工匠造成, 由风雨消蚀,是房子的阳与阴,但是这种阴阳消长,仍是形而下的事,并没 有由“无极而太极”,“而”来“而”去,仍“而”不出实际的圈套。
四、依冯先生的系统,实际事物皆“依照”真际的理。实际有阳消阴长,真际也应有一个阴阳消长的理为它所“依照”。这就是说,实际有动,有大 用流行;真际也应有动,有大用流行。冯先生却说,宇宙大全是静的,“宇 宙是静的道。道是静的宇宙”。这似乎承认真际原来是静止的,不生不变的, 不能运行的。这“静的道”又如何“动”起呢?
五、冯先生对于实际和真际的关系,实有两个不同的说法:一是“依照” 说,一是“无极而太极”说。据“依照”说,“物”“依照”其类之理而得 性,是本有理而人依照之;据“无极而太极”说,由气至理,是本有气(物 存在之基础)而后达到(所谓“而”或“至”)理。
照这种看法,不但理可 独立,气也可独立。两种独立说之合拢则有两种看法,一是从理看,一是从 气看;从“理”看,似为真际产生实际,从“气”看,又似实际附不上真际。 这两种看法如何调和,也颇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