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四大美女之一范元甄:被共产党洗脑成怪物
范元甄(1921年4月——2008年1月24日),女,汉族,湖北省武汉市人,1936年1月参加革命,1937年8月加入中国***,李锐(曾任***秘书、中组部副部长)的前妻。
范元甄1934年投身抗日救国的学生运动。1935年参加武汉学生联合会,领导本校学生参加武汉声援北平“一二·九”运动的罢课和大游行等活动。1936年7月参加了筹组武汉学联的工作。同年12月参加筹组武汉“民先”工作,并当选为宣传干事。
1937年12月参加筹组中共中央长江局青委领导的青年救国团,并任总团宣传部副部长、汉口区团部训练部部长。1938年秋,转入***领导的政治部下属第三厅抗敌演剧九队任党支部***。
1939年2月调入重庆中共南方局党报《新华日报》任记者,同时任南方局女卫委委员,先后在《解放日报》、《冀热辽日报》、《西满日报》及《解放报》工作。1940年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41年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
1951年任湖南省工业厅主任秘书。1953年任北京石景山发电厂代厂长。1954年任航空工业总局特设处处长。1956年到北京航空学院学习。1959年任国营二三二厂总工程师。1962年任航空工业总局总技术处处长。1979年任航空工业部科技局顾问。1982年6月离职休养。
1921年出生于汉口殷实人家,少女时代即投身革命。与李锐在抗日救亡活动中相爱,1939年与李锐结婚,1939年底,两人一起奔赴延安。
其成名很早:在学生运动的时候,就深得王明的赞誉;在重庆时期,更是为***夫妇所宠爱;在延安马列学院,连***都知道她的名字,路上遇到,都会说一声:“小范你先走”。论美貌,和***等并称为“延安四大美人”;论学识和能力,众口赞誉,身为***秘书的丈夫曾亲口对女儿说过,范元甄能力在自己之上。
1943年4月,李锐被诬陷为特务,被关进延安的监狱——保安处。范写道:“想到一切都是在做梦。他的一切都为了麻痹我,为了他的政治目的。我就很平静,想到将来,想到我正需要一个新的开始,摆脱了他正是一个解放,想到这些我是很冷静的。在所谓感情上,我真是对他毫无留恋了。……”并与之离婚。李锐在被关押一年零三个月之后,从监狱出来了。范主动要求与他复婚,他俩又重新成为夫妻。
解放之后极短的时间里,范元甄受到了重用。1959年因丈夫被打成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追随者而受到牵连,并被发配到热处理车间当炉前工,接受改造,身体在重压之下彻底垮掉。多次的政治连坐使她严重心理扭曲,变得似乎只有党性,而没有了人性,在很多运动风潮之中,她疯狂的揭发李锐、揭发亲人,甚至连女儿都不放过。
李锐于1960年4月被发配北大荒。在北大荒过的是非人的生活,他写信请范给他寄点东西,范竟然去信挖苦,还把他们夫妻间讲的枕边话写成揭发材料,把李的两封信交给组织。
伤心欲绝的范元甄提出离婚,两人于1961年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但范元甄没有想到的是她的做法没有得到组织的赞许,她也从此一直没有再次得到闪光的机会。王若水在《左倾心理病》一文中提出的对范元甄的看法是:“范元甄的性格有个人因素,又是制度的产物。某种制度塑出某种性格的人,这种社会性格的人又成为该制度的维护者”。
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范短暂恢复过一段工作,在航空部技术局总技术处任处长,后由于***开始,被发配到干校劳动,回京不久后便被做离休处理。
女儿李南央曾经写过一篇回忆她的文章《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文章揭示了左的思想斗争的方法可以把人性压抑和扭曲到什么程度。离婚之后的十七年中范并没有重新组织家庭,李锐于1979年彻底平反之后,她又主动提出与李锐复婚,遭到李锐的拒绝和女儿的反对。范元甄于2008年辞世,享年87岁。
最近在第三遍温习杨继绳的一本书,名为《中国改革年代的……》,奉上意,后面的字还是略去了吧,省得领导不高兴、后果很严重。在这本书其中的一段,讲到后胡先赵年间,一位左派大员邓力群拟取赵而代之,值此危难之时,中组部副部长李锐拍马拧枪枪挑邓力群,撰万言书列邓力群的罪状给老头子,并且在最后附上了一条私人恩怨:邓力群在1945年的时候,乘人之危,睡了李锐的老婆。
老头子看了之后说了一句话:不要算旧帐。但同时也将邓力群打入冷宫,左派翻身之战就此落败。
李锐的老婆,就是范元甄,当年的延安四大美女之一。
随之在网上搜索范元甄的资料,才发现原来很早以前,她的女儿李南央就写了一篇名为《我有这样一个母亲》的文章,首先在香港见诸报端,然后又在国内得以发表;该文在国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李南央后又写了一篇答读者;2008年范元甄去世,李南央写了一篇《范元甄,走好》的文章。以上这些文章,在网络上都可以搜索的到,感兴趣的可以到搜索引擎上看一下。
范元甄这个女人,其成名也早:在学生运动的时候,就深得王明的赞誉;在重庆时期,更是为***夫妇所宠爱;在延安马列学院,连***都知道她的名字,路上遇到,都会说一声:“小范你先走”。论美貌,是“延安四大美人”之一;论学识和能力,也是众口赞誉,做到中央委员的其丈夫李锐就曾经亲口对女儿说过,范元甄能力在自己之上。
范元甄就像是一颗流星,在一刹那之间迸发出了无比耀眼的光茫,让所有人都为之侧目;而在光芒过后,则是永远的黯淡,沉寂在对往日追忆和对他人仇视的炼狱之中,永不得翻身。
范元甄当然是一个极其特别的例子,以她的能力、历练、交往,就算是做到国家领导人也似乎不是不可能的——在解放后,就一度享受到副部级的待遇,而当时,她只有三十几岁。这样一个人物,却因为两次为夫所累,最后直落得惨不忍睹的地步。恐怕这也就是为什么范元甄如此痛恨李锐的原因吧。
据说李锐当年也曾被评为延安四大美男子之一,其他三大美男都娶了丑女为妻,只有李锐和范元甄,可谓是郎才女才、郎貌女貌,简直是般配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他们成婚的那一年,范元甄只有十八岁。
李锐曾经是***的秘书,而***被打为反革命集团,所以李锐跟着遭殃也就在所难免。李锐这一年被当做特务隔离审查的时候,范元甄大概只有二十二、三岁,作为叛徒的家属,当然也要跟着遭殃,负责审查范元甄的,就是邓力群。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当时极其著名的二人通奸事件。因为此事,邓力群被专门开会批评做了检讨,主持会议的是***。范元甄将会后形成的决议誊写了一份,交给李锐保存,这也就是后来李锐向老头子写信反对邓力群所附的材料之一。在书中,杨继绳这样写到:李锐向本书作者展示了范元甄亲手抄写的这份材料,好一手工整秀丽的小楷!
解放之后极短的时间里,范元甄受到了重用,却马上又因为李锐的关系重新被党所抛弃。这两次事件彻底的改变的她的世界观,也直接导致了她对李锐的无比痛恨。
于是在之后的各种运动的风潮之中,她疯狂的揭发李锐、揭发亲人,甚至连女儿都不放过,她似乎已经变得只有党性,而没有了人性,最终得到了一个众叛亲离的下场。
从各种资料中,我们知道范元甄绝对不是一个容易被洗脑的笨人,比如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当年在延安举行辩论比赛的时候,作为反方的范元甄竟然把一堆马列主义的专家驳斥的哑口无言;再比如在***的时候,她也曾经对党所发表的一系列信息的真实性表达了怀疑,并且因此而惹来了牢狱之灾。
所以我相信她的女儿李南央的一个解释:范元甄之所以最后变得丧心病狂,是因为她真的害怕了,真的被运动整怕了,所以在延安的时候,要委身于邓力群以求自保;所以在以后的运动中,要靠不停的出卖自己的亲人甚至是女儿来换取一点仅存的安全感。
如果说这个时候她还有一点私心的话,我想就是可能她希望通过不停的告发自己的家人,来向党证明自己的忠诚,以及奢望换取一点政治资本。
就像后来王朔曾经说过的:必须要爬得高一点,不是为了利益,而是为了当石头砸下来的时候可以自保。范元甄正是这种心态,她已经被整怕了,为了自己,她完全可以毫不犹豫的把别人一脚踹下水,哪怕这个人是自己的亲人。
范元甄没有想到的是她的做法没有得到组织的赞许,她也从此一直没有再次得到闪光的机会。其实她并不知道,她疯狂逼着自己相信的那一套理论,组织也只是口头上宣传而已,没有人真的相信,当有一个人彻头彻尾的相信的时候,这个人也就没有了自我,一个没有自我思考能力的人,哪怕对组织也是没有用的废人。
所以李南央的另外一篇文章中引用一位中共大员的话说:他们的不断改造那一套,无非也就是宋明理学的翻版,专门制造大量口是心非的伪君子。
正如当我们理所当然的以为“毛***万岁”这个口号是人民自发喊出来的时候,***的秘书却告诉大家:这句口号实际上是老毛亲手写上去让别人喊的。乔治奥威尔在其鼎鼎大名的《1984》中所写的情节,在真实的情况下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个心口不一的人是需要不断的被改造的;而一个被改造成功的人又会变成一个废物,在这样一个两难的境地之中,只要毅力稍有不坚强,变态或者自杀就变成了仅有的两个必选项。让李锐坚持着活下去的那句话即使是现在看起来也还是让人毛骨悚然,***说:被***杀头不要紧,被***杀头可是要遗臭万年的。
遥想范元甄当年,英姿飒爽,青春少艾,天生丽质难自弃,怀揣一个梦想,冲破一个牢笼,成为那个时代女性的典范;且笑看天下群豪,纷纷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然而在不断的改造和批斗之中,命运却让她变得品性乖张凌厉、极尽变态,仇恨所有的人并为包括亲人在内的所有人遗弃,最终在孤独和仇恨中死去。
于是,我们相信我们看到的是童话故事的延伸:在一个华丽的转身之后,娇艳无比的白雪公主变成了那个头脑里尽是些谎言和仇恨、肚子里尽是些冰块、人见人厌的老巫婆。
父亲(编者注:李锐)在北大荒写给我母亲(编者注:范元甄)的信,是他和母亲自1938年到1960年的所有信件中,我最不忍读的。每每读来,总有一种胸口堵得难以喘息的感觉。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父亲青年时代起即献身于斯,并为之忘我奋斗了二十年的党,把他像垃圾一样扔了;一个男人对孩子、对家庭不能有些许贡献,而在饥饿、病痛的折磨下,不能自禁地开口向早已冷漠了的妻子要东西,而被她长篇累牍地挖苦;食品匮乏到臭豆腐连吃两块;每天两点起床,靠稀粥、豆饼果腹的躯干,一直要“扛”到晚上,拉稀拉在裤子里还要坚持下地;还要写交待材料……我还清楚地记得父亲从北大荒寄回家的那块漆黑的豆饼。
说是豆饼,其实是豆渣和草料的混合物。父亲在北大荒经历的那种“生产大突击运动”,对人的摧残,恐怕比《半夜鸡叫》里描述的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不同的是,那残酷的本质,被一层“美丽”的革命彩纸包起来了。年方42岁,在此之前未曾肩挑手提,不久前还被通报全党的“红旗秀才”,面对这种转瞬之间上天入地的变化,这种被彻底打翻,并踏上一只脚的屈辱、煎熬,需要多么大的力量才能支撑下去!?
会记住你一切告诫。投入劳动和集体生活之后,相信自己会很正常起来:鄙视过去,相信将来,42岁开始自己真正的生活。这几个月来,没有你的帮助,自己会陷在更糟糕的情况。(1960.4.19)
想着自己在党内廿多年,历史问题审查多次,这次仍让党为此麻烦,心中有愧,也确有感伤。……因之,我惟一能做的,是在此很好劳动,很好改造自己,使得我们将来能够面目一新,孩子们在成长时有好的健康的父母。(1960.5.12)
总之,用感情的态度,我会难以支持当前的生活。是认为自己必须改造,有错误,才能支持下来的。(1960.7.16)
从这些叙述里,我看到父亲赖以支撑的不仅仅是理性的力量,他那从热河办报时起屡屡见于信中的,一贯被母亲蔑视的,“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的能屈能伸的性格,此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认同***的话:“被***杀头不要紧,被***杀头是要遗臭万年的。
”参加革命廿余年的经历,继续为自己献身的事业奋斗的愿望,他与***荣辱与共无法割舍的情结,***是“真理化身”的现实,使他不会作出如烈女林昭、张志新那样以死抗争的抉择。
既已落难,就接受现实,不能钻牛角尖,不能彻夜辗转地苦痛,要曲起身躯,麻痹神经。要想捱过这个坎,必须得这样想:自己确实需要劳动改造,改造的态度得到党的认可,才能看到“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去的可能,才能看到一家人重新团聚、孩子们将来有个父母双全的正常成长环境的希望。
38年后的1998年,父亲在《黎澍十年祭》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黎澍认为***思想可以归纳为五点:……五是不断思想改造,实为宋明理学翻版,专门制造伪君子也。这第五点,大家都曾经挨整受罪,但都没有像他这样,联系古人假道学概括得如此高妙。
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在很多情况下是将被改造者推到消灭肉体的边缘来实现的:从肉体上摧残那些胆敢持异见的人,使他们在饥饿和非人的生活环境中丧失思考的能力,丧失做人的尊严,成为行尸走肉,以此根除思考的危险,得以实现思想的大一统。这在有些人身上确实达到了“彻底改造”的目的。我的母亲范元甄,就是最好的例子。
母亲那时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下放到青云仪器厂的热处理车间当工人(是体力劳动相对较轻的工种),平时住在工厂。刚刚两岁的妹妹全托在“六一”幼儿园,我在通县的小学住校,哥哥则由老阿姨照管。用父亲的话说,此时母亲不但要“领导家中四个人,还加上乌苏里江西岸一人”(1960.4.23),要给父亲找全国粮票,买东西,转关系,这些无疑是要看人冷面孔的事;自己在单位还要劳动,接受批判、审查,确确实实让她吃不消。
“同住的两对青年夫妇搬来没有?还相容吗?”(1960.5.25)父亲在信中问母亲。我家原来的单元是5间住房,大客厅是由两间屋打通的,又从隔壁的单元挖过来一间做父母的卧室。父亲去北大荒不久,水电设计院即分来两对新婚夫妇,占去我家单元内的两间。
原先隔出的一间屋子,此时也还上了,这样我们一家5口住打通的一大间客厅。但是厨房、厕所是3家9口人共用的,尴尬窘迫,可想而知。母亲与其中一对相处还好,另一对中,女的很厉害,母亲与她针尖麦芒。
母亲的生活条件此时与父亲相比仍是在天上,但精神上,对她这么一个原本就很别扭的人,这种情形不啻是地狱般的折磨。母亲的个性,在平时都是永远的不顺,这时就可想而知了。我现在完全可以理解,她那时为何开始拿我当出气筒,有时接到父亲的来信,会疯了一样地写出上百字的离婚信,逼着阿姨去邮局按电报发走;邮局拒绝发这样长的电报,她就逼着阿姨一趟趟地再去。
父亲是“以最大努力迎接考验,并胜利一关一关通过”(1960.4.25.)的精神准备着应付一切,母亲则是万难做到了。
在接到母亲的离婚信后,父亲简短地回了一信,说离婚现在不谈,待我回来后再说。之后两人的通信就完全中断了。自那以后,母亲的“革命”变得越来越“真诚”,越来越“彻底”。她不但把父亲的北大荒来信交给组织,还把夫妻间的枕边话全部抖搂出来,用这种大义灭亲的方式,证明自己受改造的程度,以期重新得到党的信任。
她在接下去的“***”中,揭发了父亲所有的朋友,凡有外调,她一律揭发,不管是自己的熟人还是朋友。记得大概在十八九岁的时候,我曾突然醒悟,完全理解了母亲那时的难处,原谅了母亲与父亲离婚后对我过分的辱骂甚至毒打,希望能与母亲亲近些。
但是,当我知道母亲原来对“***”持有与父亲相同的看法;当母亲一封封寄来对我的批判信,甚至向我的单位领导揭发我的“反革命言行”;探亲时领着我们早请示晚汇报;因为我男朋友的家庭出身有问题,让我断绝关系,在那以后,我心中残存的一点亲情彻底毁灭了。
延安整风后,母亲和父亲已屡屡发生思想分歧,庐山会议后,两人根本无法以任何方式求同存异了。因为“同”者——孩子、感情已彻底被“阶级”所替代;而“异”者——对***和党的路线的一些怀疑,其实曾经是“同”者,则万无共存的必要了。
她真的相信共同生活了20年,共同有了3个孩子的丈夫是反党分子吗?一定不是的,否则她怎么会在20年后父亲复出时动复婚的念头?但是她被***所显示出的绝对的威望、绝对的统治力震慑住了。她看清了,如果以前自己只是使用“阶级”作为让李锐俯首帖耳的武器,此时她必须将自己与李锐划分在两个不同的阵营,才能够生存。
她被眼前的一切吓坏了,她不能想象自己永远和别人合住一个单元(母亲在延安的信中,记述了不能容忍和自己的好朋友夏英喆共一窑洞);她不能想象自己永远做一个炉前工(母亲在东北糖厂的信中,记述了受不了顶班的生活);她不能想象自己经过廿年努力而得到的,三八式干部的优越生活条件和特权,从此不复存在(母亲信中屡屡流露出瞧不起工农干部和“旧”知识分子的态度,她在东北的信中记述了自己是如何虐待保姆);她的骄娇品格,决定了她根本无法面对这样的可能。
她明白要恢复从前的生活,要保住物质的和精神的地位,今后只有紧跟***,除此别无选择。
父亲在《黎澍十年祭》中还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论述:
“自由”是一切革命者所向往的最美好的理想,因为它是共产主义的最高境界,《***宣言》中说得很清楚。在革命斗争中多少烈士为自由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何以我们现在提都不能提,每一次有人提自由,就说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大动干戈加以反对?党对学术文化的领导,应当表现在保证有发表的自由,而不是动辄违反宪法,任意剥夺这种自由。
与母亲甘心放弃思考的自由、情愿承认自己没有怀疑领袖的权利,以求保存高级干部的地位和待遇相反,父亲的“放弃”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应该承认,父亲在被放逐到北大荒时对时局还看得不很清,想得不很透,他在信中议论道:
老头们基本是好的(由公社转农场,他们的生活和收入都显著下降,有点牢骚也不多谈,而且了解国家总的政策,也看远景,只是担心自己等不到)。昨天一郭老头将他手指给我看,像弯曲香蕉,从小累得无一指现能伸直。他们也从未吃过豆饼,也跑肚,无人说怪话。(1960.5.18)
以后准备每天利用晚饭后读书半小时到一小时,有计划读《***宣言》等几篇主要东西,另外读反右等汇集文件。报纸此间可以看到。(1960.7.1) 父亲年轻时所刻意锻炼出的吃苦耐劳的品格,自幼养成的勤学习性,使他在艰难的条件下,在像野人一样吞食一切可食之物时,仍不辍学习。
这使他得以不断充实、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在环境稍稍缓和,可以思想(注意是“可以”不是“允许”)时即可做锲而不舍的苦索。因之他的灵魂仅仅是做了生存所必需的弹性扭曲,而不是像母亲那样,发生不可逆转的塑性畸变。
父亲得以在受难中逐渐走向成熟,未被那庞大的机器碾造成伪君子。从本性的倔强好胜,而逐步成长为有胆气、有真知灼见的真君子,并逐渐谙熟了发表异见的艺术。40年后,对于***,对于中国***领导的革命,父亲有了深刻、理性的认识和剖析,他的思想闪烁出大智、大勇者的光辉。父亲是可以骄傲的,他从炼狱中走过,他从炼狱中获得令人羡美的人生。
昨天返队,如回到家里,给老头和同住者吃了节省下的馒头和饼干,都很高兴。(1960.5.18)
父亲的善良,是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在噩运中得以生存的重要条件。他与同伴刚刚相处半月不到,即结下了友谊。虽然自己也食不果腹,仍与人分享。父亲从别人的高兴中,无疑感受到了人情的温暖,这温暖释放出维持生命的热量,弥补了食物的不足。
父亲的坚忍、乐观、豁达,甚至还流露出一点得意——“我已买了副裹腿,现整天都打着(高中军训时学会打的,一天都不散)”(1960.5.18.),在顺境中也许并不重要,此时则显得性命攸关。如果将母亲换到父亲的位置,不知会怎样地苟且(延安整风时便发生了不应该发生的事),今天看到的,可能不仅仅是一个变形的灵魂。
1936年父母相识,1939年相爱,共赴革命圣地延安。两人又同出延安,至热河、东北,一起南下,后转业至新中国的工业战线,为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而工作。两人的出身、学历、经历,甚至相貌的出色都十分相像。吵吵闹闹,分分合合22年,一直到庐山会议,终于走到了尽头。
其后的40年,我得以亲眼所见,不用通过信件了解他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更感动于父亲的善良,父亲的与人为善,父亲的刻苦,父亲做事的执著。这些优秀的个人品德使他历尽沧桑,却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追求:共产主义的最高境界——自由。
作为一个丈夫、父亲,个人品德对他的妻子、儿女非常重要;作为一个领导国家的高级干部,好的个人品德则更不可或缺。我惋惜父亲的秉言直书不为人所容,而未能在更高的位置上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我庆幸母亲的官位仅至退休后的副部级待遇而不是更高,人民因此少一些可能的厄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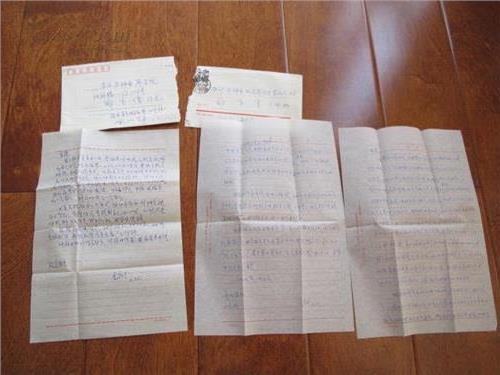


![[转贴]李锐范元甄何以离异?和邓力群有关系啊](https://pic.bilezu.com/upload/a/e8/ae88d29cd9de0265984ceca6384de453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