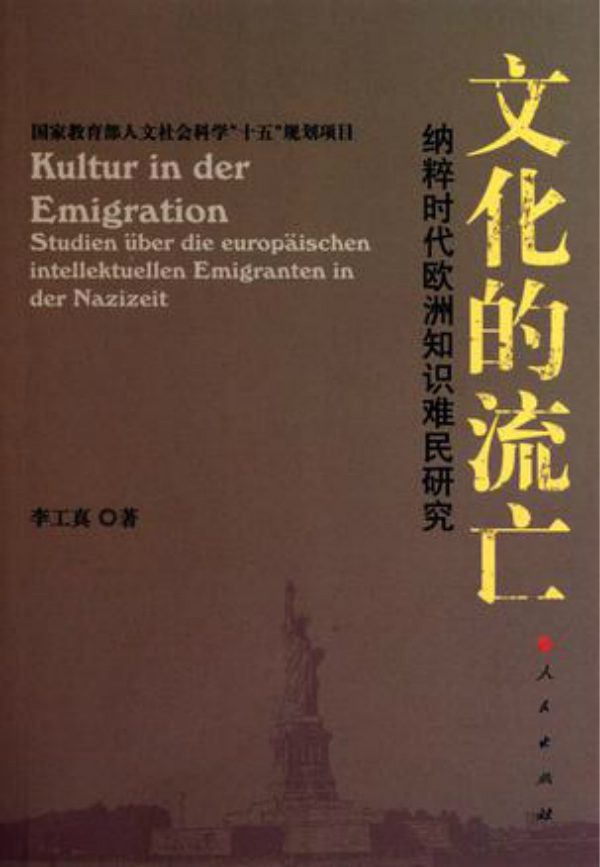李工真德国难民讲座 李工真:纳粹德国知识难民在美国的"失语性"问题
只有像大数学家理查德·库朗(Richard Courant)这样的人,由于被安置在只有1名数学教授(即他本人)的纽约大学里,才无法享受这种特权。这自然使库朗倍感授课上的语言困难,为此,他还特别"从讲演系请来一位家教,专门教他英语,并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不断地把他在交谈和阅读中碰到的口语用法记录下来。
这使他进步很快,没过多久,他便摸索出一种备课方法:先把精心准备的讲义用德语口述出来,然后再译成他所希望的'不错的英语'"。
(81) 至于其他的流亡数学家则要比库朗舒服得多,他们根本不用为本科生授课,尤其在那些流亡科学家相对集中的美国大学里,他们甚至完全不用为"语言上的孤立"而苦恼。例如,大数学家赫尔曼·外尔(Hermann Weyl)一走进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级研究所"就有这种感受:"在这里,讲德语的人和讲英语的人一样多。"(82)
由于职业上的语言障碍相对较小,这些讲德语的流亡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医学家们在进入美国高校后,很快就有了一种近乎于在"家"的感觉。正如德国流亡物理学家维克多·魏茨柯帕夫(Victor Weisskopf)所言:"到达美国后不久,我们便很快感受到,那些留在欧洲的人倒更像是难民!
"(83) 因此,他们完全能在美国继续他们的研究工作,并不断取得辉煌的学术成就。这不仅使他们与美国社会的"一体化"变得更为容易了,而且美国也从这些科学家身上获得了巨大的智力收益。
仅是在来自纳粹德国的第一代流亡科学家当中,就有13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的得主,除前文中提及的8位获奖者外,还有奥托·斯特恩(Otto Stern)、费利克斯·布洛赫(Felix Bloch)、尤金·P.
维格纳(Eugene P.Wigner)、汉斯·A.贝特(Hans Bethe)以及马克斯·路德维希·德尔布吕克(Max Ludwig Delbrück),这5位都是在流亡美国后获奖的。
(84) 而在数学领域里,赫尔曼·外尔、卡尔·路德维希·西格尔(Carl Ludwig Siegel)与约翰·冯·诺伊曼一起,很快就将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级研究所"变成了"世界纯粹数学中心",理查德·库朗则将纽约大学的"库朗研究所"建设成了"世界应用数学中心"。
"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个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并在今天广为人知的口号,实际上是当年讲德语的流亡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医学家的典型口号。而美国因为这些流亡科学家的到来,终于成为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得主最多的国家和"数学的新麦加"。
五、流亡艺术家的"失语性"问题
在语言问题上,流亡音乐家和造型艺术家无疑是所有知识难民中最为幸运的人。尽管他们同样面临了"失语性"问题,在与美国人交往的日常生活中也无疑都是"结巴",但由于他们的作品本身就是一种"天然的世界语",因而几乎感受不到职业语言上的障碍问题。
首先是那465名流亡音乐家,他们成为在美国最快安顿下来的人。著名音乐史专家博里斯·施瓦茨(Boris Schwarz)这样写道:"被迫流亡的音乐家的运气看来要比那些演员、作家和科学家好得多,因为音乐本身就是世界性的语言。
一位音乐演奏家只要有乐器在手,就可以在巴黎、纽约等地演出并能得到理解,根本没有进行口头语言交流的需要。歌唱家几乎一直就是天然的多种语言的掌握者,作曲家更能去改变各民族音乐兴趣和音乐传统之间的那些细微差别,因此,富有创造力的音乐家在远离他们的祖国时,是能很快地适应新形势的。"(85)
这些来自西方音乐传统故乡德国的流亡音乐家,不仅活跃在美国的音乐舞台上,还帮助美国高校建立或发展起音乐学专业。例如,20世纪最著名的作曲家、"无调性音乐"的开创人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先后被聘为波士顿马尔金音乐学院、南加州大学音乐学院和加州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并在美国新一代作曲家中产生了强烈影响;大作曲家保尔·欣德米特(Paul Hindemith)一手创办了耶鲁大学音乐学院,并在复兴"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代"的音乐风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斯特凡·沃尔帕(Stefan Wolpe)先后任费城音乐学院、北卡罗来纳黑山学院以及长岛学院音乐教授,素以教授作曲法而著称;而恩斯特·克热内克(Ernst Krenek)创办了瓦萨学院、哈默莱学院的音乐系,培养了许多美国著名的作曲家;卡罗尔·拉特豪斯(Karol Rathaus)则创办了纽约城市大学女王学院的音乐系,并引入了一套完整的作曲法课程。
正是由于他的努力,这所大学拥有了美国东海岸实力最为雄厚的音乐系。(86) 总之,由于音乐语言特有的"国际性"以及美国在这一领域的落后性,讲德语的流亡音乐家在美国高校中轻易地克服了职业语言上的障碍,成为音乐学这一特殊的艺术学科的创办人,以及教学、研究工作的主要力量。
如果说歌唱家、音乐演奏家和作曲家之类的音乐家是靠听觉艺术为生的话,那么画家、雕塑家、建筑设计师之类的造型艺术家就是靠视觉艺术为生的人,因为绘画、雕塑、建筑这类造型艺术是首先建立在视觉效果的基础上的。即使是从事教学工作,这些造型艺术家也是"从物质的基本特性、材料的形状、直观的结构以及简单的空间关系对生理和精神产生的效果出发,来进行课堂教学设计的"。
(87) 例如,像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路德维希·米斯·范·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马塞尔·布罗耶尔(Marcel Breuer)、拉茨罗·莫何里-纳吉(Lgáztó Moholy-Nagy)、瓦尔特·彼特汉斯(Walter Peterhans)、路德维希·希尔伯斯海默(Ludwig Hilbersheimer)这些"世界级"的德国流亡建筑设计师,也同样活跃于美国高校之中。
格罗皮乌斯和布罗耶尔执教于哈佛大学,米斯·范·德·罗、彼特汉斯和希尔伯斯海默执教于伊利诺斯技术学院,莫何里-纳吉则在芝加哥创办了自己的建筑学院。
他们在美国高校的课堂上从未感到有太大的语言障碍,因为他们"只需掌握英语中最简单的过渡性语言,就能将魏玛时代现代主义的'鲍豪斯建筑风格'传授给他们的美国弟子"。
尤其是那位被誉为美国"摩天大楼奠基人"的米斯·范·德·罗,"甚至在流亡美国后从没有努力学过英语,因为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人专门为他做翻译"。(88)
在296名流亡造型艺术家的行列中,有100多人属于流亡摄影师,他们从纳粹德国到美国新家园的迁徙以及经济上的过渡也进行得非常顺利,而这首先要归因于摄影行业的视觉传播特性和国际流动性。早在魏玛时代,由于在光学、精密机械、化学等领域中的世界领先地位,德国在摄影器材和显影技术方面都是国际上最先进的,加之1920年代"魏玛文化繁荣"中焕发出来的自由创造力,因而德国在图片新闻报道方面一直引领着世界的新潮流。
当这些摄影师在1933年后流亡到美国时,恰好赶上了美国新传播业兴起的时代。
美国此时正急需欧洲、尤其是德国在数十年来积累的技术和经验,而他们的职业特点决定了他们极少面临文字记者必然会遇到的语言问题,只需用不断的影像交流,就能提供即时的世界性认知。
因此他们在美国传媒中如鱼得水,不仅推动了美国的新闻摄影,还开创了时尚摄影和战争摄影,创办了《图片通讯社》和《生活》杂志,并为众多的美国报刊杂志提供了大量引人注目的名人、地点和新闻事件的图片。(89)
初到美国时,流亡摄影师们往往是从拍摄名人肖像起步的,不少人立即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其中最著名的有洛特·雅可比(Lotte Jacobi)、菲里普·哈尔斯曼(Philippe Halsman)与吉泽勒·弗洛伊德(Gisele Freund)等人。
雅可比专门为诸如库尔特·魏尔(Kurt Weill)、洛特·伦亚(Lotte Lenya)以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样著名的流亡科学家拍摄肖像,这些作品立即被广泛复制,并成为20世纪30-40年代的经典摄影作品。
她拍摄的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研究所里休闲的照片,在1942年被收入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20世纪肖像展"中。(90) 哈尔斯曼长期流亡巴黎,1940年6月法国沦陷后,通过爱因斯坦的帮助流亡美国。
利用新客观主义和立体主义的欧洲传统,他拍摄的名人肖像在美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仅是《生活》杂志就刊登了他拍摄的101张封面照。(91) 而弗洛伊德拍摄的人物肖像作品也被《生活》、《时代》杂志频频刊登,她的名字在美国几乎无人不晓。(92)
许多流亡摄影师很快就在美国开办起自己的摄影工作室,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来自奥地利的流亡摄影师艾伊克·波利策尔(Eyic Pollitzer)。他在纽约开办的摄影工作室生意十分红火,并为许多杂志社、出版社以及纽约市博物馆和图书馆提供了大量照片。
(93) 正如吉泽勒·弗洛伊德所言:"就社会功能而言,照片是当今最重要的大众媒介,因为没有哪样东西能像它那样对所有的人都具有说服力或接近性。照片远远不止是一种提供信息的方式,我们还能借助照相机来表达我们的思想。在艺术的等级中,它最接近于一个翻译。"(94)
除这些流亡音乐家和造型艺术家外,还有一批流亡艺术家在语言问题上经历了"先苦后甜"的过程,这就是那些专门从事舞台艺术的话剧和电影演员,以及编剧、导演、制片人之类的文化流亡者,其总数高达581人。讲德语的话剧和电影演员属于靠语言的魅力和表演来打动人心的人,但他们在流亡美国后,即使努力地学习英语,也由于其口语中不可避免的方言色彩,而无法发挥他们的表演才能。
(95) 那时,他们是多么怀念那个刚刚过去的"无声电影的时代"呵!
然而他们的"失语性"问题,却在1941年12月7日之后意外、幸运、迅速地得到了缓解。由于美国的参战,好莱坞的电影公司为适应市场需求,开始生产一系列的反纳粹影片,急需雇佣大量的德语演员,而他们纯正的德语口语非常适合扮演这些角色,因此,他们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反纳粹影片中。
对好莱坞产出的100部反纳粹电影片的调查表明:"90%以上的影片中有讲德语的演员出现,84%的影片中他们扮演了具名的小角色,54%的影片中他们扮演了主角和配角。
全部加起来,几乎所有的130名讲德语的流亡演员都在反纳粹影片中获得了工作机会。"(96)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在影片中很少扮演德国难民或流亡科学家,更多扮演的是"纳粹分子",即"他们的撒旦"。(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