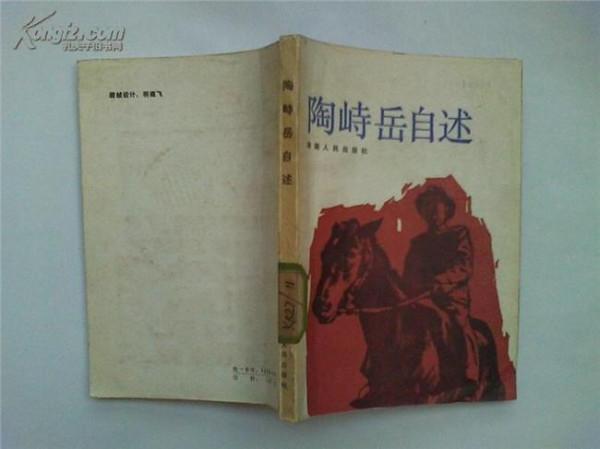夏尔巴人的平均寿命 我知道的夏尔巴人和他们的命运
的确,那详情知之与否又有什么区别?我只要知道认识的几个夏尔巴小伙子为了生活,在艰险的山途中倒下了就足够了。这些遇难的夏尔巴人很像看不见的丝线穿着的珠子,谁能猜得出下一个待穿珠子的模样?

在不可逆的时空,“如果”是没有意义的。当喜玛拉雅群山离我远去,时间尚未抹去的记忆还能使我记起这幅画是能勾勒清楚的,虽然它饱含着许多痛苦和伤感,可由此也使我清楚地意识到,那个支撑他们面对一切艰险的目的。

三年前,在珠峰前进营地许多个风雪交加之夜,我常与藏族老队员嘎亚等人围着煤气炉聊天,谈他们自己,也谈夏尔巴人,在夏尔巴人中,他们谈论最多的是27岁的小伙子昂·拉克巴。这是一个登山天赋惊人、性格开朗的小伙子,但嘎亚并不喜欢他,因为在他天马行空的个性中,似乎非常缺乏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和情谊。这不仅是嘎亚一人的看法。

4月下旬,三国登山队突击队名单排定,像所有记者都很难摆脱“明星意识”一样,我们也难免俗。一日,中方记者把昂拉克巴当作明星请到帐篷里时,戏剧性场面出现了,在一群夏尔巴队友的簇拥起哄中,拉克巴红着脸,不知所措进了中国记者的帐篷。登山十多年,拉克巴接受记者采访,这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但拉克巴开朗的天性还是占了上风,聊了一会,他就故态复萌了。
“我想想参加你们中国队!”
“为什么?”
“你们的队员登顶有奖金啊。”拉克巴大笑起来。
真说不好那天究竟是谁在采访谁,拉克巴不断反过来向中国记者发问,中国人的婚姻风俗了,中国队员不登山时干什么等等。
拉克巴的笑声极富感染力,它尽情得近乎放纵。采访这样的人对记者来说真是快事。但更令我难忘的还是他的身世——多少代夏尔巴人生活的缩影。
“我曾陪同梅斯纳尔登上过世界第四、第五高峰的洛子峰和巴卡鲁峰。”
梅斯纳尔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14座8000米以上山峰攀登的意大利登山家,并首创无氧攀登珠峰,他的一系列成就为他赢得了“登山皇帝”的桂冠。
本以为拉克巴会以很荣耀的口吻谈谈与登山皇帝共同攀登雪山的经历,谁知大谬不然。
有一年,梅斯纳尔在尼泊尔登山,原先雇佣的夏尔巴高山协作突然患病,拉克巴是作为补缺为一家高山旅游服务公司推荐给梅斯纳尔的。起初梅斯纳尔看到矮小的拉克巴还面露不满,但当拉克巴在一日之内从6000米到8000米营地进行了两次往返运输后,梅斯纳尔被震骇了,拉克巴叙述说:“就是从那时起,梅斯纳尔每次来尼泊尔登山,都指名要我陪同。”
“据说梅斯纳尔每登一座山,都会出版一本书,他在书中是否提到过你?”
“不会的,他连书也不会寄一本的。我们身强力壮时,他从不给我们拍照,一旦生病,却会拍个不停。他想以此显示比我们强!”
这就是夏尔巴人的宿命?为了生活,他们几乎每人都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为了生活他们踏遍了喜玛拉雅南麓的群山。但光荣不属于他们,只属于他们雇佣他们的外国登山者。
“梅斯纳尔当然是个了不起的登山家,但他登山常常是只背相机步话机,有时不寒而栗要我们在前边开路,只是他手中才有步话机,所以他永远是‘第一个登顶’。”拉克巴又大笑不止。
这时,帐篷里的中国记者都笑了。像拉克巴一样开心。
为了能得到雇主的雇佣,拉克巴和他的同胞们都必须充分展示自己的高山活动能力,只不过拉克巴表现得更突出而已。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是夏尔巴人,也没有忘记夏尔巴人的巨大牺牲。这才是完整的不该被遗忘的历史
“你是否想过超越梅斯纳尔呢?”
“太难了,他有赞助有后援,我没有。再说,我喜欢登山也不怕死,可我的父母早亡,家中还有姐弟需要我照顾,总登山难免会出事,一旦出事,他们怎么办?我想再登几年,挣够了钱就去做生意了。”
这时的拉克巴在我心目中不再是个只会炫耀二头肌的楞小子了,他承担着着一个家庭的责任,这个夏尔巴人在“历史的规定”中,显示的是那么热爱生活,充满自信。
拉克巴在接近我们的采访时,已经离家一个月了,他说他想家了,说着,他用手向珠峰的方向指了指说:“快了,过几天,翻过这座山,我就能回家了。”
5月5日,中日尼三国联合登山队12名登山队员到达“天庭”,拉克巴与中国藏族队员次仁多吉、日本队员山田升从北坡登顶,从南侧下山,成为历史上第一批跨越珠峰的人。
这个活蹦乱跳的小伙子竟走了,拉克巴欢快的形象强烈抑制住了我悲悯的冲动。在同样的境遇中,我几乎无法肯定自己能像他一样充满自信,笑口常开吗?
就在给昂·索那拍照那天,一只足球被抛到绒布冰河上,中日尼三国队员在冰河——世界海拔最高的足球场上,展开了一场忘情的、阵线混乱的大战,这只足球就是夏尔巴人带来的,它带来的狂歡节般的气氛,狂歡中,满场飞奔大呼小叫得最欢的也是夏尔巴人。
在永久雪线,这种狂欢不是表演欲望能营造出来的,它来自生命中的真正激情。没有这种激情,如何判定一个人真正像一个人那样生活过呢?
夜深了,卡桑说他要赶公共汽车回学校,我送他去车站途中,他又说起自己的选择,本来他已经考取“托福”,可以公派去美国学机电专业,但最后他还是决定自费来中国学医,这样将来会有更多的用武之地,但因此他也要承受很大的经济压力。
卡桑登车离去了,正像南国朋友介绍信说得那样:“卡桑为人真诚坦率”。
感谢我的南国朋友,他的这封信让我心中又荡起了遥远的来自天庭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