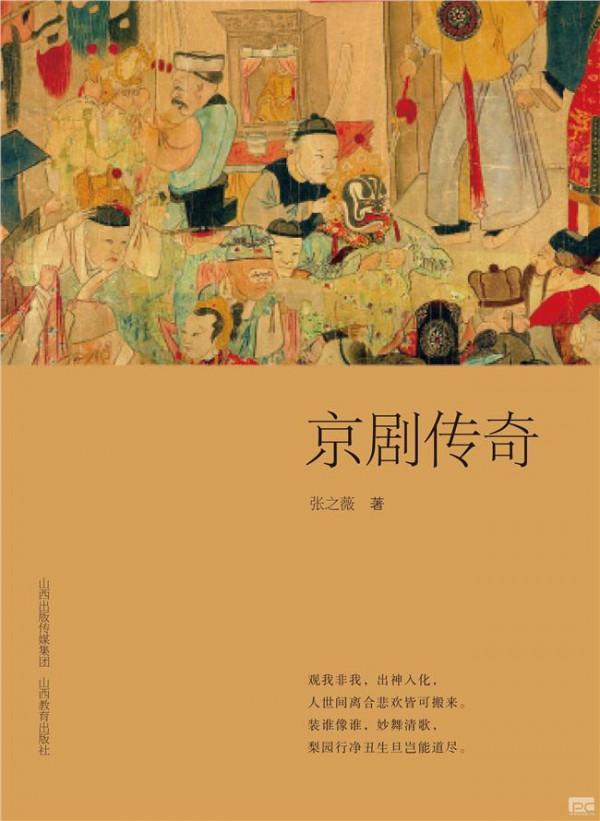合肥六中吴兴国老师 专访跨界表演艺术家吴兴国:我恨我 我也爱我
2011年8月,吴兴国将携他10年前的旧作《李尔在此》参加爱丁堡戏剧节,吴兴国一人独演《李尔在此》剧中的十二角。”——吴兴国 吴兴国在《李尔在此》中,打通生旦净末,一人独演12个角色。
石岩
专访跨界表演艺术家吴兴国:我恨我,我也爱我
吴兴国 艺术家 表演 1986年 七等生 Mokwha 表演艺术家 李尔王 爱吃 跨界 欲望城国 吴国秋
专访跨界表演艺术家吴兴国:我恨我,我也爱我
专访跨界表演艺术家吴兴国:我恨我,我也爱我
演出
2011年8月,吴兴国将携他10年前的旧作《李尔在此》参加爱丁堡戏剧节,吴兴国一人独演《李尔在此》剧中的十二角。今年爱丁堡戏剧节的主题是“到遥远的西方去”,这是爱丁堡戏剧节创办63年以来第一次聚焦亚洲艺术,入选四个剧目中只有两部是完全由亚洲艺术家制作的,一部是韩国Mokwha仓库剧团的《暴风雨》,另一部就是吴兴国的《李尔在此》。
“我知道传统的精致和丰富。我要找西方,就找门当户对的。”——吴兴国
吴兴国在《李尔在此》中,打通生旦净末,一人独演12个角色。 (Dirk Bleicker/图)
看到吴兴国,你最先注意到的是他脸上的皱纹。他58岁,有很大的眼袋,眉毛不浓不长,却好像要飞入鬓角。每当他要强调什么而瞪大眼睛时,额头上就会拱出深长的皱纹。他的嘴唇很薄,天生一副吃开口饭的精明利落,不过从鼻翼处牵扯出两条很深的皱纹像括号一样把削薄的嘴唇囊括其中,平添一股冷峻,而且让你产生一种错觉:英挺的鼻子下面一直挂着一副髯口。
他演过中国五千年历史上形形色色的男一号,从庄子、屈原,到诸葛亮、李后主、林冲、秦琼、岳飞、袁崇焕、范仲禹、蒋介石……他演的《霸王别姬》让法国观众认为自己在看希腊悲剧。
他曾站在世界级的舞台上,用生旦净末丑演绎《麦克白》、《暴风雨》、《李尔王》、《哈姆雷特》、《奥瑞斯提亚》、《等待戈多》。他被法国阳光剧团艺术总监亚里安·莫努虚金称作“伟大的表演者”;因为对莎翁剧目的精彩演绎,他被英国《泰晤士报》比作劳伦斯·奥利弗。劳伦斯·奥利弗饰演过莎士比亚所有重要角色,是20世纪公认最伟大的莎士比亚戏剧演员,并曾11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提名。
他的皱纹与其说是岁月的痕迹,不如说是职业的痕迹。生旦净末丑的表情已经像晒图一样藏进吴兴国的皱纹里,只等着感光显影。
1986年12月10日,《欲望城国》在台北首演。(刘振祥/图)
小兵立大功
“我在这里谈创新,可我是从传统出身的。我可以随时唱一段老戏码,但其实我已经二十年没碰它,那种感觉就像犯人在监狱里关了二十年,突然被放出来。”2011年5月,吴兴国在新竹交通大学和台北医学院演讲时说。
此前一年,吴兴国跟书画家张光宾、作家七等生、作曲家赖德和一起获台湾“国家文艺奖”。四位获奖者没有一个是守成者,评论家们说,七等生的小说是写给一百年后的人看的。而“国家文艺奖”那尊并不沉重的奖杯也是“京剧逆子”吴兴国第一次获得台湾主流文艺界的一致承认。此时距离他第一次在台北文艺界掀起强烈震动,已经过去25年。
1986年12月10日,《欲望城国》在台北社教馆首演。苏格兰将军麦克白变成东周时期蓟国大将敖叔征,“欲望”代替了京剧惯常的忠孝伦理,成为贯穿始终的主题。
唱腔大体还是皮黄,可是已经没人能分清敖叔征究竟是武生、老生还是花脸;旦角没有水袖,穿起宽袍大袖带裙撑的大摆裙;手眼身法还在,可留神细看,其中已经穿插进现代舞;像歌剧一样,这出“新编京剧”开场前有一分半钟以“悲壮”为基调的序曲,为这一分半钟,吴兴国和唢呐手刘春晖试过不下十个调门,吴兴国想要“悲壮”,刘春晖“能悲不能壮”。
“那天我迟到了,在外面等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一股人气和热浪扑面涌来,台上和台下一定是融合一气的。”台湾大学戏剧研究所教授王安祈至今记得《欲望城国》首演带给她的激动。
观众的反应千奇百怪。有人疑惑:旦角能这么演,这还叫京剧吗?有人怒:欺师灭祖!有人高调赞美:这是台湾三十年来最好的一出戏!不管褒贬,《欲望城国》让台北的文艺界沸腾了两个礼拜。林怀民说,这出戏是“小兵立大功”,王安祈说它肇始了一个“古典和现代混血、密不可分的时代”。
吴兴国并无意肇始一个新的时代,《欲望城国》酝酿三年始终笼罩在破釜沉舟的悲壮里:“不行就是我们这群人的问题,是这个剧种的问题,我们只能被时代淘汰。”
那是1986年,随着经济起飞和老兵退伍,国民党迁台之后一手扶持的“国剧热”已经渐渐退潮。吴兴国所在的台湾三大军中京剧团之一“陆光剧团”虽然还勉力维持着一个季度一次的公演和日常的劳军,但这种演出已经变成一个笑话:演的越来越漫不经心,经常不排练就上台;看的无滋无味,宁愿在剧团的演出记录表上直接盖戳,打车回家,也不愿坐在台下受罪。
京剧曾是别人强加给吴兴国的繁华旧梦,当他终于把这个梦做成他自己的,成为舞台上的一只虎一条龙,却发现戏台子底下是空的。
从吴国秋到吴兴国
吴兴国原名吴国秋。读过西南联大的母亲给不到一岁就没了父亲的儿子取这个名字,背后的意思显而易见:“国家多事之秋”。
父亲没留下一张清晰的照片,一段完整的生平。只有一次,母亲把他和哥哥从“国军先烈子弟教养院”接回家,特意炒父亲生前爱吃的菜,炒到一半,锅飞了起来。吴国秋不知道这个带着鬼气的细节,是不是母亲忧伤的想象,他没找到机会问。那个曾经“晚上拉着妈妈辫子才能安心睡觉”的小男孩,一生跟母亲呆在一起的时间只有五年,大部分还是在三岁以前。
11岁,吴国秋被母亲送进复兴剧校,此前,他读过“国军先烈子弟教养院”和宋美龄为大陈岛遗孤办的华兴小学。
华兴小学在台北阳明山上。吴国秋读不进书,整天坐在山坡上想家,“老师叫背《出师表》,背不出就打手板。”惟一爱上的课是音乐课。因为是宋美龄办的“窗口学校”,华兴的孩子经常有机会陪蒋介石夫妇去教堂唱圣诗。吴国秋声音最响亮,音乐老师告诉妈妈:这孩子声音很好,可以叫他去国外学声乐。妈妈苦笑。
从“华兴”毕业时,有人建议把吴国秋送到复兴剧校,“管吃管住,能学一技之长,只要扛得住打。”妈妈问吴国秋的意见,吴国秋不说话,沉默的潜台词是:“反正我也不能在你身边,你要养活自己,你把我送到哪里就是哪里。”
复兴剧校是后来的台湾歌星陶喆的外公王振祖创办的。王振祖被称为“票友界的梅兰芳”,当年蒋介石被逼在庐山下野的时候,王振祖特意带着戏班到庐山为他演出。按照“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口号排序,这个学校的第一届是复字班,吴国秋上的第二届是兴字班,“吴国秋”从此变成“吴兴国”。
复兴剧校条件很差,学生们饿得晚上去食堂偷馒头。练功练不好要被打,一个人练好而别人练不好也要被打,老师们相信这样能凝聚团体意识。因为怕被打,吴兴国每天埋头练功,来不及想喜不喜欢。剧校念到第三年,校长王振祖再也无力支撑,一度闹到要自杀。老师们有时吹牛他们大陆演一个晚上可以挣多少金条,买多大的四合院,对吴兴国来说,这简直是《一千零一夜》。
身在高雄的母亲想念在台北念书的儿子,经常写信来,谁也没有吴兴国家信多。信常被同学借去看,有人看过之后不还,吴兴国一怒之下把满满一书包信全烧掉。
烧信后来成为吴兴国一生的遗憾:“我妈是军人子弟,我外公是一个将军,国共战争的时候留在大陆,我妈一个人逃到台湾。她年轻就会抽烟,抽到后来肺积水。那时候她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我一把就能把她抱起来。”
受伤、挨打、流汗、流泪的时候,穿着黑色制服、剃着光头的吴兴国会暗暗地恨妈妈,恨刚弥漫上来,他马上又明白,妈妈和他都没有别的选择,心马上变冷。“有一天,你发现你所有的眼泪,一下子跟你的戏剧结合了,跟你所有演的历史沧桑、悲凉人物全部结合。”那是吴兴国迷上京剧的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