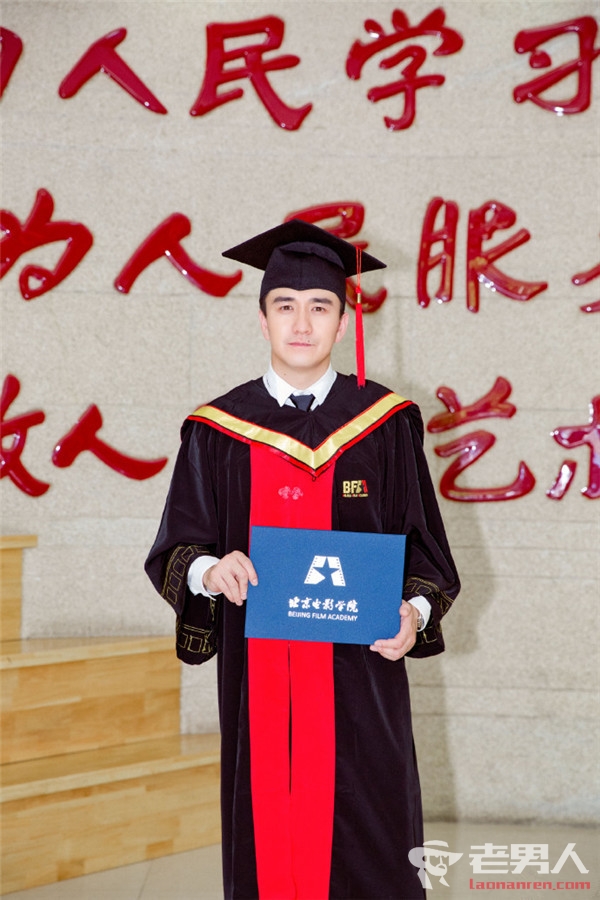约翰逊博士的字典 约翰逊博士和他的词典
奇迹与奇缘 ——读包斯威尔《约翰逊传》 作者,周泽雄 这本书,我今年大年初一才买到手,待到大年初五告诉一位书友时,竟遭到他轻微责难:“你应该当天就告诉我,在书店里,你应该第一眼看到‘她’时,就告诉我。”对一本书使用代词“她”,并不符合我的习惯,但既然是转述朋友的话,而我又相信,这位朋友肯定试图突破汉语声音上诸他不分的局限,坚持用“她”这个天地间最美丽的代词来称呼此书。
出于对我理解力的友情信赖,他只是没有改用笔谈方式特地写出那个“她”字罢了。
诗人在歌颂太阳的时候,通常不必担心因用词过猛而予人以肉麻之讥,本书正属于书籍星云中的恒星。 当然,我说的就是那本《约翰逊传》,那本属于包斯威尔也属于约翰逊,属于传记也属于文学,属于十八世纪也属于人类历史,属于英国也属于世界的《约翰逊传》。
她甫一问世,就以其纯粹灿烂的人文光芒,迎来了历代读者圣火传递般的虔诚礼赞。这样的杰作煞是罕见,竟然可以摆脱读者的忽视、批评家的质疑、同行的刁难和时代的流变,一出手就征服了世界,历两百年而不衰。
为一本书奔走相告,这份心情实在是久违了。犹忆八十年代初我们还在大学校园里时,倒是经常为学校那家临河小书店里新进了某本书,而逐个寝室地四处张扬。
然而今夕何夕,随着出版市场的空前繁荣,随着“出版”的神圣性早已被“做书”二字所取代,随着“某某某隆重推荐”的轻薄作派在坊间大肆风行,今天,似乎再也没有一本书,需要如我这等闲人为之特别奔走了。
除非,就是那本《约翰逊传》。 虽然辉煌如阳光,传递到地球上也需要8分22秒,但这本重要性凡人尽知、文学性万人共仰、趣味性众生倾倒的杰作,传递到中国读者面前,竟然花了两个多世纪的时间,实属匪夷所思。
作为对照,希拉里·克林顿女士的大著《亲历历史》,却是以超音速的速度送到中国读者手上的。我本着对希拉里参议员最大的善意,也只能在《亲历历史》和《约翰逊传》之间,找到这样两个共同点:其一、体裁相同,都属传记体;其二,中国读者读到的,均非足本。
若我为了表达对包斯威尔的起码敬意而不得不暂时置人间虚礼于度外,则将两书在任何意义上的合并比较,都是对希拉里女士的无上抬举,对包斯威尔先生的极端侮辱。 我不会自不量力到试图评论《约翰逊传》的程度,“她”属于经典,大概一百年前就不再属于评论界了。
关于“她”,我只想说几句与评论无关的话。我们没有读到足本,读到的只是所谓“哈泼诺版的浓缩本”,这多少让我不够过瘾。我以为,有些书是不妨出浓缩本的,如约翰逊博士的朋友爱德华·吉本厚达七卷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或约翰逊博士的后人詹·乔·弗雷泽的煌煌巨著《金枝》,因原著篇幅实在过于浩瀚,为了不致吓退非专业类读者,浓缩本实有嘉惠后生、厚泽广被之效。
《约翰逊传》则大有不同,她属于欣赏类读物,阅读快感伴随始终的读物,一卷读罢必会生出恋恋不舍之情的读物,斜刺里突遭此横空一刀,似有无端夺人之爱的嫌疑。举个未必不伦的例子,那相当于金庸迷面对删节版的《笑傲江湖》。
当然,笔者不识译事艰辛,对“原书上百万言的典雅、精致、正统英文”有可能给译者造成多么沉重的压力,完全不知轻重,所以,我仍然愿意将最大的谢意,献给台湾的罗珞珈女士。这本“一定要翻译出来的书”,正是这位自称“职业是家庭妇女”的台湾淑媛,在“先生太忙,孩子尚小,事无巨细,全要‘躬亲’”的情况下,翻译出来的。
以我这双外行人的眼睛看来,她译得非常出色。 拜读《约翰逊传》,我始终怀着一个困惑:为什么她会被一致公认为传记文学上的皇冠?书中到底有哪些既显而易见又难以仿效的杰出特质,确保她两个世纪来占尽传记文学的风光?当然,塞缪尔·约翰逊博士身为十八世纪英国文坛的祭酒,他那飞流直下的独特文风,舌战群儒的强健谈风,以及黑熊般任性的处世作风,作为传主,本身就极具观赏价值。
但这显然不是主要原因,甚至连次要原因也够不上。因为首先,人物的伟大并不能保证以他为题材的传记同步增辉,我们也没有按照人物等级排定传记优劣的习惯。
何况,历史上的英雄,也未必能够人均有份地享有一部传记。其次,不管我们如何赞颂约翰逊博士,公正地说,在人间伟人的万神殿里,他远非具备睥睨群英的资格,约翰逊博士的影响力充其量只能算得一时无二,而且该影响力的幅射范围还得大幅收缩,不仅必须地理上限定在英国,还得在人文分类上限定于文学领域。
否则,与约翰逊约略同时的哲学家大卫·休谟,那位曾经把康德从“独断的睡梦”中惊醒过来的哲学神童,岂有屈居人下之理。
若再把范围稍稍逸出国界,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端,他又将一头撞上伏尔泰和卢梭两位人文巨子。两相比较,孰轻孰重,可以说除了约翰逊本人,“地球人都知道”。约翰逊博士对伏尔泰曾经不乏微词,这甚至遭到了他的崇拜者兼传记作者包斯威尔的轻呵。
约翰逊认为卢梭“是世界上最大的坏蛋之一,一个无赖,他应该像以往一样被逐出社会”。这话听在今天任何一个人的耳朵里,都算不得一种高论了。 那么,且换一个方向来求证,是否《约翰逊传》的作者詹姆士·包斯威尔(1740-1795),具有人间第一枝生花彩笔呢?得了吧,那可更是谈不上。
如果约翰逊尚能列入第一流人物的高尚席位,包斯威尔充其量只具有第二流人物的资质和才情,何况,他除了这本传记和一册名叫《黑白地群岛之旅》的游记外,并无其他著述可供挂齿。
话虽如此,拜读《约翰逊传》之后,我对于该书“天下第一传记”的伟大声名,已不敢持丝毫异议了。我毫不犹豫地就想加入那支赞美该书的圣火传递队伍,即使排在末尾,吆喝的热情也不会减却分毫。
我关于“为什么她会被一致公认为传记文学上的皇冠”的困惑,事实上也立刻获得了答案。简而言之,《约翰逊传》的伟大,来自一种千年一遇的人间奇缘。
这是一份除洪福齐天的约翰逊外,人间并无第二个天才得以幸致的缘份。 本书传主塞缪尔·约翰逊博士(1709-1784),生前即享有英国一代文豪的声名,亦秉具一代奇才的异能,博闻强记,舌辩滔滔。他著述甚丰,其中以一介寒士身份历时三年独立完成的旷世巨著《英文字典》——作为对照,在当年法国,编纂一部类似的法文字典,需要倾四十名法兰西院士之力,且历时四十年,始克告成——更是一举奠定了他文坛“大独裁者”的尊崇地位。
在约翰逊的有生之年,这个地位从未被人撼动过。相反,举止怪诞、言语超常、具有一副巨无霸身材的约翰逊博士,还以源源不断的灵感,进一步夯实那座属于自己的青铜雕像的基座。他的生命既伴随着不可一世的文学成就,也始终充满着言语传奇。
他的天才是楚霸王式的,按包斯威尔一位叔叔的看法,他是“一个力拔山河的天才,生下来就为了揪住整座图书馆不放。”在他身上我们找不到一丝文弱文士或瘦诗人的特征,无论写作还是言谈,他都能使从自己心里发出的每一个文词,充满阳刚大美,他的文风独特到这种程度,以致英国人发现必须用一个专有名词加以概括:约翰逊体(Johnsonese)。
即使足不出户,即使履踪极少出现在伦敦之外,他照样有能力用自己出奇不意的格言、匪夷所思的警句,照亮伦敦的社交界和思想界。
甚至,他的种种怪癖,包括奇特的走路方式(有人曾这样形容:“约翰逊在街上走路时,只看到他的头在不断地滚,身子跟着移动,好像根本不用脚走路似的。
”),也给人提供了莫大的知性愉悦。一副黑熊般身坯的上方,偏偏长着一颗最为聪慧的大脑,这构成了约翰逊形象的扼要。 然而,令百年后的约翰逊博士喜忧参半的是,就历史影响而论,他以文化参孙之力毕生营造的那座文学宫殿,他全部著述的总和,在巍峨程度上竟还及不上詹姆士·包斯威尔先生那本以他为题材的传记。
这可真应了约翰逊自己说过的一句话:“每一个人的成就,和他当初梦想的成就比起来,都会气死人。”不过据我猜测,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天堂里的约翰逊博士,最终还是会喜大于忧。
要知道至情至性的约翰逊是一个在坟墓里都盼望着能收到信件的人,种种迹象显示,对于自己百年后的声名,他比任何人都更在乎。在他活着的时候,与任何人相比,他也从未显示过对一己声名的不在乎。
包斯威尔曾多次提到,“一般说来,约翰逊很喜欢接受别人的称赞”,而他对自己的学生、当时名满英格兰的天才演员加雷克的复杂感情(表现为“不容许除了他本人外,任何对加雷克的挖苦批评”,与此同时他本人却又对加雷克竭尽挖苦批评之能事),最能看出约翰逊所承受的声名之累。
约翰逊曾这样评论加雷克的成就:“你想想看,你曾提到过的那些显要人物,他们只能在远处听到掌声,而加雷克得到的喝彩,却是迎面而来,震聋了他的耳朵,加雷克每晚都是带着千万人的欢呼回家的”。
——不过,借助包斯威尔的传神文字,冥府中的约翰逊已不必再对自己的学生存有醋酸之情了,他身后赢得的掌声——虽说仍然只能在远处听到,还隔着阴阳两界——差不多都可以震裂他的棺木了。
关于传记,本书传主约翰逊博士持有一个观点:“除非作者能和那人一起吃喝玩乐,论古说今,否则就不够资格为那人写传记”。应该承认,这个观点惟一值得商榷的地方,就在于它过分正确了。
如果我们贸然加以认可,甚至将此视为撰写传记的入门条件,则人间已有的传记,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将被摒挡在外,不管它们的作者是司马迁还是普鲁塔克,是茨威格还是约翰逊本人。当晚年的约翰逊撰写《英国诗人列传》时,他同样不具备自己开列的条件,稍早些的《莎士比亚》,也是在“不够资格”的前提下写成的。
也许,为苏格拉底传神写照的柏拉图或色诺芬——尤其是色诺芬——才勉强够格。之所以“够格”前还要加上“勉强”二字,在于无论柏拉图还是色诺芬,与苏格拉底“论古说今”容或有之,“吃喝玩乐”则没到那个份上。
毕竟,两人是以“执弟子礼”的方式出现在传主面前的,而“吃喝玩乐,论古说今”,需要的却是一种大致平等的朋友关系。
准乎此,虽然古代帝王出征时总喜欢让历史学家随侍在侧,以便随时记录自己的丰功伟绩,但考虑到双方地位的悬殊,尤其考虑到帝王们几乎不可能有与御用史官“一起吃喝玩乐,论古说今”的雅兴,他们的记录,仍然要大打折扣,这也正是伏尔泰瞧不起路易十四的宫廷史官珀利松的原因。
我们注意到,与约翰逊博士打过笔仗的伏尔泰,这方面的观点却与他的对手完全一致。他同样认为:“要描绘某个首相(指马扎然)的性格,要说出他内心多么勇敢,或者多么软弱,要说出他怎样谨慎,或者怎样狡黠,必须和他朝夕相处。
”我甚至觉得,约翰逊的话只不过是说说而已,伏尔泰对自己的观点则虔诚地捍卫着。也正因此,伏尔泰对希腊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评价并不高,普鲁塔克的《伟人传》,在他眼里也只是“道德价值多于历史真实”而已。
可以想见,如果他读过司马迁的《史记》,评价大概也不过如此。因为他曾断然写道:“要描绘一个未曾一道生活过的人物,那简直是十足的江湖骗术”。
如果约翰逊关于传记条件的话不是说说而已,那么只有一个可能,这话他是说给包斯威尔听的。他为传记定下如此苛刻的标准,原本就不是为了自我鞭策,而是提醒那个老是追随自己的苏格兰小子,希望他打点精神,在自己百年后,写出一部惊天动地的杰作出来。
这就要说到传记作者包斯威尔与其传主约翰逊博士之间的美妙关系了。作为一名从偏僻的苏格兰来到伦敦的年轻人,包斯威尔就像十九世纪法国作家笔下那些从外省来到巴黎的年轻人一样,心中也是自卑与好奇交错,野心与幻想纷陈。
此外,他还有一个完全符合他这类人物身份的强烈爱好:热衷于结识天下英豪。虽然约翰逊“相识满天下”,但以人物的重要性而论,他那“列成名单,可能要厚达数册”的私人通讯簿,也许还及不上包斯威尔随意扳动手指提出的四五个人名,不必说,伏尔泰也曾经待包斯威尔如上宾。
在包斯威尔二十二岁初次见到约翰逊之前,“已经沉迷于他的书本和教诲中达数年之久”,当时,约翰逊博士的地位正如日中天。
不多久,包斯威尔就下定决心,打算在约翰逊博士百年之后,完成一部《约翰逊传》。这个决心一下就是二十一年。 有趣的是,这还不是一个秘密的决心,包斯威尔很早就向约翰逊表白了心迹,也可以说是当面向约翰逊征求许可,约翰逊则愉快地向他口头颁发了许可证书。
当包斯威尔询问,“如果他不嫌烦,又不嫌我太冒昧的话,我请求他将他生命中发生的琐事,巨细无遗地告诉我;他上过什么学校,何时上牛津,何时到伦敦,等等”,约翰逊表现出一反往常的和蔼,还表示“我们慢慢地,一件事、一件事再谈吧。
”考虑到约翰逊有着无比凌厉的目光和高不可攀的自负,他在答应包斯威尔请求之前,肯定已反复掂量了包斯威尔的能力和才情。
所以,他答应包斯威尔的请求,决非一时冲动,而只能视为一项极为审慎的决定。 包斯威尔除了对约翰逊有着最大的敬爱和忠诚之外,他还是一个格外善解人意的谈话伙伴。对于传记作者来说,没有比“善解人意”更为珍贵的素质了。
据译者介绍,他“能够将自己的思想语言,以最快的速度,转换到适应对方的思想和语言。因此,每当包斯威尔与人交谈,每次都能令对方感到,是在和‘另外一个自己’交谈似的,既轻松又自在”。结果,虽然约翰逊是一个极难讨好的人,一个嘴上毫不容情、从来不知何为积口德的舌辩大家,包斯威尔还是和他结下了深厚友谊。
那是一份长达二十一年的友谊,两人相处的时间,共计两百七十六天。就是说,平均两周不到,两人就见一次面。
其中一人长期住在伦敦,另一人的家则安在苏格兰。住在伦敦的那个人,论年龄甚至比住在苏格兰的那个人的父亲还要年长。约翰逊博士临终时,包斯威尔不在身边,据别人相告,弥留者一直念叨着包斯威尔的名字。这份念叨中的意味,说有多深长就有多深长,说有多感人就有多感人。
“吃喝玩乐,论古说今”,这个标准也是非常约翰逊化的。我们相信,凯撒不会提出这个标准,一生俭朴、被斯多噶派奉为精神远祖的苏格拉底,也很难认同这个标准。
但对约翰逊来说,“吃喝玩乐,论古说今”,差不多构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内容。约翰逊著述虽多,其中还不乏鸿篇巨制,但由于天生一股文化神力,他花在写作上的时间并不多,“他最杰出的一些作品,都是以一种狂热而横扫千军的快速力量完成的”。
约翰逊曾说:“我坐下来一口气写完480页,然后一夜失眠。”包斯威尔也曾纳闷:“我简直想不出他怎会有时间创作。……回想起来,每次我邀请他去酒店消磨时光,他几乎都没有拒绝过”。而约翰逊最具光辉的风采,往往也就在“吃喝玩乐,论古说今”的场合,这当儿他意气风发,咳金唾玉,四处寻衅,可以在一个晚上摆开四个或八个不同的论辩战场,再各个击破。
一席终了,他那些原本均非泛泛的朋友,头顶上已插满约翰逊语言军团的旗帜。
通常,这样的场合,是极难被一枝笔墨及时加以捕捉和描摹的,但由于包斯威尔在场,遂使咳唾不致随风飘散。包斯威尔甚至有这个能耐,可以一边成为交谈中的一员(为此,他免不了经常遭到约翰逊大肆嘲笑的命运),一边又用自己那套独特的速记法,记录下当天的种种交锋。
在约翰逊的鼓励下,包斯威尔还坚持每天写日记。如果约翰逊哪天发表了一通精彩绝伦的观点,他还会提醒包斯威尔,别忘了回家作业。 从来没有一位传记作者,与他将要记录的那个人,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
两人年龄悬殊,性情迥异,智力也不在一个等级上,与此同时却心心相印,很早就达成一项事关生命的重大默契。两人发生过争吵(通常以包斯威尔的忍气吞声为结束),也曾“手挽手在河滨漫步”;他们有过经济纠纷,也曾结伴出游。
他们深宵长谈,彼此都保留有通信副本,晚年的约翰逊甚至在家中为包斯威尔特地“准备了一间客房”。 约翰逊为传记文学制订的笔墨苛政,可以吓退每一个有志于传记文学的人,他的朋友包斯威尔却毫不费力地做到了。
当包斯威尔宣称:“我敢断言,在这部传记中所见到的约翰逊博士,将是有史以来,人类中最为完整的一个人”,他的底气并非来自文学上的抱负,而是相信,世上没有第二位传记作者,具有他的优势,曾经完全融入传主的生活。
他熟悉传主的一切,包括他的伟大与渺小,慷慨与自私,也正因此,《约翰逊传》成了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大孤例,一个无人可以仿效的榜样。我们从来没有在别的书中,读到如此真实又如此缤纷复杂的人物。文学上的奇迹,与生命中的奇缘,就此合为一体。 转自,猪头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