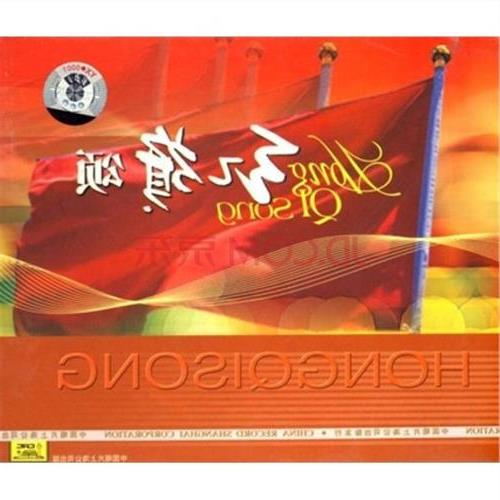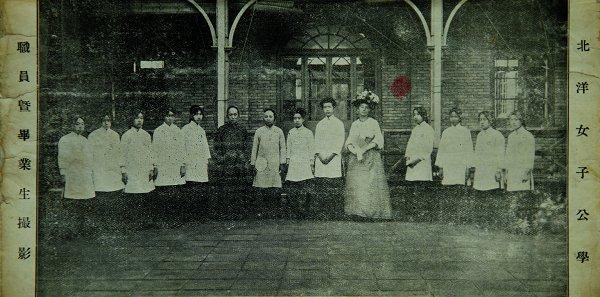【吕其明红旗颂】吕其明:新乐路上 写下《红旗颂》
◆当年吕其明就在这间朝北的小房间里奋笔疾书。 摄影 蒋迪雯
■本报记者 沈轶伦
1965年,在新乐路147号5楼朝北的小房间里,刚刚30岁出头的吕其明奋笔疾书。
在他的窗外,是上海旧日法租界的住宅、不远处是热闹的淮海路,充满异域风情的梧桐叶摩挲着,谈笑风生的都市青年在街上走过。但这一切都丝毫不能映入作曲家的眼帘。

他心中涌动的,是千千万万革命烈士鲜血染红的旗帜,是自己的父亲在英勇就义前写下的绝命诗,是自己10岁参加新四军后亲历见证过的战斗场面……短短一周,在新乐路公寓小小的房间里,他写就《红旗颂》。这是他献给父亲的赞歌、烈士的赞歌、红旗的赞歌……而这首曲子也将从这个房间开始,传唱至祖国大江南北。

新乐路往事
直至20世纪初,新乐路周边,还是人烟稀少,一片沟浜菜地,今淮海中路987弄一带,原称钱家荡。新乐路还是白茫茫一片宽阔河道,被称作“白洋河”,四周多为坟丘、菜地。居民集资在河上建桥,横跨今新乐路上海首席公馆与圣母大堂之间,取名“沈家木桥”。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法租界的殖民者越界填荡筑宝昌路(今淮海中路)、善钟路(今常熟路),至1914年后这里成为法租界的一部分。1932年,法租界开始扩张,公董局在此填河筑路,工程一直持续到1935年。
新乐路原名亨利路(Rue P.Henry),据悉取名于在与义和团一战中丧生的法国海军军官Paul Henry。短短的小路,曾是流落上海的白俄侨民的汇聚之所,其中新乐路55号,正是东正教圣母大堂。
圣母大堂建成于1936年2月,为典型的拜占庭建筑和俄罗斯东正教教堂风格的建筑,中间顶部为大的半圆穹顶,南侧一幢两层楼房,为神职人员住宅。以此为原点,周边入住大量外侨,也为社区注入“洋派”的生活气息,1934年起,在原新乐路街道范围内陆续建成新康花园、上方花园等。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豪绅巨贾、达官贵人、帮会头目以及外籍侨民,纷纷涌来这一地段造屋定居。杜月笙、何应钦等在此都曾拥有别墅,一时,这一地带成了繁华的商业地段和中上层人士集聚区。原新乐路街道并不大的范围内,就有花园住宅252幢、公寓52幢、新式里弄924幢、旧式里弄761幢、新工房36幢。
感受朝北房间的阴冷
但在1957年至1970年,入住新乐路的吕其明,感受到的不是十里洋场的“洋气”或“小资”,而是艰苦和阴冷。他与家人被分配入住新乐路147号5楼的公寓房,也是原来外国侨民的公寓。
这是一幢修建于1930年代的建筑,房屋内部的设计,全然西式。或许因为早年公寓的设计中,附带有锅炉集中供暖,因此就忽视了上海冬日的采光和供暖问题。
公寓内部结构设计上,分为一层楼四户人家,两户全北套,两户全南套。当时吕其明一家分到的是全北套公寓,即三间房间的朝向都是面北。而在上个世纪50年代,因为物资匮乏等缘故,公寓的锅炉供暖功能又已停用。因此每到冬天,三间小屋终日没有阳光,阴冷异常,晒出去的毛巾滴水结冰。
每年冬季,吕其明在房间内工作谱曲就格外辛苦。不仅必须要全副武装,把所有的大衣、棉袄都穿上,在室内坐着头上还要戴皮帽子,即便这样,还要冻得鼻涕直流。1961年,长期在这种阴冷环境工作的吕其明,又因为营养不良和工作辛苦的缘故,罹患哮喘病。但即便如此,他依旧视新乐路为其创作生涯的宝地。
1949年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后,吕其明的上海足迹,先后经过华山路范园、今上海戏剧学院内“新实验空间”小楼——昔日西餐俱乐部“台尔蒙”内。1951年赴京工作后,又于1955年回沪,先入住愚园路,后来在1957年被安排住到新乐路,一直到1970年搬到上海新村,并最终于1983年入住江宁大楼至今。
在新乐路的三年岁月,见证了吕其明创作过程的一个高峰期,一批传唱至今、家喻户晓的作品正是在那三间终日不见阳光的朝北房间里,被以极大的热忱和激情创作出来的。
触摸上海的光辉历史
1956年-1957年,在新乐路上,吕其明完成了电影音乐作品《铁道游击队》,由他作曲的电影主题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后来成为全国人民传唱几十年不衰的经典。1958年,他一年完成了七部作品,其中《铁窗烈火》这部电影,正是以1948年在上海工人运动中就义的王孝和烈士为原型。在烈士牺牲的土地上,作曲家写作这一部作品,也体现了吕其明对上海城市精神的理解。
上个世纪60年代,随着“上海之春”的出现,吕其明几乎每一年,都有新作品通过这一平台问世。1960年到1966年,他完成的电影音乐作品有 《六十年代第一春》《红日》《霓虹灯下的哨兵》《白求恩大夫》《大庆战歌》等。为了写出大庆油田中石油工人的奋战精神,他还去黑龙江实地下生活,住在草原的地窝子里,用原油燃烧的小炉子取暖,目睹工人为祖国献石油的澎湃激情,他为能参与这伟大的时代而自豪。
那时,上海音乐家协会党组是“上海之春”的权威领导机构,由贺绿汀、丁善德、孟波、黄贻钧、钟望阳、瞿维和吕其明组成。1965年2月,上海音协党组在研究各单位报上来的作品时,老前辈们建议让吕其明赶写一部作品,黄贻钧建议,曲名就定为《红旗颂》。
在兴奋和激动中,吕其明接受了这一艰巨的创作任务。“当时,我对歌颂伟大祖国的作品,向往已久。但题材太大,不敢轻举妄动。如果不是‘上海之春’,没有老前辈们推一把,就可能没有了 《红旗颂》。”吕其明后来曾这么说。
《红旗颂》以红旗为主题,描绘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情景。同样,它以宏伟庄严的歌唱性的旋律,表现了中国人民在红旗的指引下奋发向上的英勇革命气概。而在战火中成长的吕其明,对红旗的感情,更是比别人更为深厚。
才满10岁,吕其明就随父去淮南抗日根据地参加新四军,先后在二师抗敌剧团、七师文工团、华东军区文工团任团员。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新四军全部由皖江地区向山东撤离,曾担任安徽无为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的共产党员父亲吕惠生由于叛徒出卖,身份暴露,不幸被捕,同年11月就义时年仅43岁。
牺牲前,吕惠生在狱中写下绝命诗: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敌后,扰攘展民猷。八载坚心志,忠贞为国酬。且喜天破晓,竟死我何求!
这一年,吕其明15岁,他加入共产党,决定接过父辈们身体力行所树立起的信仰旗帜。当想到先烈在红旗指引下战斗的场面,和1949年在开国大典上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情景,无数往事涌上心头,在上海的公寓书桌上,吕其明选择单主题贯穿发展的三部结构,短短一周写就《红旗颂》。
《红旗颂》创作出来后,首先在上海电影乐团排练厅里试奏。后来经过前辈建议,《红旗颂》从15分钟删减成9分多钟,更精炼流畅。1965年5月,第六届“上海之春”开幕式上,《红旗颂》由著名指挥家陈传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电影乐团和上海管乐团联合首演。
嘹亮小号奏出以《义勇军进行曲》为素材的号角音调及主题音乐。紧接着,双簧管奏出深情旋律。中间的颂歌主题变成铿锵有力的进行曲。第三部分是主题再现,表现亿万人民尽情歌颂的情绪。尾声的号角雄伟嘹亮、催人奋进。台下的吕其明心中,也是心潮澎湃。
在新乐路,吕其明埋头创作,后来又谱写了一大批作品,同时,1959年到1965年期间他带职在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深造,攻读本科,学习了五年作曲、两年指挥。
从洋派的新乐路,到上音所在的小资的汾阳路,再到热闹的淮海路,住在这里的几年中,吕其明坦言一次也没逛街购物过。沿路风景对吕其明并无意义。那几年除了工作就是不舍昼夜地埋头创作,家里没有聚会,少有访客,在吕其明的印象里,几乎所有的同事在那样一个火热的年代,都以极高的热情投入时代的建设。
在上海漫长的冬天里,他裹着棉袄创作不止,哮喘病发,最后因为身体原因,吕其明一家被安排到上海新村居住。但回首新乐路的岁月,他感叹自己在那里度过了人生一个“如痴如醉的创作高峰”。而诞生于那间朝北屋子里的音乐,也曾陪伴几代中国人,成为人们共同拥有的红色旋律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