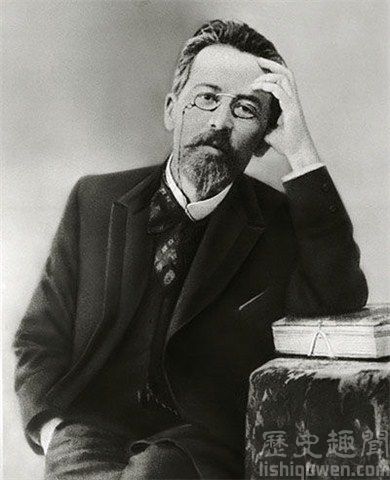契诃夫凶犯主要内容 惜别大家丨谢谢契诃夫 更要谢谢童道明先生
1904年1月17日,是契诃夫的四十四岁生日。莫斯科艺术剧院选择这一天首演《樱桃园》。演出前还为剧作者举行了祝寿仪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后来在《我的艺术生活》中记下了这个庆典的隆重但也沉重的印象:“在庆祝会上,他(即契诃夫)却一点也不愉快,仿佛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

在那个距今已有九十一年的莫斯科市区的夜晚,契诃夫预感到了他是在过自己的最后一个生日,但他未必会预见到《樱桃园》的长久的活力。
“活力”在哪?不妨先勾勒一下它的可以一下子梳理出来的故事头绪:为了挽救一座即将拍卖的樱桃园,它的女主人从巴黎回到俄罗斯故乡。一个商人建议她把樱桃园改造成别墅出租。女主人不听,樱桃园易主。新的主人正是那个提建议的商人。樱桃园原先的女主人落了几滴眼泪,走了。落幕前,观众听到“从远处隐隐传来砍伐树木的斧头声。”

无疑,《樱桃园》的意蕴联系着“樱桃园的易主与消失”这个戏核。但随着时代的演进,从这个戏核可以生发出种种不同的题旨来。在贵族阶级行将就木的20世纪初,由此可以反思到“贵族阶级的没落”;在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十月革命后,由此可以引导出“阶级斗争的火花”;而在阶级观点逐渐让位给人类意识的20世纪中后叶,则有越来越多的人从“樱桃园的消失”中,发现了“人类的无奈”。

在最早道出这种新“发现”的“先知先觉”中,就有比契诃夫晚生九年但比契诃夫多活五十五年的契诃夫夫人克尼碧尔。
她也是“樱桃园女主人”一角的最早的扮演者。在她去世前不久的20世纪50年代末,像是留下一句遗言似的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樱桃园》写的“乃是人在世纪之交的困惑”。

“困惑”在哪?不妨再挖掘一下剧本的可以一下子挖掘下去的故事底蕴:美丽的“樱桃园”终究敌不过实用的“别墅楼”,几幢有物质经济效益的别墅楼的出现,要伴随一座有精神家园意味的樱桃园的毁灭。“困惑”在精神与物质的不可兼得,“困惑”在趋新与怀旧的两难选择,“困惑”在情感与理智的永恒冲突,“困惑”在按历史法则注定要让位给“别墅楼”的“樱桃园”毕竟也值得几分眷恋,“困惑”在让人听了心颤的“砍伐树木的斧头声”,同时还可以听作“时代前进的脚步声”……
《樱桃园》是一部俄罗斯文化味道十足的戏剧。但在它问世半个世纪之后,随着新的“世纪之交”的临近,当新的物质文明正以更文明或更不文明的方式蚕食乃至鲸吞着旧的精神家园时,《樱桃园》这个剧本反倒被越来越多的人看成是可以寄托自己情怀的一块精神园地,这就是为什么近三十年来世界著名导演竞相排演这个戏的原因。
于是,《樱桃园》里包裹着的那颗俄罗斯的困惑的灵魂,像是升腾到了天空,它的呼唤在各种肤色的人的心灵中激起了共鸣的反响。其中自然也包括我们黑头发黄皮肤的龙的传人。
20世纪50年代末,旅欧华人作家凌叔华重游日本京都银阁寺,发现“当年池上那树斜卧的粉色山茶不见了,猩红的天竹也不在水边照影了……清脆的鸟声也听不到了”。而在寺庙山门旁边“却多了一个卖票窗口了”——告别已经成为营业性旅游点的银阁寺,凌叔华女士在她的散文《重游日本》里写下了自己的“心灵困惑”:“我惘惘地走出了庙门,大有契诃夫的《樱桃园》女主人的心境。
有一天这锦镜池内会不会填上了洋灰,作为公共游泳池呢?我不由得一路问自己。”
在“樱桃园”变成历史陈迹的时候,有《樱桃园》女主人心境的人,并不非得是女性,甚至也并不非得熟悉契诃夫的剧本《樱桃园》。50年代中期,当北京的老牌楼、老城墙在新马路不断拓展的同时不断消失与萎缩的时候,最有契诃夫《樱桃园》女主人心境的北京市民,我想一定是梁思成先生了。
古人留给我们一句“物是人非”或“物在人亡”的成语。所谓“倏来忽往,物在人亡。”现在人的寿命大大延长了,而“物”呢?反倒容易陷入“面目全非”或“面目半非”的窘境。这几年来,多少个博物馆的“半壁江山”割让给了现代家具展销会,多少个幼儿园“脱胎换骨”成了高档餐厅或卡拉OK歌舞厅。我们该在心中兴起“倏来忽往,人在物非”的感喟了。
时代在快速地按着历史的法则前进,跟着时代前进的我们,不得不与一些旧的但也美丽的事物告别。在这日新月异的世纪之交,我们好像每天都在迎接新的“别墅楼”的拔地而起,同时也每天都在目睹“樱桃园”的就地消失。我们好像每天都能隐隐听到令我们忧喜参半、悲欢交加,令我们心潮澎湃,也令我们心灵怅惘的“伐木的斧头声”。
我们无法逆“历史潮流”,保留住一座座注定要消失的“樱桃园”。但我们可以把消失了的、消失着的、将要消失的“樱桃园”,保留在我们的记忆里,只要它确确实实值得我们记忆。大到巍峨的北京城墙,小到被曹禺写进《北京人》的发出“孜妞妞、孜妞妞”的声响的曾为“北平独有的单轮小水车”。
谢谢契诃夫。他的《樱桃园》同时给予我们以心灵的震动与慰藉;他让我们知道,哪怕是朦朦胧胧地知道,为什么站在新世纪门槛前的我们,心中会有这种甜蜜与苦涩同在的复杂感受;他启发我们快要进入21世纪的人,将要和各种各样的复杂的、冷冰冰的电脑打交道的现代人,要懂得多情善感,要懂得在复杂的、热乎乎的感情世界中入徜徉,要懂得惜别“樱桃园”。
内容选自《一只大雁飞过去了》
丨作者
童道明:生于1937年,江苏省张家港市人,现居北京。著名戏剧评论家、剧作家、翻译家,也是契诃夫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论文集《他山集》,专著《戏剧笔记》《我爱这片天空:契诃夫评传》,散文随笔集《惜别樱桃园》《俄罗斯回声》等,戏剧创作包括《赛纳河少女的面模》《我是海鸥》《秋天的忧郁》,其译著包括《梅耶荷德谈话录》《海鸥》《万尼亚舅舅》《樱桃园》等。
童道明先生于2019年6月27日早上仙逝,享年82岁。童道明先生的为人和作品都展现出了深厚的人文关怀,深受读者喜爱。四川文艺出版社受惠于先生作品,在此表示无尽的追思和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