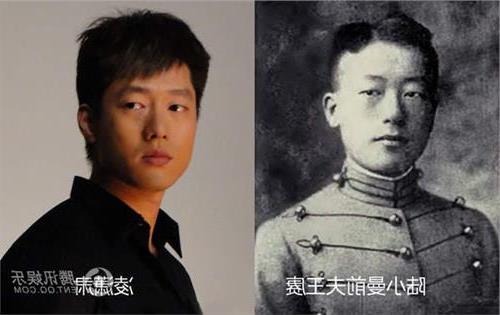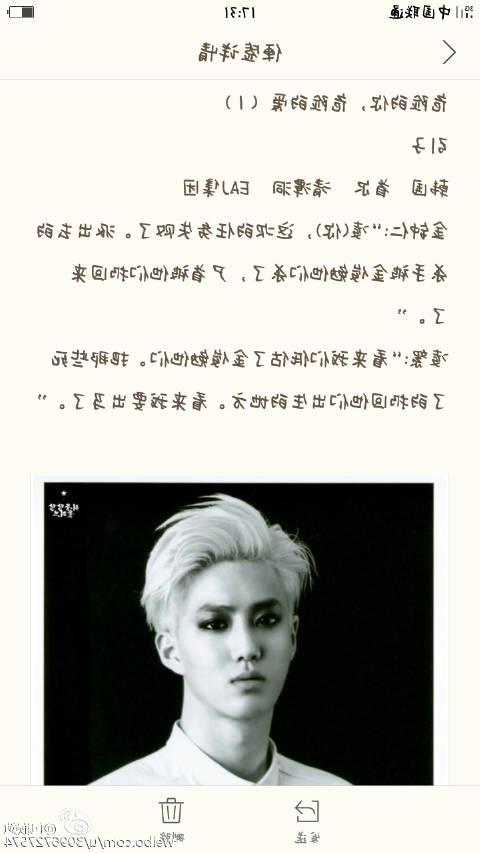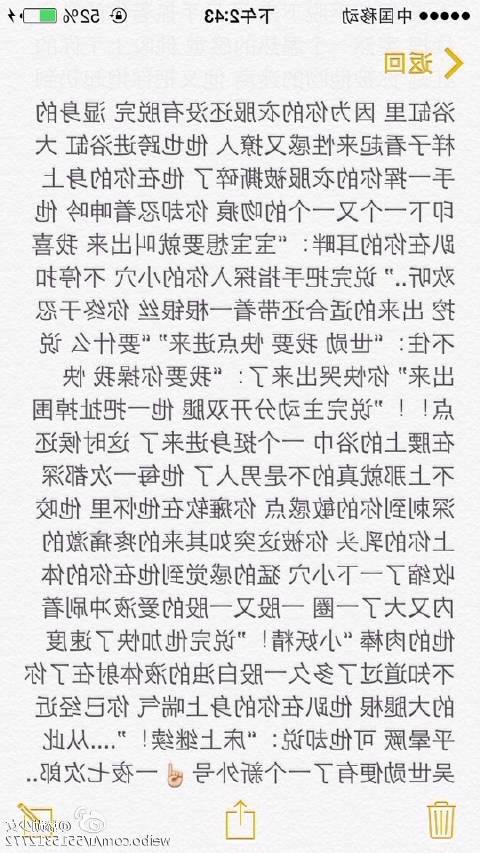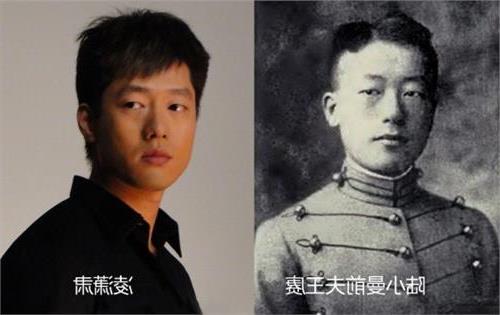王小鲁英文 王小鲁:“后文革”电影叙事
还能与中国电影的第五代导演谈作品的独立精神吗?这里谈的不是“独立电影”,而是电影制作的一种精神指标,它存在于一切电影中。第五代导演不再承载当代经验和价值追求,在触碰历史时也缺乏真诚的思考,这已成为大家共见的现象。若以那个指标来衡量,第五代当下的电影创作,精神层面十分荒芜。
对于中国电影曾出现的如此明晰的代的划分,也是一个让人沮丧的文化现实。每一代在与上一代的历史对比中,具有某种差异性,而在一代之中,则显示了美学齐步走般的同质性。这也是贫瘠的证明。
不过,在对第五代的历史讲述和学术整理中,有的导演则难以在其中被整合,比如彭小莲。她是北京电影学院1978级导演系的学生,与陈凯歌、张艺谋等人是同学,符合中国电影“第五代的的历官方定义”。但是她与那个群体一直是游离的。
第五代普遍与当下文化现实显示着某种精神上的协调一致,只有一小部分异质性的东西被两三个人所承担,比如田壮壮、吕乐、彭小莲。他们相对显得不那么红光满面,而显示了一种别样的面容与疏离感,他们的思想中没有显示“一切都解决了”的圆熟,他们仍然保留着某种思想的纠结。我认为这恰好是最可贵的东西,这也是我想采访彭小莲的原因所在。
不久前,张艺谋在为 《山楂树之恋》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文革’已经过去了,还要沉重多久”,对此彭小莲很气愤,她认为对于个人来说,许多事情是永远过不去的。有些人选择了让某些事情过去,从而选择了一种轻松的生存态度;有些人甘愿承载着某种不能让人愉快的沉重,背负着它前行。
在报纸宣传《山楂树之恋》的时候,她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日本人拍摄的纪录片《延安的女儿》。此片讲述“文革’中一个知青与他人相爱,生了私生女后被判刑,后来孩子送给了当地农民。
多年后那个私生女到北京寻找母亲,母亲拒绝相认。这是关于那个时代的性与爱的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使我们看到 《山楂树之恋》里对于“文革’时代爱情的理解是缺乏人性深度的。
彭小莲最早给我深刻印象的是电影《美丽上海》(2003),它讲述了一个经历“文革”的大家庭在当下的冲突。这把当代展现为一个 “后文革时代”,显示了一种历史眼光,它同时也对当代人的自我理解做了深刻的提示。电影中郑振瑶扮演的老人已到垂暮之年,她的丈夫曾在“文革”中被鞭打致死,现在她召唤分散在各地的子女们归来,并向他们分配遗产。
这是一种具有象征性的行为,这里有补偿,似乎也有讨还。海外归来的小妹 (王祖贤扮演)和充满铜臭味的二哥 (冯远征扮演)发生了冲突,小妹认为二哥没有人情味,并认为母亲对他过于偏袒。
母亲把装满小妹年幼时玩具的盒子送到她手中,令她十分震惊并号啕大哭——因为里面还有一张她与父亲划清界限的信,母亲说,我不是有意地保存这个信件,我不是不原谅你,但是,你哥哥当年在受到挨打等折磨时,坚决不和父亲决裂,他并不是你说的那种没有感情的人。
这个电影获得了很多政府奖,我想里面的表达还是有限的。但是她坚持对于历史进行思考与反思的精神,在当下显得如此珍贵。彭小莲的选择,与她的家庭背景有关。她父亲是著名的“胡风分子”彭柏山,上海市曾经的宣传部长,她母亲曾是新四军 《前锋报》主编。
彭小莲1953年出生,在她只有几岁的时候,父亲被活活打死,母亲也受批斗,但是她带着几个孩子坚强活了下来。这形成了彭小莲对于女性的独特的理解,她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经常是那么饱满、坚定。
后来她插队9年,然后于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1982年毕业后分到上影厂,拍摄了几部电影厂体制下的作品。1989年去美国纽约大学读电影硕士学位,1996年左右回来后虽然成了独立制片人,但是仍然为电影厂拍片,拍摄过商业片《犬杀》(1996),也拍摄过主旋律电影《上海纪事》(1998),她独立筹资的电影也在国内获得政府奖,如上面说的《美丽上海》。
她的电影在审查层面上是顺利的。她说她会自觉地接受审查,“我的片子从来没有被要求删减掉什么镜头,甚至没有修改过台词。
”但是她对于这样做的意味,有着深刻的自觉,这是一个区别,被分裂的她认识到了这个分裂,并且有能力评价它,有的人则完成了自洽,并使用一些理论色彩的语言来弥合这个裂缝,来显示自己是圆满和愉快的,欺骗自己也欺骗世人。
彭小莲是一个导演,还是一个优秀的作家,而且她非常勤奋。但是她坚从拍摄 《假装没感觉》到上美丽上海》。都十年了,我觉得这十年我应该有一个飞跃性的进步,但是她我没有。
这是此次访问中我听到的最惊心的一句话。人之所以是创造性的,是因为他是自由的。但如今我们无法通过勤奋和天分获得进步,就像我们无法通过勤劳和智慧去致富一样,这是当下制度反文化和反价值的例证。但是对于彭小莲来说,她最近有一个创举,她完成了一部独立纪录片《红日风暴》
这个纪录片对于她自己的经验进行了整理,对于历史提供了解释。这其实是大家对她期待已久的。历史总会找到一个最适合于言说它的人来完成叙述,关键看那个人是否愿意承担。开始的时候,彭不愿承担。1985年胡风去世,1986年举行追悼会的时候,彭小莲代表父母前来参加。
“胡风分子”希望做导演的她拍摄一部关于胡风案的电影。她选择了逃避。1996年朱微明去世前,把悲惨往事讲给从美国赶回来的女儿听。“从2003年起,我带着寻找父亲的愿望访问了几乎所有的‘胡风分子’。
”2009年,这部独立筹资的电影完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发生自1955年并一直延续下去了的最大文字狱,胡风和他的同仁因为其文艺思想被政治打压,全国牵涉2100多人。
电影把“胡风分子”与政治力量的关系处理为鲁迅的精神力量与延安文艺座谈会工具论文艺思想和极权思想之间的斗争。这个纪录片是国内第一部关于政治运动的全景式的纪录片。资金困难的局面与担当、对于思想线索的艰难思辨以及反思历史的勇气,让彭小莲在这里体现了真正的独立精神。
王:请讲述一下《红日风暴》的拍摄情况吧。很可惜我还没看你这个片子,我想知道你是怎么进入的?
彭:就用我的话外音开始叙述我和我爸的关系,我爸不在了,我想去认识我的父亲,然后通过我父亲的故事,把“胡风事件”引出来。最开始出了两个镜头,一个是鲁迅的葬礼,一个是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我采访的人百分之九十都去世了。就这几年的事情,去年和前年,几乎全都去世了。里面讲得比较多的绿原、何满子、梅志、贾植芳、谢韬夫妇,都去世了。
王:这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关于“胡风集团”的纪录片?
彭:应该说是中国政治运动中的第一部纪录片。一般都是个人的。中国任何一个政治运动都没有纪录片,包括“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可能会有一个人说他 (她)怎么经历了“文革”,但那都是很个人的,比如《我虽死去》,写的是“文革”的事情,但没有写整个运动的来龙去脉。
王:我看过你的文章,说当时你很小,看到你父亲彭柏山的尸体,我想你可能会逃避这件事情。
彭:我记得最清楚,1981年有一段时间我们到北大去体验大学生活,准备给韩小磊老师的剧本收集素材,我碰到黄军涛,天天在那里瞎聊天,有一天在食堂吃饭,他问我胡风是怎么回事。他天天问,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问到后来我问他你干吗?他说,我觉得你以后什么电影都不要拍,什么都不要弄,就是要把这个事情彻彻底底地弄清楚!我说我才不干呢,我烦都烦死了,觉得他跟我讲这些事情,有病啊!
王:我很想知道,现在直面“文革”的剧情片完全没有,只有几部民间的纪录片。其实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有大批关于“文革”的电影,比如谢晋的 《天云山传奇》、黄建中的《如意》。我猜你母亲当年看了这些电影,应该是有自己的态度的,她会怎么评价呢?
彭:你现在去找本书,李洁非写的《解读延安》,它说从解放前到现在,中国的文化系统全是延安系的。包括你说的那批写“文革”的东西,也是用了17年的那种“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思想状态来叙述那个东西,其实还是有很概念的东西在里面。
它没有一个很具体的、个体的、人性的思考,它的命运在这个时候的被扭曲,它的反思,它的挣扎,那时候还没有这种东西。虽然拍了很多“文革”题材,但你今天来看还是很幼稚的。但是,要是一直拍下去就会不一样的,总是从简单的思考,慢慢地走到深刻的。
王:事实是后来根本就没有继续拍下去,似乎越来越成了禁区。
彭:所以我觉得我们做 《红日风暴》……当然我们不可能没有自己的观点,当你把别人的叙述放进影片的时候,你也是有自己的选择的对不对?但是我的观点我不说出来,还是让人家在叙说。这样就比较开放,每个人从这个电影里会有不同的解读。我们不会老是在那里给人家概括,那种都是延安系的思考,所以你要把更多的信息交给别人,也许多少年以后,你的思考又会有新的层面出来。
《解读延安》里就说,为什么有“文革”?是从延安开始,从延整风运动”就已经奠定了“文革”的整个基础。你想,从第一次文代会(1949年)开过以后,作家都很自觉地写起那种作品来了,三四十年代的那种文学氛围一下子就没了。
其实不可能一个会议就把作家全部改变,是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这些东西就开始在系统地形成。我们讲“胡风运动”,就是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起的,而胡风就是反对“延安文艺座谈会”那种东西的。但是和李洁非不一样的是,我们还是比较感性的认识,不自觉地追溯。
所以后来我和李洁非讲,你是非常理性地做了那么多研究出来,系统地提炼出很多思考和认识,我不是做学术的,我写的东西都是凭感觉的多,但是我们也是这样把这条线理了出来。我就觉得这样比较好,你多种角度解读的时候,我们这个片子就具备了很多东西。
王:你父亲与鲁迅有书信往来?
彭:对。他是鲁迅的学生。他们都在上海。
王:片子里涉及鲁迅的地方多吗?
彭:当然多啊,贯穿一条线的。所以一上来就是鲁迅的葬礼,然后是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其实就是一个独立人格对集权抗争的故事。但是我们也不要说那么白,就是把两段影像摆在这里,然后慢慢叙述。
王:鲁迅的思想对胡风他们的影响是非常深的,胡风这些人的独立的个性,与鲁迅精神有深刻的关系。
彭:对,一代人都受到他的影响。后来我到电视台去帮助拍摄萧红,到鲁迅博物馆去的时候,他们就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最没劲了,知识分子里就是“胡风分子”好。“胡风分子”为什么有可爱的一面?他们就是在解放之后这么大压力下,也从来没改变过自己的理想,没有屈服。刘再复说过一句话,他们身上没有奴性,他们的灵魂是站立着的。说得非常对。后面的人是没有办法,包括老舍啊,曹禺啊,所有的知识分子在体制下讨饭吃,没办法啊!
王:这批人才是“五四”的真正的成果。
彭:对对对。“五四”精神留下来的。其实“五四”的时候这部分人大部分才出生。
王:你在片子里有没有采访当年首先把胡风私人信件交出来的舒芜?
彭:他拒绝采访。他蛮假的一个人,文字不错,人很聪明,但是虚伪。他比较功利,他当年巴结胡风的时候,那时候胡风是鲁迅死后的一个重要人物。但解放后就知道大势已过,已经没胡风的位置了。当然他也没想到把胡风的信交出去后胡风会这么惨。
他后来也很悲惨,“文革”的时候他夫人被红卫兵拉着头发在地上拖。他不内疚,你去看他《回归五四》的书,都在为自己开脱,说刚解放的时候对毛泽东的热爱比较幼稚。他这种人怎么可能幼稚呢!他就迷惑大家,把自己等同于解放后刚十七八岁的小青年。他之所以活到八十几岁活得很好,因为他灵魂没有叩问。
王:真是幸运,你还是在最后的时刻拍到了。
彭:但是好多好多还是没有。当一个科技进步的时候,就像电脑出来的时候,你就不知道现在网络对体制是多么大的威胁,多少案子是网络引起的,你看“邓玉娇案”不是因为网络,早把她判死刑了。科技的革命对很多事情来说你是想不到的,现在有了DV。
当时小川绅介(日本纪录片导演)说要搞亚洲纪录片运动,我说你根本不可能的,他说胶片可以从日本运过去,我说16MM胶片去哪里洗印,他说拿到日本洗印,我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他就讲了很多可能性。
后来,就看到了那种大录像带,那种大的机器,那也不可能。但是最后当我做的时候,是科技的进步帮了我们。所以你都没想到,有一天能做这种事情。而且我的朋友在香港,我们大量的联系,包括申请欧洲鹿特丹电影节的基金,我们根本不认识,全是网络的联系。
后来宣布的时候说几月几日你们上网去查,7月几号我一查,有我们了,我那天在网上看到特别高兴。其实根本不在乎他汇过来一点欧元,关键是突然有人在支持你,就很有信心。所以后来我特别感谢那个主席。今年夏天,上海电影节的时候我送她一本书和一个带子。
王:那个基金很少,你应该是自己出了一部分的。
彭:大部分是自己出的,我和魏时煜一人一半。卖没卖掉多少钱,反正做这个事情不是为赚钱做的,为了给历史一个交代。至少这些老人走了,他们的痛苦,愤怒,幽默,全都留下来了。在香港国际电影节放的时候,有个80后小孩就站起来,她非常愤怒地说:“都说我们自私,都说我们对社会没有责任心,但是谁告诉我们历史的真相?我根本不知道在我们中国有过这样的事情,我真的很震撼,看完后我不是痛苦,是愤怒,我愤怒没人告诉我历史,如果我不到香港我都不知道这个历史。
”放的时候我没去,所有放映我都不去,我不想招事。但听说后我觉得很感动,放完了后观众都不走,都在提问问题。
里面有两个地方,片子里贾植芳的朋友一直在那里写检讨,不知道毛泽东已经去世了,贾植芳说,你不要写了,红太阳落下去了。全场鼓掌,很久很久。我听了都特别感动,我片子做到这时候就知道什么是成就感,这个时候就有一种成就感。不过拍完就拍完了,不想了。人家说你功德无量,所有人都说这句话。鲁迅的儿子看了后特别激动。他给我打了很长的一个电话,说一个人在家看了。
王:我想和你谈“文革”的东西,因为你的身世和经历使我想起很多。我喜欢《美丽上海》这个片子,因为里面的“后文革叙事”,这种“文革”的叙述现在很少很少。你写“文革”的东西母亲都没有看到。
彭:没有。我母亲1996年去世,就是她去世前我回来的,回来后一直在医院照顾她。所以很可惜,我总是想如果我母亲知道我写的那本 《他们的岁月》,写的都是她和父亲他们的生活,那该多好。
王:《美丽上海》里王祖贤和父母划清界限,是你自己的经历吗?
彭:没有,你说我这种人怎么可能和我爸妈划清界限呢?我肯定是和造反派对着干的人。也办学习班,也批斗我妈妈,开批斗会的时候,我也批判我妈妈。但我妈妈知道那是假的,她和我挤眼睛,被造反派看到了,造反派大骂她。
王:《美丽上海》剧本是你写的,细节都是真实的吗?
彭:剧本我写的,我写过一个长篇小说,然后改的,里面的故事都是有生活原型的。很多细节都是编造不出来的,很多细节我都听到过嘛。那个戏也卖得不好。其实中国老百姓是很要看这个电影的。第一次放的时候,在电影节的时候,上海影城1200个人的场子全部坐满,最后没有一个人中途走掉。当然开始的时候是冲着王祖贤来了,但是看着就把这个事给忘了,看进去了。
王:其实第五代拍“文革”的也不少,早期的《活着》,还有《霸王别姬》、《蓝风筝》。更深地进入人性的某种感觉还是没有很具体地写出来。《霸王别姬》还不错,《活着》和《蓝风筝》也很好,但多拍摄那种苍茫的感觉,总是在大的历史进程的视野里去发掘那种宏大的时空感、年代感,发出 “历史无情”、历史轮回的浩叹的东西比较多。
彭:进入人心的复杂的东西没有写出来,还是控诉的比较多。走入个体的每个家庭,每个成员的被侮辱被损害,那种状态其实都没写出来。而且我喜欢写那种——看起来很平静,但是你突然走进去,才知道那种伤害是永远不会平复的。不是那种很大的,不落实到局部的角落的那种。电影经常一写就写大了,我觉得这和我们的教育有关系。
王:第五代后来也有与“文革”有关的,张艺谋的《山楂树之恋》,还有《我的父亲母亲》也有与文革”叙述,但基本都不是在写实层面表现,它只是为某种特殊的感情提供了一个契机。
彭:“文革”只是一个背景。前段时间我写了一篇影评,《〈白丝带〉的象征意义》,因为我看见《南方周末》登出了张艺谋的访谈,他说:“‘文革’”都成历史了,还要沉重多久。这是对历史的回答吗?什么“文革都过去了”。
所以我对报纸说你们要删我前面的东西就别登我的文章,他们就没删。后来报纸评《山楂树之恋》,我就说下一篇一定要登我的一篇文章,评,延安的女儿》,禁欲,是反人性的,这是纯爱吗?难道我们要回到中世纪啊?《延安的女儿》是一个日本人拍的纪录片。
写了文革”时一对插队的知青,生了小孩在那里,被抓起来判刑了,女孩就送给农民,长大后完全是农民,后来听说父母是北京人,就到北京找父母,父亲落魄地住在小破房子里,而现代的北京是很冷漠的城市,母亲坚决不出来认女儿。
她走的时候,爸爸根本不送她。我就说下当人们都被盛世所迷惑的时候,当人们把延安的浪漫都剥去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反思,我们是要让下一代埋单的。我说你怎么可以对这个历史不反思。
王:按照代的划分,78级算第五代,你也在这个范围内。第五代拍摄的方向都蛮一致的,几乎是齐步走的。对于你来说,在78级和第五代的叙述里,你好像是比较游离的。
彭:我从来就游离,读书的时候就游离,组织活动也不参加的,拍戏都不想叫我,哈哈哈,觉得我老不跟人家好好合作,说起来就是“不合群”
王:你现在找钱很困难吗?
彭:很困难。我的戏人家都觉得不卖座嘛。《我坚强的小船》是350万拍的,投资人是赚回来了。没多赚但是也没亏,拿了点奖,政府奖也给了一点。但是发行就是小发行,华夏发行公司把北方的部分买断了。现在电影谁给你买断?都是分成的,能买断就很不容易了。
现在这个本子350万是拍不下来的。这个本子也是刚完成不久,也是在报纸看了一条消息,说一个修车人,我特别感动。那天我就去弄堂口看他,特别冷,我就去了,他给我一个凳子我坐都坐不下来。
就站着和他聊了一下午。也没什么人去修车,回来后我都感冒了。为什么我要着急去,是因为他要过年回家了,他已经很多年没回乡下了,在河北,很偏远的地方,采访完后我就和朋友说和他一起回去,后来我们就买了一张票,背着摄像机就拍回去了。一直拍到乡下。找不到钱,一问就说票房是怎么样啊,这种话我听都不想听。
王:对。票房在目前来说的确是个大问题。
彭:我觉得这个是政府问题,全世界没有这样发行电影的,全世界都没有!你总得给电影院另外一种声音。你的资金要资助文化的,文化是一种奢侈的东西。你他妈的要全靠票房,全靠自生自灭,那我跟你说,最好的东西一定是最脆弱的,你要这样弄,全都死光光,剩下来全都是杂草,你去田里面看看,你不管的话杂草比稻子长得好得多了。
下转47版
上接46版
王:现在你的独立拍摄状态和电影厂时代拍片状态比较的话,是怎么样的?
彭:好不了多少。电影厂时代也是左不通过右不通过的,也是预算给你卡到最低的呀。我们拍摄商业片,预算总是最低的。
王:关键是中国电影的想象力还是非常受限制的,给你戴上紧箍咒去思考和想象。现在导演都是到了拼命抓钱的时候了,现在资本的审查包含了政治的审查,政治审查看起来没有很大的激发义愤了,是因为政治审查已经被资本方首先考虑在内了。你要创作要想象,一想象就碰到雷区,那你还能怎么去创造呢?
彭:而且现在,你要问什么是不可以拍的,还没有说明。中国就是黑色幽默,什么不可以拍是要你凭感觉思考的。从 《假装没感觉》到《美丽上海》,都十年了,我觉得这十年我应该有一个飞跃性的进步,但是,我没有。你写出来是要能拍的啊,还有什么想象力?你写剧本首先要过自己的一个审查关。所以我就开始写小说。小说就不会受这么多局限了。人都说我小说比电影好,废话。小说你不发我就放在那里。
王:你的电影基本上都是院线电影,拿到许可证的。而且还拍过主旋律电影,即使与“文革”有关的《美丽上海》,也获得了金鸡奖这种政府奖,我很想知道你创作《美丽上海》时,前期后期受到哪些限制和约束?
彭:我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那么久,还是比较理性的一个人。所以,我不会拍不通过的片子,我总是按照游戏规则去做。我自己就很自觉地先审查,所以我的片子从来没有被要求删减掉什么镜头,甚至没有修改过台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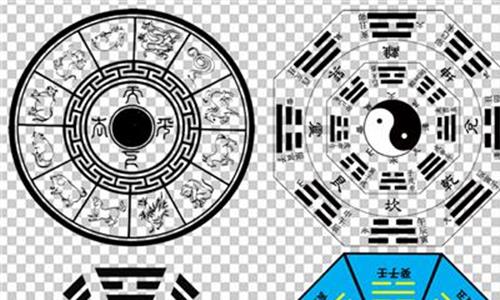

![王垠现状 [转]王垠的过去和现状](https://pic.bilezu.com/upload/8/a9/8a9340599f2de633fa5b6988d4d697d6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