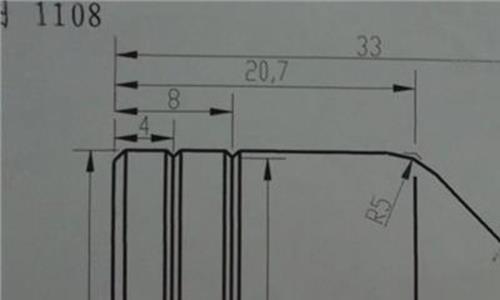廖一梅一个女人 廖一梅:樊其辉是“女人” 用笑面对惨痛生活
主持人王东:而且有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情境,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那个博尔赫斯我这里也特别抄了他的一句话,他也曾经说过"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
廖一梅:是的,这句话我也记得。
主持人王东:这句话我觉得非常棒的一句话,而恰恰你就是一个表达者,我也是一个表达者,你怎么来看待这种宿命,就是总是不断地被误解?
廖一梅:接受其实就是误解,就像我去做讲座的时候,有的观众问我,就是说我看了,我看你的戏。但是我不知道我懂没懂,这个懂是怎么懂,其实可能它在某一瞬间他内心的某种东西被这个戏激发了,或者说它想到了某种东西我觉得这已经是懂了,你要求完全的懂,那是怎么一种懂呢?任何一个东西给出去它具有它自己的生命了,就像它是一个独立的人一样,你有多大的程度了解它,或者说跟它产生一个怎样的交流,那个只是个运气了。
主持人王东:你有没有觉得戏剧中的你跟现实中的你还是差异还是挺大的,还是说这方面恰恰是相反的相通的?
廖一梅:我是一个诚实的作者,如果我在戏中采取什么态度,我在生活里就采取什么态度。比如说这个《柔软》的结尾,我写了有半年最后一幕,不是说我不能用技巧性的结尾把它了结,我会编出无数的,我可以十多种用各种方法更有戏剧性的,或者说更有冲突感的,更感人的,或者更让人刺痛的,哪一种结尾我都能够写出来。
但是我不能写一个技术性的结尾,如果我对这个故事,或者对这几个人采取的对生命采取的是什么态度,我是要求自己,我以后的生命里都是这个态度,我不能以一个虚假的态度来了解我的戏,每一部戏都是,至少在当时是完全诚实的,然后完全诚恳的,你说它后来改变了那是有可能的。
但是在那一个当下就是我,在舞台上的就是我,代表我所有的态度,我对生命的态度,对人的态度,对爱的态度,对孤独的态度,对交流的态度都代表,这个是我对自我的一个要求,我可能还是那种比较老派的人,把写作当成一个严肃的事情,而不是一个玩乐吧。
主持人王东:不是一个娱乐的东西。我可不可以提一下,樊其辉这个人,也是跟你写这部戏也有一点关系,他的影子在这部戏里。
廖一梅:是。
主持人王东:樊其辉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他曾经是在设计界,服装设计的一个领域里面其实是挺有成就的一个人,很有幸,我也找他做过衣服。
廖一梅:他唱白光的歌。
主持人王东:他呢,其实他长的并不是很好看的人,然后还很粗壮的那种感觉,但是他到了晚上他还非得邀请我去看他的表演,但是我没有敢去。
廖一梅:你没去过吗?
主持人王东:没有。
廖一梅:那你就不知道了。
主持人王东:但是我虽然没有去过,但是他给我看过他的照片一些东西,甚至一些东西我都看过,比如说他在夜晚在酒吧里可以扮成一个妖娆的女人在那里唱白光的歌曲。
廖一梅:对,我去过,看过很多次。
主持人王东:看过很多次。
廖一梅:对,我还为他写过一篇稿子,我当时看见他的感觉就是说我是一个真的女人,但是他是一个十足的女人,就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女人,然后他把女人的那个外在形象贴在一个男人身上,他也不好看,但是说不出来的沧桑和风情,就好像所有的那个,总是一副什么地样子呢,就是脸上的眼泪干了,流了很多次,然后干在脸上了然后永远在那儿甚至流下了眼泪的痕迹的那样一张脸,真的很吸引人,不同寻常。
主持人王东:对,他非常爱那个表演,他好像每次就为了那个表演活着似的。
廖一梅:对对。
主持人王东:但是很不幸,应该是在去年还是今年,去年他离开人世,然后当时在微博里边有很多的人,圈子里面的人去悼念他,转发相关的一些消息等等。他这样一个人物一个形象,他的故事给你创作《柔软》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廖一梅:原来这个故事只有两个人,就是两个人的戏,一个女医生,和一个阳光灿烂对人特别友好的,但是唯一的问题他认为自己是女人的一个年轻人,只有这两个人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复杂的感情纠葛。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没有那种跳跃的感觉。
就是它完全一头扎进了这种东西里面,我特别希望这个作品能有一个地方是透气的,我也希望我喜欢我的东西是很愉快的,不是愉快的,是幽默的吧,即使是最惨痛的事情,它也应该是以一个幽默的调子来谈论的,这个是我一贯的原则。
所以我当时觉得他不够幽默,或者他的自嘲和嘲弄都不够锐利,所以我一直想有一个什么因素能够改变这个戏,后来就想到了樊其辉,就是他演出的时候会说很多笑话很多故事,他会倒我的台词,我看过他演出,他改那个《琥珀》的台词原来说是所有的爱情都是悲哀的,但尽管悲哀仍然是我们所知道的最美好的事物。
他当时在台上冲着我说:所有的爱情都是悲哀的,可尽管悲哀,仍然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好玩的事情,最有趣的事情。对,我觉得很合适他说,他是一个能把生活里最伤感或者惨痛的事情都当成笑话再说的人,就是态度,而且他既非男也非女,他既不认同自己的男性身份,也不认同自己的女性身份。
他是一个生活在生活之外的人,就是非常难得在这世界上有人生活在生活之外,不让任何人给他贴上标签,就是他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很难归纳的一个人,但是又完全真实。所以我当时觉得,我需要这样一个人物来调整这个戏,后来又加了一个人物,写了第二稿。
我当时打电话告诉他,打电话问他了,我说你介不介意我把你写到戏里,他说太不介意了,你赶快写吧。所以我其实是想,因为你也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时装设计师,所以我当时是希望他能来给《柔软》设计服装的,但是就在开新闻发布会的前三天,就是我们才夜里拍剧照一整夜的时候,那天拍了一整夜在拍剧照,然后早晨起来回家睡到上午的时候,我看见电话在响,我一看是我们的化妆师给我们发的短信,他跟樊其辉也是好朋友,然后就说他出事了,当时对剧组的人也是一个挺大的刺激,郝蕾跟樊其辉也很熟,我们都谈论过这个,后来不太敢谈论了,就是说生命真的很沉重也很脆弱,他不是说你一两句玩笑就能轻松渡过的,你真正要面对他的时候需要更大的力量或者说勇气。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把他原来的样子留在舞台上也很好,就是他一直就是那么一个,对于最惨痛的生活都来怀着笑的那么一个人。你看你跟他打过交道,他说过话什么的。
主持人王东:对非常风趣。
廖一梅:对,非常风趣充满了笑料。就是讲每一件事的时候,他有特别多的自嘲和嘲弄,你看到他既刻薄,但其实又宽容,对他来说任何苦难也得能渡过,但就这样的人也终究没能渡过,如果是我还没写完的时候知道发生这样的事儿,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继续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