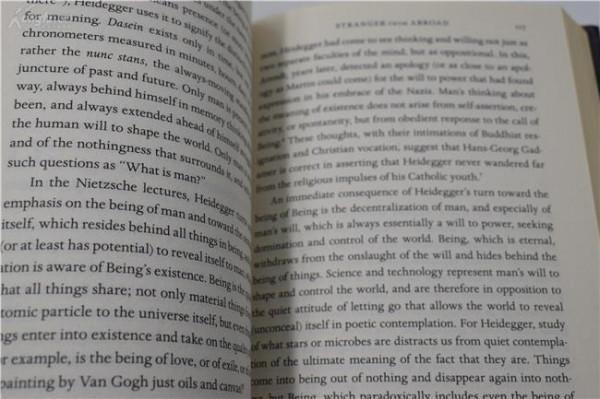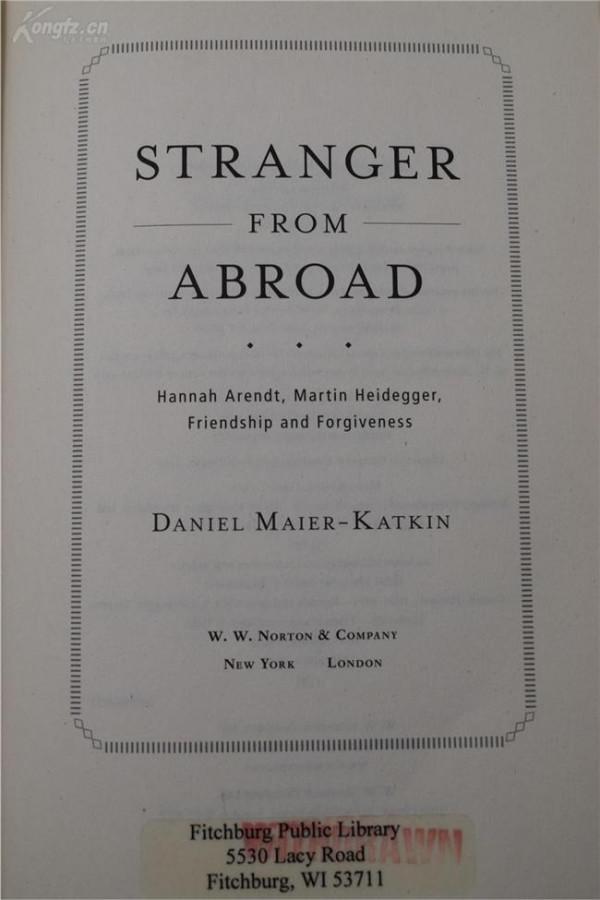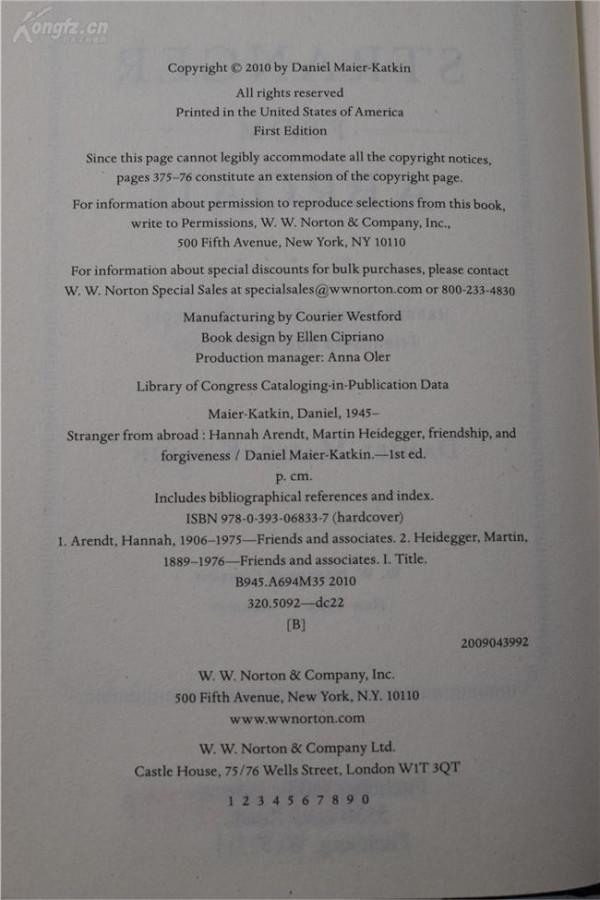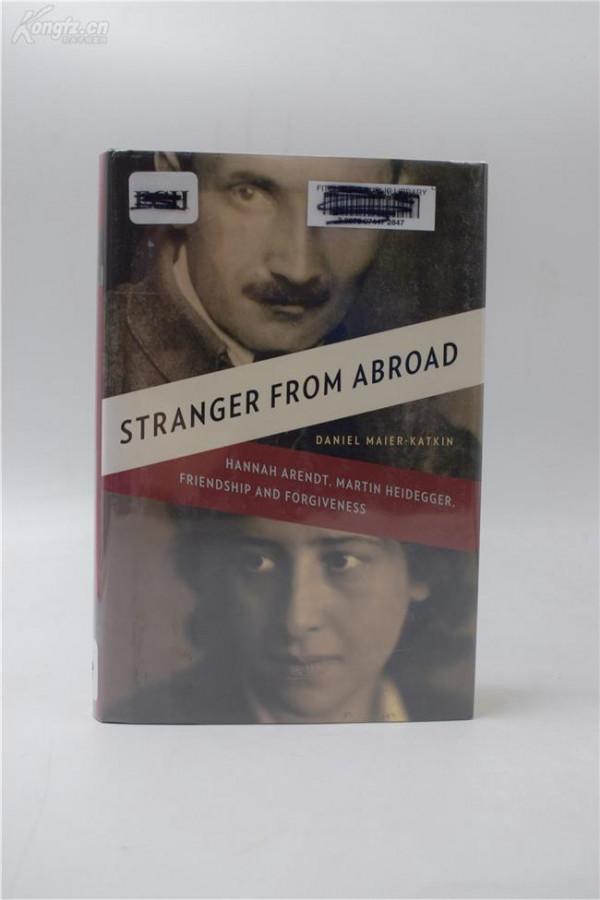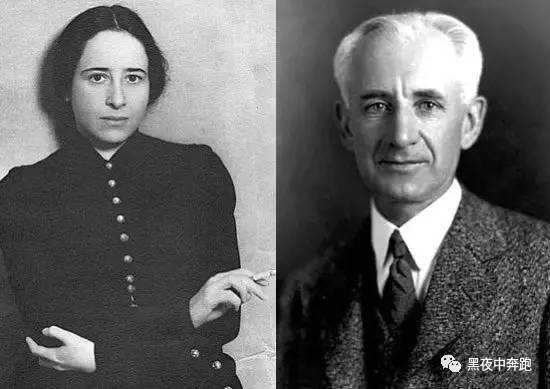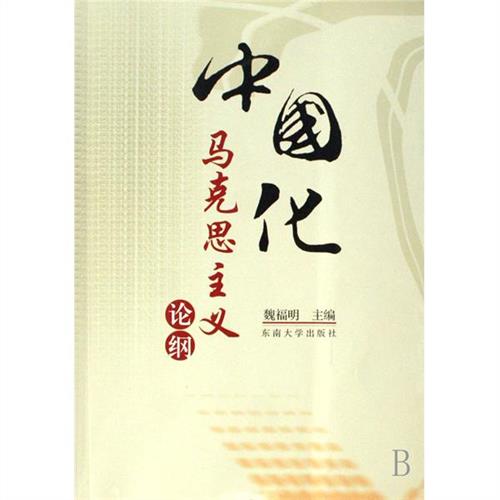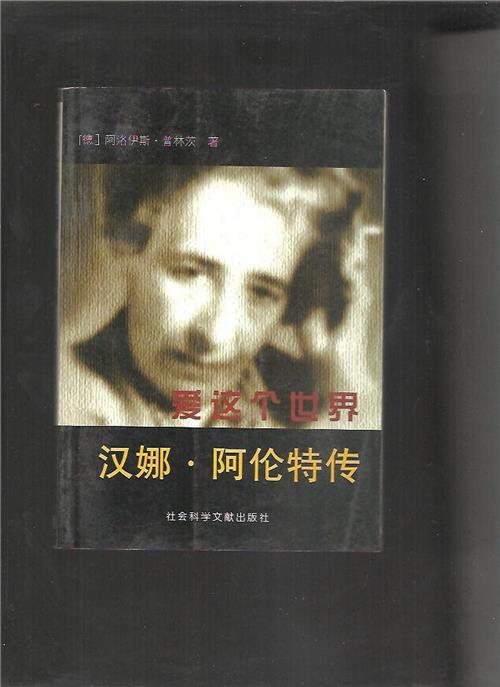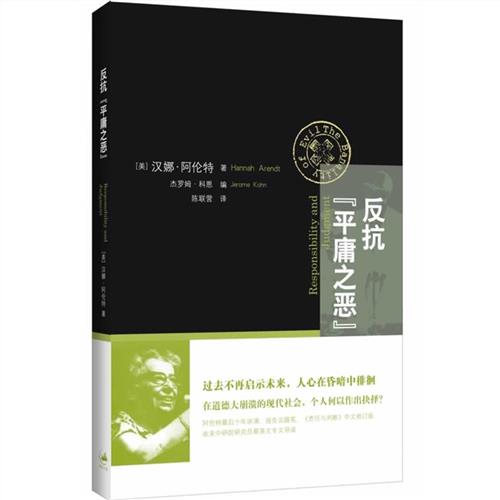海德格尔阿伦特 汉娜·阿伦特:海德格尔的情人
在写下这个标题之后,我感到十分矛盾:为什么我会跟其他所有人一样,强迫她进入到“他的故事”里?为什么我不能把汉娜·阿伦特视为完全独立的存在,而一定要首先引入海德格尔这个名字?似乎阿伦特是为了海德格尔才存在,似乎阿伦特的意义就在于身为海德格尔的情人,给予了海德格尔女性的灵感。
哪怕她的脸上收揽了所有女性的美,哪怕她的头脑里收揽了所有人类的智慧,当我触摸汉娜·阿伦特这个名字时,总是先触摸到海德格尔的存在。
也许我可以给出理由:一个女人总是无法独立于男性世界,无法独立于HISSTORY。长期以来,女人处于被说的地位,被观看的地位,这是展品的地位——她们需要被评判的眼光得到确立。我无法以纯粹女性的眼光去审视汉娜·阿伦特,这其实同时也是我个人的悲剧:一只看不见的手取走了我独立的视角。这只手从黑暗中来、从历史中来、从潜意识中来、从创世中来、从四面八方而来,它取了我的一半甚至大部分,把它们交给了男性。
每个人都在重复所有的人。根据自相似理论,这无疑是一个事实。
在你的生活道路上,你曾遇到过汉娜·阿伦特吗?
阿伦特是个犹太人,七岁那年失去了父亲。她的个性从小便体现为冷漠与激情的混合——这样的人一般都拥有丰富而秘密的内心生活。对于父亲的去世,她淡漠地安慰母亲说:“别人家里也会发生这样的事。”而对于自己想结交的一个女孩子,她却在夜里从窗口跳出去,搭火车找到那个女孩的家,把石头扔在她的窗口,把她从睡梦中唤醒——虽然家人反对她结识这位安娜·门德尔松,阿伦特却用自己的方式结识了她,并且结下了50多年的深厚友谊。
18岁那年,阿伦特进入马堡大学学习哲学,海德格尔是她的哲学老师。第二年,海德格尔向这位美丽聪明的学生表达了爱慕之情。阿伦特把自己全部初恋的情感献给了海德格尔。多年之后,海德格尔曾坦露,那是他一生中最富有创作激情的阶段。
这场恋爱一开始就注定了是场悲剧。非常在乎自己声誉的海德格尔不会为了阿伦特离婚,在这一点上,他跟其他自私的男人毫无二致。为此,他甚至对阿伦特施加压力,要她转学到海德堡大学,这样他们的关系将更加隐蔽。海德格尔精心安排每次幽会,控制写信的次数,唯恐这段感情暴露出来会毁了自己的前程。
对海德格尔其人,我一直怀着犹豫不决的态度。
当教授海德格尔诗学的老师,用他那清澈的、略带四川口音的语言讲述海德格尔之际,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纯粹。
从文字里,我触摸到的,是一个澄明的海德格尔,一个向内生活的海德格尔。他的目光深入到从未有过人迹之处,而在目光所及之处,一切物性向它敞开。他所深入的荷尔德林,甚至是荷尔德林自己也未曾到达过的神秘地点。这是一个伟大而孤独的灵魂,在言语的尽头面对荒芜,却向那空虚索要言语。
遮蔽,敞开,澄明,诗意地栖居,仰望天空,倾出,必死者,大地……爱极了这些词语,而必须是海德格尔以这种方式言说,它才能进入我的心灵。
实在难以相信,这样的灵魂会成为纳粹。
我就像陷入初恋之中的阿伦特,为海德格尔找出种种开释的理由。在无话可说之际,痛苦进入我的心房。
可后来我停止了这种恋爱。作为海德格尔,他的悲剧自有他自己的灵魂作承担,根本不必我试图去做徒劳的证明。
阿伦特跟海德格尔的恋爱也停止了。
海德格尔将担任弗莱堡大学的副教授,处于事业颠峰的海德格尔担心跟阿伦特的关系会贻误自己,决心彻底了断这段感情。
缺少恋爱经验的阿伦特陷入到绝望的痛苦之中。
“爱,对于我来说,包含着生活的全部意义,我失掉了你的爱,就失去了真正的生活。”阿伦特在信里写道。她的感情几乎崩溃了。她认定,离开这个自私而伟大的心灵,她将再也不会去爱。她将拒绝向任何人打开自己。
安娜·门德尔松是她唯一的安慰者。她建议阿伦特阅读犹太女作家拉尔·法哈根的作品,从痛苦中走出来。
阿伦特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在拉尔·法哈根本人经历过的爱情悲剧当中,阿伦特看到了自己的身影。发现自己不是唯一的痛苦者,几乎是毁灭性的痛苦原来不只是降临到自己身上,本身就是一种安慰。何况,法哈根以一种回望的心情去注视这一悲剧,便具有了一种睿智的平和,这正是阿伦特当时最需要的精神支柱。
每个人都在重复所有的人。
按照霍尔奈的成熟理论,受到伤害之后个体会产生防御心理,而且个人是以抛弃其真实感情和发展复杂的防御策略来治疗焦虑。
阿伦特从这段情感中成长起来了,然而其代价却是个人或多或少地放弃其真实感情。这并未被她自己所意识,因而她往往会盲目地相信另一种情感假相。
在本质上,这种疼痛是一生也无法摆脱的,就像女性一生无法摆脱“他的故事”,这是一重早已注定的无奈。这时,我们的灵魂将会一点点逸出,从那个肉身里蜕出来,在疼痛中重构第二重肉身——这其中,我们丢失了最原初的真实情感,但我们拥有了更安全的生活。
26岁的阿伦特遇到了君特·施泰因,一位年轻的哲学家,此前,他们曾在海德格尔的讨论会上见过面。
失恋的痛苦被新生的肌肉所包裹,生活慢慢恢复了正常,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什么非此不可的必然性。如果有,那只是因为个体把这一必然性当成了自己的信仰。
阿伦特是个缺乏耐心的人,也许是因为行动的速度总是低于思想的速度,她不断地处于构思之中,一个选题还没写完又马上进入到另一个选题的构想当中,结果没有写完过其中任何一个。施泰因帮助阿伦特静下写来,写作她的博士论文。相识八个月后,阿伦特和施泰因举行了婚礼。
施泰因是个富有才华的年轻人,父母均为相当知名的儿童心理学家。然而,阿伦特并没有真正爱上他。她以为自己是的,其实她爱上的,只不过是海德格尔一个淡淡的影子。施泰因也是海德格尔哲学的崇拜者,他们常在一起讨论海德格尔哲学,这是她爱的一个原因,也是隔离她爱的一个原因——这是心头一重永远的痛苦,施泰因对海德格尔的崇拜只能加重这一痛苦,而不是从其中摆脱出来。
阿伦特需要一种更为成熟、更为笃定的爱,她需要把自己仍然嵌在第一重肉身当中的最后一点尾声拉出来,否则,心灵总会不由自主地沿着这点尾声回到过去,在其中陷溺于痛苦,并把痛苦进行永恒化、崇高化。
她的灵魂被镇住在由海德格尔的名字构成的那座雷峰塔底,逃出来的只是灵魂的虚影。
海德格尔来看望过这对新婚夫妇。君特送海德格尔上火车时,阿伦特无法控制自己,偷偷地跟在他们后面,目送着海德格尔上车。她写给海德格尔的信还是那么刻骨铭心:
我看着车厢里的你,几十秒钟已经过去,你是完全可以看见我的!可你的目光只是漫不经心地向车外扫了一下,你并没有看见我。
汉娜·阿伦特像隐形人一般,彻底退出了海德格尔的生活。
阿伦特与君特的婚姻也出现了裂痕。阿伦特满怀激情地投身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当中,关注妇女问题,初步显露出自己的个性。而君特含蓄内向,难以接受阿伦特的个性,互相之间又缺乏沟通的方式。1933年,柏林国会大厦纵火案之后,形势相当紧张,君特独自逃亡巴黎,两人的婚姻从此名存实亡。
排犹反犹思潮的泛滥,流亡、飘泊的生活,激发了阿伦特对政治的兴趣,也引发了阿伦特对“三个地狱”——反犹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思考。自1933年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犹太人的生存处境空前恶化。
1936年,流亡巴黎的阿伦特结认了海因里希·布鲁希尔。阿伦特解除了与君特的婚姻关系,跟布鲁希尔生活在一起。直到此时,阿伦特才真正从心理上走出海德格尔的阴影——这足足用了十年的时间。她将海德格尔的爱当作珍贵的礼物深藏心中,而跟布鲁希尔共享尘世的爱情。
对于犹太人而言,当时的生活意味着无尽的磨难和恐惧。阿伦特和布鲁希尔先后落难集中营,在这段时间的一个空档里,他们结了婚。集中营生活使得阿伦特对“集中营”进行了深入思考,她认为,集中营是一种极权形式,斯大林的集中营跟希特勒的集中营并无区别——然而,歌颂斯大林的高尔基命运显然要比歌颂希特勒的海德格尔好得多。
她提醒人们,不要只看到是否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实行极权主义,而要看那个国家内部是否如此。集中营就是极权主义的内部形式。
君特·施泰因并没有给阿伦特带来爱情,但他的确是个大度的绅士。1940年,欧洲政局继续恶化,已经流亡到美国的君特对布鲁希尔夫妇逃往美国鼎力支持,帮助他们顺利拿到了签证。
同一年,滞留在西班牙边境的本雅明出于对自身和对世界的绝望,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现实在此处是一片黑暗。而他的目光照亮了它。只有他能为它描出肖像。对其他任何人而言,那是无意义的存在,无意义的碎片,无意义的黑暗。
当我被一个春夜被本雅明的《单向街》所打动时,同时也翻看了一篇对本雅明的评价。我为评论者的才华所震惊。
当时,我只是模糊知道评论者是位女性。她以一种本雅明的方式来重构她的本雅明。从光芒的内部。她认为本雅明以及其他一些天才在死后才能获得声名的原因是:其一他们无法归类,其二驼背小人总会来到他们的生活之中。驼背小人会带来坏运气,并不是因为你要注视他,而是因为他注视着你。
她写道:
“本雅明被迫进入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位置,这个位置事实上直到后来才被证实和判断。”
“他们的物质生存建立在无工作的收入上,而他们的知识态度基于坚决拒绝被政治或社会整合上。”
“这些道路事实上就是巴黎的象征,因为它们显然同时既是内部的又是外部的,以这样完美的形式表现了它真实的自然。一个异乡人在巴黎就像回到自己的家里,这是因为在这个城市里,他可以像住在他自己的四面墙里一样自由自在。”
直到前几天,偶然打开以前的日记,我才发现,这位天才的评论者正是汉娜·阿伦特。
以她的才华,的确不需要附着在海德格尔这个名字才来构建自己的价值。虽然,在这个男权社会,汉娜·阿伦特的名声永远无法与海德格尔相提并论(除了他们作为情人这一事实),但她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她的声音很轻,但是我喜欢。
这是汉娜·阿伦特自己对声名的看法——
声名是一种社会现象;“就声名而言,一个人的看法不足为据”,虽然对友谊和爱情而言,个人的看法就足够了。差别作为社会领域的基本元素正如平等是政治的基本元素一样。
我在想,爱情到底是不是一种必需。
我决定把一切推翻重来,重新思考汉娜·阿伦特和海德格尔的关系。
在阿伦特身上,我再次感觉到这个道理: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决定你会有什么样的未来。正是跟海德格尔的四年,决定了阿伦特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是幸福的。她做了四年的倾听者,倾听海德格尔的思想从他的唇上说出,这种快乐一定超过了我倾听海德格尔的思想从余虹的唇上说出——余虹就是那位带四川口音的副教授,也是《诗·语言·思》的主要译者。
汉娜·阿伦特把所有的爱情和痛苦都收藏了起来,把放弃作为一种占有——她把这段感情称为“伟大的爱”。她怀抱着这一伟大的爱,在爱情和痛苦中成长起来。终其一生,她都没有背叛过这种爱情,这心灵和肉体的初次恋爱——这是女性的一种特质,很容易将爱情信仰化。
海德格尔成就了阿伦特。他给了她一种属于天空的、近乎神性的爱。他与她的决裂并非出于自私,而正是出于理性,出于对二者的保存。倘若他真的是个彻底自私的男人,或者他就会一直将她霸住,反正她情愿做出这样的牺牲。
对于阿伦特,海德格尔的爱和离开都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一个带个伤口生活的人注定是个倾向于精神的人。
TA必定要包扎自己的伤口,或者以另一种伤来代替这一种伤。对于阿伦特,她的作品就是她的伤口。
阿伦特回到了大地上,布鲁希尔是她的大地之爱。
也许在每一个女性心里,都或多或少地期待过天空之爱,正如《大话西游》里的紫霞,期待着大圣“脚踏五彩祥云”而来。这种倾向正是女性从创世纪里带出的伤口,它持续得越强烈、越长久,将越能成为女性的精神内核。一个伟大的女性必须是一个破碎的女性,她身上的伤口正是识别她的标志,正如有人身上带着蟑螂供我们识别一样。
云朵下降到地面,在四周落下雨水。女性从天空之爱沉降于大地之爱,在原野上生长为一棵开花的苹果树。
布鲁希尔具有大地的一切属性:豁达、睿智、宽厚、沉稳。他怀抱着对阿伦特的尘世之爱,成为她的臂膀、她的生活支柱、她的合作者和她的父亲。正是在他的帮助下,44岁的阿伦特完成了最重要的作品《极权主义的根源》,指出极权的基础在于孤独,在于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受到隔绝。
阿伦特的母亲马塔从来没有接受过布鲁希尔。她不能接受自己的女儿四处奔波、养家糊口,而布鲁希尔却长期没有固定收入。
这一点上,阿伦特表现出坚定不移的态度,支持布鲁希尔的生活方式。在阿伦特与布鲁希尔之间,有一种深厚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因而,当这种信任出现裂缝时,将会成形巨大的坍塌。在阿伦特48岁那年,布鲁希尔有了外遇。布鲁希尔坦然为自己辩护:“我对妻子是绝对忠诚的,那不过是我的方式而已,我绝对爱我的妻子,也不想离开她。”
对于忠诚这个概念,我感到无比的迷惑。它的存在似乎就是为了让我痛苦,为了让我沉陷到对于忠诚的分拆之中而无法愈合。矛盾就在于此:忠诚事实上我的一个内部概念,它不同其他任何人的忠诚,也不同于某个公共版本的忠诚。
我相信布鲁希尔的诚挚,无论对自己,还是对阿伦特。心理学家曾经指出过男人和女人在对待忠诚问题上的差异:男人认为肉体的出轨算不上不忠,精神的出轨才是背叛;女人认为精神的出轨算不上不忠,肉体的出轨才是背叛。这一差异决定了两性对于“忠诚”问题永远的落差与痛苦。
相当一部分男人把嫖妓作为忠诚的一种方式:跟妓女之间纯粹是一种交易,完全不牵涉感情在内,又避免了外遇的可能,保全了他们对婚姻或者情感的忠诚。这在女性看来,是非常荒谬的,这无异将于破碎作为一种完整来保存。
我也能感受到阿伦特当时的痛苦。或者说,我把她当作了我自己,我是在向内审视,我体内的那个阿伦特并从中体会到她的痛苦。这一痛苦混杂着嫉妒、自卑、自我怀疑、愤怒、耻辱、失衡以及难以言喻的失落感。更为痛苦的是,她已经无法离开布鲁希尔。她不能再度悬浮于大地于天空之间,成为一种悬而未决的命运。
她原谅了他。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阿伦特是不忠的。在她的一生当中,她一直怀抱着对海德格尔精神上的忠诚,对他保持着永远的崇敬。她的精神导师雅斯佩尔斯与海德格尔决裂后,她曾多次试图修复他们之间的关系;顾及到海德格尔的心情,她还几乎放弃为雅斯佩尔斯致辞的活动。
1950年,阿伦特与海德格尔在弗莱堡重逢。此后,她致力于海德格尔著作在美国的出版,两人频繁通信。海德格尔对阿伦特始终保持着一种非凡的魅力,令阿伦特心甘情愿为他付出。在海德格尔受到指责之际,她为他辩护、洗刷,宣传他的作品,甚至谴责他的妻子影响了他的创作。
阿伦特令我感到心痛,因为,我以为,我是了解她的。
事实上,在你的生活道路上,她并不是你遇到的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