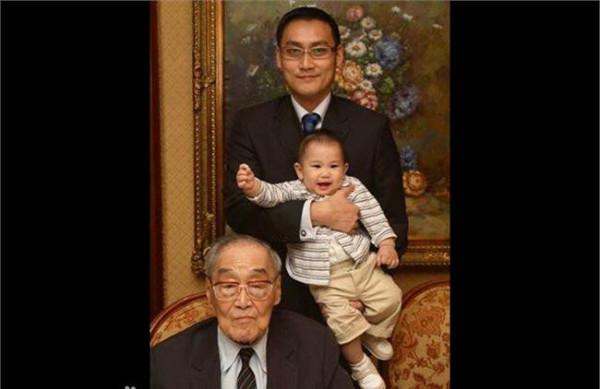【海子为什么会在德令哈】海子和德令哈
诗人海子与我是同时代人,他曾来到我所生活和工作的成都,我们没有见上面,失之交臂:大约是1988年夏秋之际,海子与诗人潘家柱(可能还有诗人付维)来访,不遇。当时我住在四川大学的教师集体宿舍,那时候,没有任何可以即时通讯的工具(没有手机和传呼),朋友之间的相互拜访,只能靠运气和等待。没有想到,那次不遇,竟成为永生的遗憾。

拜访的事件并未就此结束。快30年过去了,7月,我与妻子千里迢迢来到青海海西州府所在地德令哈。我们从下榻的中德酒店出发,步行约一刻钟,在巴音河畔,找到了海子诗歌陈列馆。我远远就看见陈列馆的大门紧闭,一把黄铜质地的旧锁横陈于门环之上。那一刻,我的内心无比沮丧。
大门两侧,书写着诗人吉狄马加的一副楹联:“几个人尘世结缘,一首诗天堂花开。”从旁边海子茶社的一位服务员口中得知,过几天,这儿将举办第三届海子诗歌节,所以要闭馆装饰。我急切地问道,海子的那块墨绿色纪念石碑呢?服务员随手一指,就在后面,河边。
思绪又回到1989年,那年3月26日,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尽,令人悲痛震惊。经过仓促的计划,由我和潘家柱、龚青森等人发起,在成都科技大学第三教学楼举办了一场诗歌纪念会,并为海子的作品出版募捐。现在还记得,到场的成都诗人中,黎正光认捐了1000元,这在当时不是一笔小数目。我朗诵了海子的《亚洲铜》,那是我最喜欢的海子诗作。
此刻,我就站在海子诗歌陈列馆背后的诗林中,就站在《亚洲铜》石碑的旁边。那块石头的纹理,天然带着一种黄铜的斑斓,在那上面镌刻海子的这首诗,真是太美了。我对妻子说,我要在此,抚摸着海子的石头或金属,再朗诵一遍海子的《亚洲铜》:“亚洲铜/亚洲铜/看见了吗?/那两只白鸽子/它是屈原遗落在沙滩上的白鞋子/让我们——我们和河流一起/穿上它吧。”
这时,我的双眼湿润了。举目望去,没有白鸽子的影子,天空中的雨滴也停了下来。我想到了屈原,想到了那只橘子。
饥饿的橘子
一说到橘子,我们便会想到两千多年前的楚国诗人屈原,他曾写下传诵千古的名作《橘颂》。这种固执地只生长于南国大地的神秘之树,不仅忠贞不移,而且,所结出的硕果美丽而灿烂。这样的果树,实在是生长于诗人内心深处的妙物。或者,在屈原的梦想里,他本身就是一株孤独的橘子树。借用阿多尼斯的话说:孤独是一座花园,里面有一棵橘子树。
火红的橘子,介乎太阳与月亮之间的果实,海子一定是喜欢的吧。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太阳是我的名字/太阳是我的一生……我必将失败/但诗歌本身以及太阳必将胜利。”
海子与火车的悲壮故事广为人知,但海子与橘子的故事,却是一段不忍言说的秘史。27年前,海子在踏向毁灭之途时,身上只带了三本他最心爱的书籍。但是,后来的医学解剖证明,海子身上还带着一样东西:人们在他年轻又绝望的胃里,看见了一只橘子。
橘子,这种让同样死于自杀的先辈诗人屈原歌颂过的水果,现在又被一个年仅25岁才华横溢的诗人揣进了最后的胃里。我坚信,海子并不是因为难耐的饥饿而吞下了那粒小小的果实,而是在以一种绝决的方式,海子的方式,向屈原述说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秘语。
对于橘子,我始终保持着敬畏:完美的肉质,可以充饥解渴,黄金般的皮壳,新鲜时可以做成照亮夜晚的灯盏,干枯时可以入汤入药。只要能闻到橘子的气味,生活就有了希望。
海子十分敬仰屈原,在他的灵魂里,很多时候,是与屈原同体的。有人甚至认为,作为诗歌烈士的海子之死,是对屈原的一种壮丽模仿。海子生前,曾写下《水抱屈原》一诗,来表达对屈原的热爱:“水抱屈原/一双眼睛如火光照亮/水面上千年羊群/我在这时听见了世界上美丽如画/水抱屈原是我/如此尸骨难收……”
在这首诗中,海子虽然没有提到橘子,但我却仿佛看到了它无比耀眼的身影:一双眼睛如火光照亮水面上的千年羊群,让诗人,也让我们,听见了世界上最美丽的画面。
“青黄杂糅,文章烂兮。”那只与海子一同乘坐火车抵达山海关外、并最终被海子吞下的,并不是仅仅一只饥饿的橘子,而是以春秋孕育、以生命滋养的苦难与甜蜜。
诗人与城市
没有历史,没有记忆的城市,就是一座空心的城市。
是海子应该感谢德令哈,还是德令哈应该感谢海子?
一座城市的记忆,很多时候是由诗人来构成的。比如,说到成都,就会想到杜甫草堂,说到德国的法兰克福,就会想到歌德。而说到德令哈,我们会不假思索地想到海子。尽管海子既不是德令哈人,甚至也没有真正在德令哈呆过,他只是坐火车路过,并写了一首《日记》。海子所思念的那个姐姐,在德令哈吗,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这个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诗人海子,已经成为德令哈的一部分。
海子可能永远也不会想到,他会以如此微妙的方式,以一首小诗和一座遥远的城市结下深刻的联系:诗歌成了德令哈和海子相互联系的脐带。海子已经离不开德令哈,德令哈也离不开海子。海子已经内化到德令哈的基本记忆之中,成为这座城市诗意的底色,同时也成为德令哈的另一种海拔高度。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诗人海子,在祖国的东边山海关陨落,却在西边德令哈获得了重生,甚至永生。辽阔无边的海西,的确是一个充满神性的地方,它能抚慰受伤的心灵,甚至能让你重振山河。
那么,到底是海子应该感谢德令哈,还是德令哈应该感谢海子?有一个事实可以肯定:很多异乡人,包括我自己,第一次知道德令哈,是从海子的《日记》中知道的。这个来自蒙古语“金色世界”的德令哈,总是让我想到北欧或西亚的一些景象。而且,德令哈的金色,恰恰也是海子最喜欢的,因为,金色是太阳的颜色。而太阳,那是海子诗歌永恒的火焰。